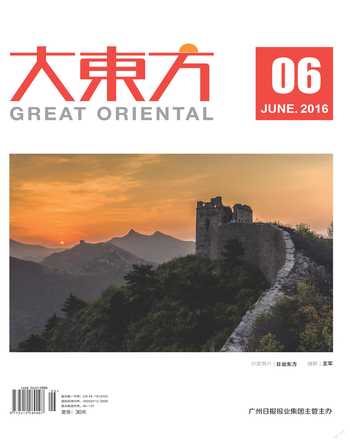淺談何鈞佑錫伯族民間故事的價值
陳維彪
摘 要:錫伯族民間故事的家庭傳承與文化自覺,其意義有四個方面,何鈞佑錫伯族民間故事的文化本真與書寫型傳承人關系,世界口頭文學的自覺結合和相互滲透。
關鍵詞:錫伯族民間故事價值;何鈞佑個性;世界民俗的多樣性;如何保護
錫伯族是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中人口較少的民族。我們大略知道,其族源有東海女真和鮮卑后裔諸說,在晚近幾百年中,錫伯族群經歷了從主要從事漁獵和放牧,進入逐漸定居農耕的階段。與其經濟生產生活的變化相契合,其文化藝術活動也經歷了諸多演變,留下許多未解之謎。從西伯利亞到蒙古高原,歷史上生活過眾多族群,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相當緊密和交錯,在分分合合中,留下了謎一樣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圖譜,錫伯族就是這樣,他們在歷史上與周邊族群有復雜的互滲關系,從其文化形態和特質上看,有大量與周邊民族集團共享的元素,同時也有其專屬的特質。鄂倫春族的摩蘇昆,赫哲族的伊瑪堪、滿族的說部等形態各異的北方民族口頭傳統典范,都已先后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何鈞佑《錫伯族民間故事》于2011年被國家文化部列入第三批非遺保護名錄,這些氣韻生動的口頭演述和極具生命情態的表現形式,承載著這些民族的歷史源流、人文傳統、文化認同和生活世界,被民眾視為本民族歷史的“根譜”和文化的“寶典”。這應當是我們理解錫伯族民間敘事的一個大前提。
當我們說一個民族擁有發達的口頭敘事傳統時,往往有兩層意思,一個是說這個民族的口頭敘事藝術文類多、數量大、傳播廣,再一個是說他們通常擁有造詣很高的、可能是職業化或半職業化的傳承人。何鈞佑的家族對講述錫伯族故事頗有造詣。他出生在錫伯族官宦世家,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接受了很好的故事熏陶,他掌握了錫伯族歷史上影響甚大的“郭爾敏朱伯”(詞意為“長長的故事”)這種關于部落英雄或部落歷史的長篇敘事。何鈞佑家族的口頭藝術傳承經歷,其實可以看作是錫伯族歷史際遇和文化變遷的生動縮影。
宏觀地看,“何鈞佑錫伯族長篇故事”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何氏家族傳承的錫伯族這些敘事以史詩般的氣勢和宏大的畫卷,生動反映了錫伯族人從歷史深處一路走來的足印。故事中不但有關于錫伯族歷史生活的全景交代,還有對特定人物、事件的細致描摹,堪稱歷史的特殊見證和詮釋。
其二,這些錫伯族故事不僅是對民族情感的藝術表達,信仰的堅守,正義和道德的宣示,還包含了民眾關于榮與辱、德行與失范、正義與邪惡、崇高與卑下等范疇的取態和立場,都體現的較為完整。
其三,少數民族的口頭敘事傳統,具有某種特殊的樣本意義。通過對這些樣本的深入解析,對社會文化演進過程中語言變化如何影響民間敘事等問題進行解析樣例。
其四,一個民族敘事藝術的高峰,往往通過其長篇敘事得到體現。一個民族是否能夠承載篇幅巨大的敘事藝術,并不在于其人口規模,而在于其藝術創造的動力和藝術消費的潛力。
以何鈞佑老人為例,他的經歷比較復雜——接受過高等教育,曾被認定為右派坐過監獄,還在國外生活過。這些經歷讓他與尋常所見多數民間故事家頗為不同。現在一些學者認為今天的社會生活已經發生巨變,拘泥于民俗學的所謂“本真性”,已經不大能適應時代的發展了。以美國民俗學界為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關于誰是民俗主體(誰民俗中的“民”)的討論,就漸次展開,鄧迪斯、布魯范德等人,皆有精辟論述。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民間文化傳承人,接受了現代教育,通過現代傳媒和其他渠道,獲得大量不屬于本土的民間文化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和知識也在改變著他們的觀念。
在談論我國史詩演述者群體時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觀點:就已經發現的材料來看,史詩演述者群體,可以視作一個譜系,而不是內部有高度同一性的群體。從受過教育的大體等同于“文人”的“書寫型”傳承人的一端,到地道文盲傳承人的另一端,其間真不知有多少復雜的中間形態。倫洛特作為醫生和文人的在大量收集民間詩歌的基礎上,創編了大型史詩《卡勒瓦拉》受到熱捧,被認為是芬蘭民族精神認同的最主要象征。美國學者約翰·邁爾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芬蘭學者勞里·杭柯(Lauri Honko)認為,倫洛特所“書寫”的《卡勒瓦拉》應當被界定為一類“以傳統為導向的”(tradition- oriented)文本,從而確認了它與民間傳統的關聯程度以及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國境內,衛拉特蒙古“江格爾齊”(史詩江格爾演述者)加·朱乃在大量吟誦之余,也親手謄寫詩篇若干,且刊印出版;在歷史洪流的進程中,總會有人扮演銜接書面世界和口語世界、書面文學和口頭文學兩個世界的角色。巴爾干半島的普列舍倫和涅戈什,是民間詩歌向書面文人詩歌轉化過程中的特殊關折點,他們本身既是接受了系統教育,又是傳統的民間文化的繼承者,他們的作品中含有大量的民間敘事成分,也有某些書面文化的影響,作為脫胎自民間口頭詩歌的文人與詩人,他們的文學活動起到了打通了兩個世界的作用。現今對于他們文學創作活動的述評,對我們研究而言頗有啟迪作用。何鈞佑的“創編”過程及成果,從現象上看與“以傳統為導向的文本”多有類似之處,他本人具有“書寫型傳承人”的諸多特點。不過,在做出深入的研究之前,我們還不能下此論斷。我的看法是,在社會日益發展、教育日趨普及、信息交流日新月異的今天,抱持今天的民間傳統乃是古代“遺留物”的陳舊觀念,而不能夠將民間文化視作永遠流動的生命過程,是無法回答新時代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的。
從2006年起,沈陽市于洪區文化館即著手對何鈞佑的故事講述實施保護與采集工作。在專家的培訓與指導下,區文化館先后組織了五支由遼寧大學民俗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教師們組成的工作組,有條不紊地進行了系統的采錄得到保存。通過錄音錄像和文字等方式記錄下來的何氏家族傳承的敘事。在刊布時,整理者根據出版要求,只在文法、句式和史實方面做了適度的調整,總的原則是盡可能保持講述者的語詞風格和特點,從而使這幾部錫伯族長篇敘事較好地保留了錫伯族“郭爾敏朱伯”的質樸風貌與特點。使之有機會讓學界有機會接觸到這些頗具特色的、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敘事藝術。
(作者單位:遼寧省沈陽市于洪區文化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