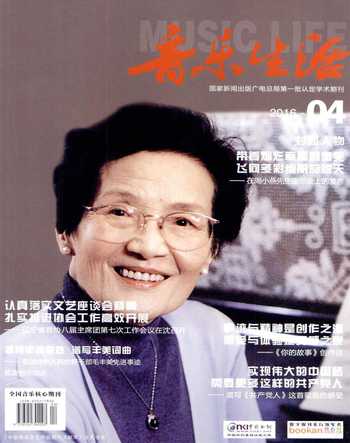獻給瓦格納
車新春


布魯克納于1872年10月開始創作《第三交響曲》的時候,已經存維也納居住了4年。到維也納之后,鄉土氣息濃郁的口音、怪異的舉止、笨拙的社交等等,使得布魯克納完全無法適應維也納的生活,實際上,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他一直處于一種緊張與焦慮的狀念,并且承受著繁重工作的壓力,后來才逐漸得到緩解。
《第三交響曲》正是創作于這段時間,完成于1873年年底。與布魯克納的其他交響曲一樣,作曲家隨即開始了持續的修訂工作。他先后進行了5次修頂,一共存留下來7個稿本。修訂工作集中于1874年、1876年、1877年(1878年潤色)、1880年、1889年。現存比較重要的三個版本分別是1873-1874年的第一版,1877-1878年的第二版,以及1889年的第三版。
《第二二交響曲》(WABl03,d小調)又被稱為瓦格納交響曲,這是因為布魯克納去拜羅伊德拜訪瓦格納的時候,拿著《第二交響曲》與《第三交響曲》的總譜,希望瓦格納能夠接受其中一首的題獻,瓦格納欣然接受了后者。不僅如此,在最早的1873年版本中,布魯克納還引用了瓦格納某些著名的音樂片段,例如,《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愛之死”動機、《女武神》的睡眠動機,等等。這些引用雖然存布魯克納后來的版本中有所刪減,但這部作品不可避免地被貼上瓦格納陣營作品的標簽。
對瓦格納的題獻以及對其音樂的引用,帶給布魯克納的是災難性的后果,當然布魯克納大膽的和聲與配器效果也令維也納觀眾的耳朵難以接受。首先,首演變得困難重重。布魯克納先是將總譜交給維也納愛樂樂網,該樂團指揮德索夫原本答應上演,之后卻告知布魯克納節目單上已經無法再安排這部作品,樂團后來又答應演出,接著又以無法演出為由拒絕了布魯克納。幸虧他的朋友海爾貝克但任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管弦樂團的指揮,準備支持布魯克納完成首演,然而還沒有排練完,海爾貝克就去世了,幾經周折,作品終于在1877年12月16日首演了,此時、布魯克納的《第四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都已經完成了。由于沒有指揮愿意出演這部作品,布魯克納只好親自上場。觀眾對這次演出的反應也是冷淡的,僅有幾個忠實的支持者在祝賀他。漢斯利克的評論同樣是尖刻的,他在《維也納報》上甚至指責布魯克納“把貝多芬音樂與瓦格納音樂攪合在一起,而最終又屈服于瓦格納風格的影響”。
布魯克納對瓦格納的崇拜始于十多年前。將布魯克納引入瓦格納音樂世界的是奧托·基茨勒(ottoKitzle),他不僅引領布魯克納研究總譜,幫助他認識到瓦格納音樂作品中的新穎配器和作品的美,而且引領布魯克納了解如何構成形式、如何配器與作曲,為他打開通往交響曲創作的道路。實際上,基茨勒從孩童時代就開始崇拜瓦格納,他不僅出席了德累斯頓的《唐豪塞》首演,而且作為童聲合唱團的一員,參與了瓦格納在1846年指揮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出活動。基茨勒在維也納拜訪了瓦格納,獲得他的許可,得以在林茨演出《唐豪塞》。1863年2月12日,布魯克納在林茨第一次觀看了《唐豪塞》。瓦格納的音樂深深地吸引了這位原本僅僅熟悉傳統音樂的教堂音樂家,雖然二者在風格與氣質上幾乎沒有相似之處,但它無法抵擋布魯克納的崇拜,并且激勵著布魯克納去尋找自己的獨特風格。
《第三交響曲》采用四樂章的形式。它呈現出《第二交響曲》的某些結構特征,例如首尾樂章采用奏鳴曲式,并且擁有三個主題,柔板樂章采用五部形式,諧謔曲具有鮮明的奧地利鄉村舞蹈的音樂特質,音樂不時出現一些大的休止,等等。但是,與《第二交響曲》相比,《第三交響曲》的每個樂章的個性更為突出。
第一樂童的演奏時間遠遠超過其他樂章,超出柔板樂章與終曲一半之多,超出諧謔曲近三倍,可見這一樂章在整首樂曲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音樂一開始,PP的力度,弦樂奏出的安靜震音、木管及隨后的銅管吹出的長音,都彌漫著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氣息。然而,布魯克納的做法又與貝多芬不同,布魯克納一開始就堅定了樂曲的主要調性d小調,由大提琴和貝司奏出的D音上的持續跳音,顯示出這種決心;貝司則是一開始就通過模糊調性,產生音樂發展的強大動力。
開始的小號主題又令人想起瓦格納《漂泊的荷蘭人》的開始動機,這個小號主題令瓦格納印象深刻,據說,當人們存他面前提及布魯克納的時候,他就會叫道:“是的.小號!”
這一樂章一共有三個主題,性格各有不同。主部主題富有英雄氣質,它經由次要主題以及漸強力度的鋪墊逐漸引入,并且陳述了兩遍,一遍是在d小調上,一遍是在降B大調上。副部主題組溫暖柔和,具有舞蹈音樂律動,它巧妙地運用了所謂的布魯克納節奏型(3+2和2+3)。并目.一直持續了70多個小節,這一主題組包含兩個主題。一個是由第二小提琴奏出的優美主題,一個是中提琴與圓號奏出的抒情片段,它們以對位的手法,相互呼應。第三主題是木管與銅管的八度齊奏,音樂莊嚴肅穆。呈示部的結尾處,作曲家引用了自己在1864年創作的《d小調彌撒曲》中降福經中的Miserere樂句。在發展部中,作曲家在不同的調性上運用呈示部主題進行發展,并將音樂推向高潮。再現部進行了簡化,再一次強調了d小調這一主調,尾聲令人再次想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最后音樂結束在輝煌的全奏中。
第二樂章的情感深沉內在,它在布魯克納作品中處于非常經典的位置,布魯克納的“柔板作曲家”的美譽就是由此而來。第二樂章的結構在不同的版本中有所不同,有些與《第二交響曲》一樣,采用ABABA的結構,有些則采用了ABCBA的拱形結構。這一樂童不僅綜合了古代與現代的音樂元素,將19世紀的宗教音樂、瓦格納的音樂動機與大膽的和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漳顯出它與步魯克納宗教音樂作品之間的密切聯系。例如,主部主題與布魯克納在1842年所寫的《C大調彌撒曲》中的降福經中的主題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第三樂童的諧謔曲雖然看似簡單,但動感十足。這一樂漳中,諧謔曲狂風暴雨般的動力與三聲中部中優雅的蘭德勒舞曲之間形成巨大張力。諧謔曲一開始的力度是PP,這是布魯克納在前幾首交響曲中從未用過的。同時,他借鑒了貝多芬的方法,音樂一開始就存低聲部上。通過從屬音半音級進上行最終到達主音——這種傾斜式的方式,肯定了d小調這一全曲的主要調性,并且整個樂章成功融合了多種不同風格的音樂元素:奧地利鄉村舞蹈、恢宏的管風琴音樂、牧歌風格的音樂等。
第四樂章回憶與綜合了之前的所有主題,并將音樂推向全曲最終的高潮。它的三個主題個性鮮明。英雄性的主部主題在弦樂的顫音背景下奏出。副部主題擁有兩個不同風格的主題:一個是弦樂奏出的波爾卡舞曲風格的歡樂主題,一個是銅管奏出的圣詠風格的冥想的痛苦主題,二者處于同一時空領域,并且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多重復雜的情感氛圍。第三主題是由銅管奏出圣詠風格的音樂段落。在全曲的結尾處,音樂由d小調轉入D大調,存狂歡式的輝煌凱旋中結束。
有學者指出,布魯克納前半生的意義在于做著一項準備——即為他后半生的交響曲創作做準備。《第三交響曲》成為他個人創作風格形成的標志,杰拉爾德·亞伯拉罕指出,不明確的主題、管弦樂色彩與和聲形成的巨大塊狀音樂、經常占據支配地位的銅管樂、提供力度與主題頂峰的終樂章等音樂特征是在《第三交響曲》中形成的。當然,也有評論家認為,這首交響曲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例如,在曲式結構上存在著不平衡的現象、對瓦格納音樂的引用不合理、缺乏音樂發展的動力,等等。但無論如何,這部交響曲都值得大家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