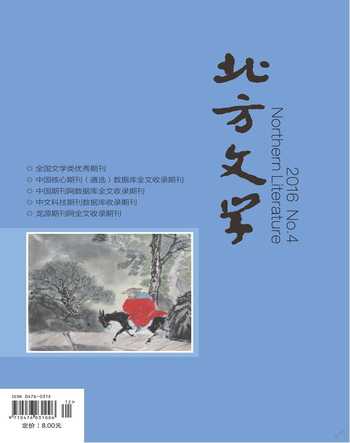病態(tài)又迷人的殘酷之美
喬夢楨
初讀《檀香刑》時還小,帶著顆獵奇的心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讀完,為此失眠了數(shù)夜。之前一直認為最邪惡的酷刑莫過于將人活埋至頸,剖開頭皮,皮肉間注入水銀,曝于太陽下,受刑人難耐奇癢,最終從自己的皮中跳出——這回又多了個檀香刑。近年又讀了數(shù)遍,其華麗的結(jié)構(gòu),濃郁斑斕的語言,鮮活飽滿的人物,所描繪那段磅礴蒼涼的歷史,都令人贊嘆。但最令人著迷的,是它所蘊含的殘酷之美。
“殘酷”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以貫之的,《生死疲勞》中財主西門鬧被槍決后在畜生道里永世輪回;《酒國》中嬰兒被紅燒成一道名菜,父母們爭相販賣自己的孩子;《豐乳肥臀》中女知青為了一個饅頭一邊被強暴一邊大嚼大咽,最后卻被撐死。莫言寫這些殘酷時是冷的,不動聲色,冷眼旁觀;而《檀香刑》更矛盾些,它以集殘酷至極之刑為載體,活潑又冰冷,恣意放蕩又一本正經(jīng),令人絕望又叫人著迷,形成了一種病態(tài)而又迷人的殘酷之美。
先說這殘酷之病態(tài)。
小說中主要描寫了六場行刑,筆墨舒緩,儼然一場精彩絕倫的貓腔大戲。“閻王閂”一出場便不俗,小蟲子一雙大閨女般的俊眼“從‘閻王閂的洞眼里緩緩地鼓凸出來,黑的,白的,還滲出一絲絲紅的”;腰斬似一個小小的鋪墊,腸肚迸出,血沫飛濺,赤裸裸的慘狀被赤裸裸地寫出;兩場凌遲穿插出一幕小高潮,細膩而癡情,青年軍官勻稱健美的身體,名妓凝脂般的雪肌,第五百刀剜下的心頭肉好似胸口一顆朱砂痣;戊戌之斬是曲大悲調(diào),六君子各狀與趙甲的快刀構(gòu)成一曲悲壯樂章;檀香刑是壓軸大戲,著墨最為濃烈,隨著檀木橛子一點點釘入孫丙的身體,全書也迎來了的高潮。《檀香刑》是文壇中極罕見的將中國酷刑描寫得毫不避諱的作品,且極富細節(jié),流血呻號冷汗失禁全都擺上臺面,多種感官躍然紙上。這種將酷刑寫得認真又興致盎然的風格,就仿佛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一邊笑瞇瞇地散糖,一邊給孩子們講著最恐怖的村野鬼話,讓人不禁毛骨悚然:這是怎樣一種病態(tài)的創(chuàng)作手法?這是怎樣一篇詭譎的故事?
這病態(tài)也真切地體現(xiàn)在小說中的人物身上。統(tǒng)治者好欣賞酷刑,無論是東方咸豐“必須把執(zhí)刑的過程延長,起碼要延長到一個時辰,要讓它比戲還要好看”,還是西方克羅德“希望能有一種奇特而殘酷的刑罰,讓犯人極端痛苦但又短時間死不了”。行刑于他們而言就是一場娛樂活動,看著逆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著臣子百姓惶恐昏厥,看著被征服者面如土色卻只能曲意逢迎,他們心中當是充滿了無限的快感,無盡的成就感,和無窮的自滿、自傲與自戀。
至于刑場的看客,似乎早在魯迅筆下就已是“病態(tài)”的代言人。一場酷刑中,劊子手與受刑者是主角,但臺下的看客才是精髓所在;就像一場戲,若無觀眾吶喊叫好或是沈默,便不成其為戲。《檀香刑》的看客與魯迅筆下麻木愚鈍的看客是不同的,他們更具獸性,帶著欲望和需求而來,盡興而歸。他們擅長用“漢子,漢子,說幾句硬話吧!說砍掉腦袋碗大個疤”這類話來鼓動渲染氣氛;會在被凌遲的妓女掛著金耳環(huán)的耳垂被扔到地上時“猶如洶涌的潮水,突破了監(jiān)刑隊的密集防線,撲了上來,嚇跑了吃人肉的兇禽猛獸”;喜好以劊子手的技藝與受刑者的死狀作為談資,使一場酷刑余音繞梁。看客們一邊欣賞著他人的殘酷,一邊慶幸著自己的幸免;一邊憐香惜玉著瀕死的名妓,一邊恨不得咬光美女身上的肉。他們摩拳擦掌,他們血脈賁張,是酷刑與死亡的真正的消費者。
再看這殘酷之迷人。
酷刑固然慘不忍睹,但無法否認它獨特的吸引力,不然怎使得人們爭相一睹。人對痛苦忍耐的極限在哪里,一場刑罰究竟能達到怎樣精彩的程度,美究竟可以怎樣被毀滅,這一切都讓讀者們躍躍欲試。試想,一具健美的肉體被均勻分割,只剩一副枯骨的妓女臨死前鵝蛋臉依舊絕美,聲音蒼涼的男人高懸于檀木上宛如受難的耶穌。還有那雞血蒙面的劊子手,手法精細,刀風尖利。這一切,怎不是一種詭異又致命的美,怎不讓人心醉神迷!
一場轟轟烈烈的死,是這殘酷的另一迷人之處。每人心中都有悲情英雄的情結(jié),英雄生前成事與否不重要,死得悲壯、可歌可泣就好。錢雄飛、孫丙之流的結(jié)局便成了理想,甚至還要加以拓展。行刑前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儼然鐵漢一條;行刑中要怒目圓睜,破口大罵,最好留下句讖語,引得臺下看客如癡如狂;死后要入詩,要入戲,要驚天地泣鬼神,要名留青史——當死亡成為無力感的宣泄,酷刑成為精神的寄托,殘酷何嘗不是一種誘惑?
病態(tài)也好,迷人也罷,歸根結(jié)底便是兩個字:人性。麻木、愚昧、殘忍、邪欲,與其說是人性的原罪,不如說是人性的本真。現(xiàn)今說,美女最美的時刻是被潑硫酸的時候;那么在《檀香刑》的語境里,那妓女最美的時刻便是被一塊塊凌遲的時候。人們喜于看見美被破壞而惡肆虐,喜于看見他人受難而自己幸免,喜于做無謂的反抗和乖遂的順從,喜于在集體無意識的殺戮狂歡中暫時失掉所謂神性、盡情袒露獸性。所以我們在品讀《檀香刑》的殘酷時,會猛然升騰起隱秘的快感,會沉浸于這病態(tài)而又迷人的美。
莫言在談及《檀香刑》時曾說:“在構(gòu)思的時候,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受刑者,其實人類靈魂中有著同類被虐殺時感到快意的陰暗面,在魯迅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寫這些情節(jié)時,我自己就是一個受刑者,在‘自己的虐殺下反而有種快感。酷刑就像是一場華美的儀事,整個大戲都在等待這個奇異的高潮。”文人的筆,如劊子手的刀,將自己剖開,直面人性的丑惡——這是對靈魂的拷問,是慈悲的救贖,是真正的文學的良心。莫言稱《檀香刑》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但實際上,它只是披著貓腔的民間外衣,其荒誕陸離的想象,其殘酷敘事的方式,仍是以先鋒的意識與姿態(tài),引領了人性敘事的前進。
當然,《檀香刑》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如想象力與語言恣肆而無節(jié)制,部分情節(jié)前后矛盾(如凌遲妓女原本為余姥姥所為,后來卻變成了趙甲所為)。但瑕不掩瑜,《檀香刑》以其精妙的結(jié)構(gòu),深沉的境界,以及詭譎殘酷的美感,注定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