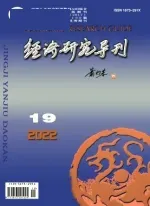社群主義視域下的城市規劃公眾參與
金煥玲
摘 要:歷史、文化和政治等原因,使得目前我國城市規劃公眾參與還處在一個起步階段。從社群主義的視角出發,提出增強城市規劃公眾參與度需要建立“城市共同體”的思維框架。首先,需要規劃者具有全局和整體意識;其次,需要公眾樹立積極主動的社會責任意識;再次,需要公眾具有參與城市規劃的奉獻意識。
關鍵詞:社群主義;城市規劃;公眾參與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3-0132-03
一、社群主義概述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在韓國、日本及臺灣地區多翻譯為共同體主義,也有稱之為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社團主義、新集體主義等。
作為社群主義之核心概念的社群一詞古已有之。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社群即指“城邦”。他認為:“社群團體不僅使人類可得更廣泛的經濟自給,而且可以使人們能夠向往共同體優秀的道德生活。” [1]之后,社群思想一直受到了歷代許多思想家的重視,西塞羅、奧古斯汀、阿奎那、愛德蒙·伯克,再到約翰·密爾、黑格爾和杜威等。直至19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埃米里·杜克海姆于1887年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社群主義的概念,并把它看作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后來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群學說。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社群主義的聲音一直顯得比較微弱。直至20世紀80年代,發軔于對美國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正義論》一書批評的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當代政治哲學思潮和倫理思潮在吸收、繼承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和成熟,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理論,并成為一種可以對占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產生嚴重威脅的主要思想派別之一。
當代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戴維·米勒 (David Miller)、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阿米泰·依左尼等。
當代社群主義的誕生,從表層次看是緣起于對羅爾斯等人自由主義的直接批判;而從深層次講,則離不開當時各種社會現實因素的影響。首先,國家的不作為與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西方在20世紀80年代雖然實現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但卻造成了失業率高居不下的結果,同時也使得兩極分化更難對付。”[2]總人口1/5最富裕人口的收入與最貧窮的1/5人口的收入,兩者之間的比率從1960年的30∶1增長到60∶1。其次,個人主義大行其道、道德危機嚴重。在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新自由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主流。長期奉行個人主義價值觀,過分強調個人的自由及權利,導致了一系列“現代性的病癥”。再次,傳統社群日益衰落、新型社群逐漸興起。隨著西方發達國家信息化的不斷加強,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趨于一體化,各種利益團體的作用被嚴重削弱,傳統的中間性社群如教會、社區、協會、俱樂部、同人團體、職業社團、等級、階層、階級、種族等在市民社會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嚴峻挑戰。與之同時,一些新的社群如綠色運動組織、反戰和平組織、女權運動組織等新社會運動社群卻在西方國家中出現,并且對現實生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和作用。最后,20世紀70年代后興起的新人權運動(第三代人權運動)及新“社群運動”應該說也為社群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社群主義作為對自由主義進行反思和批判的產物,在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完備的思想體系。首先,它建構起“目的優先于自我”道德哲學基礎;其次,它確立了“社群”本位的倫理價值取向;再次,明確了“善優先于權利”的道德價值理念。這一理論的確立使其在道德實踐領域特別強調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權利。他們認為傳統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基于“權利優先于善”的錯誤觀念,給予了個人權利消極意義上的理解,造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消極影響之一就是:公民對于國家事務漠不關心,缺乏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缺乏對公共利益的認同,不愿承擔應當承擔的國家義務。只有個人積極參與團體的或國家政治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在群體或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強調被自由主義輕視的積極權利、集體權利[3]。麥金太爾心目中的共同體,就是個體善、共同體善、生活善的統一,是內在善第一、生活善第一、共同體善第一的統一。
二、我國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現狀、問題及成因
改革開放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城市規劃照搬蘇聯模式,完全是一種政府主導的行為。城市規劃實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公眾沒有參與的渠道和途徑,也缺乏參與意識和參與的積極性。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加快,以及“以人為本”“民主參與”等現代理念的逐步確立,城市規劃逐漸走入大眾視野,并通過立法確定了公眾參與規劃的權利和地位。城市規劃公眾參與在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信息公示、舉行聽證會、論證會等公眾參與的渠道和途徑逐漸得到落實,但是目前中國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仍存在著不少問題。具體如下:
一是公眾參與程度較低。參與程度可以從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兩方面看。目前,在很多城市規劃編制、規劃項目審批過程中公眾參與的深度并未隨著規劃項目級別的提高隨之加深,大多停留在公示等形式層面。許多規劃建設項目都是由政府領導說了算。參與的寬度是指公眾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范圍和公眾參與的比例。我國城市規劃中市民參與的權力和范圍受到許多因素的限制,而市民參與的比例也很小。另外,公眾參與受市民自身環境、利益、性別、年齡、職業等條件限制,外來人口參與少[4]。二是參與機制不健全。目前我國在城市規劃的編制、審批等階段存在組織協調機制、執行保障機制、反饋修正機制等不完善的情況,從而造成公眾參與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三是公眾主動參與意識不強。有些人在涉及個人利益時表現出較強的參與意識,主要是維權意愿強烈,這是一種被動的參與,而不是主動的,基于社會責任感進行的參與程度非常低。四是參與效果不明顯。按照美國規劃師莎莉·阿爾斯坦提出的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程度的階段模型理論,即“市民階梯理論”(最低層次是“無參與”(Nonparticipation)、第二層次是“象征性的參與”、第三層次是“市民權利”)。目前,我國的公眾參與程度還遠未達到第三層級即“市民權利”的階段,基本處在“象征性參與”或“無參與”階段。
我國公眾參與程度較低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從歷史文化傳統看,我國古代城市的建立和發展更多的是出于軍事政治目的。《吳越春秋》中講到: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藝文類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由于統治者對于城市軍事意義的極端重視,所以在建造城市的過程中多是由上層主導,城市規劃采取的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缺乏普通公眾的參與,從而未能形成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歷史傳統。其次,從政治層面看,建國后人民享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力,對城市規劃等理應有發言權,但是由于法律法規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人民或者以運動的方式參與國家政治事務,或者不參與,這對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程序化運行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再次,從經濟方面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廣大民眾為了擺脫物質貧困不斷謀求經濟利益,參與政治的意識逐漸淡漠,這也造成了參與城市規劃尤其是基于社會責任感的參與程度非常低的情況。
三、城市共同體: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邏輯和現實起點
社群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理論影響,盡管也有許多問題,但它對于批判極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為人們的公共生活進行辯護等方面具有的積極意義是不可否認的。社群主義以共同體的利益為出發點,能使城市利益實現最優化。
城市共同體,強調整體、統一、協調地解決問題。公眾以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城市發展,規劃考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口、環境、交通等各個方面。城市共同體,是指不單是一個城市,它包括城市群共同體,如京津冀一體化就強調協調有機統一和互相對話。城市自身發展中所形成的“整合性”和“內在關系”以及城市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決定了“城市共同體”的思維構成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邏輯和現實起點。
我國城市發展的現實背景決定了我們必須一種宏觀的視野解決和面對城市發展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在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城市問題,被稱之為“城市病”。首先,城市貧富分化嚴重。收入差距加大、居住空間分化、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身份階層的固化等,都體現出城市發展中的財富分配不均衡現象。其次,環境問題越來越嚴峻。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污染、電磁輻射污染等,嚴重影響了人們的身體健康和城市發展。再次,交通擁堵問題難化解。我國很多大中城市的交通擁堵范圍逐漸擴大,擁堵交叉口及路段越來越多,擁堵程度越來越嚴重,這大大降低了城市的宜居性和市民的幸福感。
“城市共同體”意識要求我們面對各種“城市病”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應對:
首先,需要規劃者具有全局和整體意識。只有認識到城市體系中各種事物相互之間的關系,才能根據整體成本和收益,預知建成環境的私人生產者、業主利益、城市貧民等所面臨的問題,從而做出認真的努力,緩和已經出現的危機[5]。按照“交往性規劃”理論,規劃的決策過程是一種“政府—公眾—開發商—規劃師”的多邊合作,目的是取得所謂“合意”(consensus),即共同體成員通過各自的策略選擇而達到的一個均衡結果。這也需要規劃者改變過去自持的精英地位,轉而去適應同時扮演多種角色——公眾參與的組織者和促成者(organizer)、公眾意見沖突的調停者(mediator)、為特定價值辯護的交涉者(negotiator)[6]。
其次,需要公眾樹立積極主動的社會責任意識。有學者指出,社群主義認為,社群價值目標的實現需要懂得規范的好公民,更需要擁有德性的好人,因此,公民教育的重點應該是道德教育。社群主義的道德教育觀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以整體主義世界觀為哲學基礎,以公益至上價值觀為理論前提,以培養有德性的好公民為教育目標,以促進公民參與實踐為現實途徑[7]。
再次,需要公眾具有參與城市規劃的奉獻意識。目前,我國的公眾參與還處在比較低層次的水平,出現的很多公眾參與的案例也多屬于這樣的情況,即“只有到了生活不方便時才呼吁一下,反映一下,以期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和解決,從而形成了關切到自身利益的事務參與多,公共利益方面參與少的局面。”[8]公眾普遍缺乏公益心和奉獻精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搭便車”等心理,嚴重制約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深入進行。所以,必須大力宣揚和培育公民的奉獻精神才能真正提升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和建設的層次和水平。
參考文獻:
[1]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 常成寶.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群主義[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
[3] 孫枝俏,王金.尋找市場社會的道德基礎——評西方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觀念之分歧[J].求索,2007,(2).
[4] 李東泉,韓光輝.我國城市規劃公眾參與缺失的歷史原因[J].規劃師,2005,(11).
[5] 高鑒國.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6] 程遙.超越“工具理性”——試析大眾傳媒條件下城市規劃公眾參與[C]//和諧城市規劃——2007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2007.
[7] 何霜梅.試論社群主義的道德教育觀[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3).
[8] 趙秀敏,葛堅.城市公共空間規劃與設計中的公眾參與問題[J].城市規劃,2004,(1).
[責任編輯 陳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