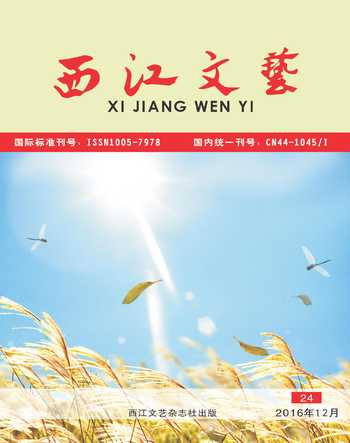性情與格調
孫萍
【摘要】:明清詩歌流派眾多,各個詩派都有自己的詩歌理論,性情說、格調論等文學理論盛行。性情說最典型的代表詩人當屬明末公安派袁宏道,他強調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認為詩歌只要能抒發真實的心理感受,就是好詩。到清中葉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詩派與袁宏道一脈相承,強調詩歌表現自我、生動風趣。格調論的主張者則前有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和李東陽創立的茶陵派,后又以沈德潛為主的格調詩派。
【關鍵詞】:詩歌理論;性情說;格調說
一、性情說
先秦時期,“性情”已經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出現在先哲們的文論中;魏晉南北朝時期,詩道“性情說”開始大量出現在詩學著作中。“性情說”于晚清更是在“詩言志”、“詩緣情”、“性靈說”這幾種傳統詩論中脫穎而出,成為眾多詩學流派成員論詩的核心詞匯。性靈說本是詩家習用的概念,眾多詩人尤其是崇尚性靈的公安派都以性靈為詩歌的核心要素。不過他們對“性靈”一詞的使用,內涵與之前的意義大致相同。“性靈”即性情,強調自由不受束縛,抒發真實情感,外現為“趣”、“韻”。韻、趣擺脫了理的束縛、書的制約,強調獨特的個性抒發。袁宏道主張詩歌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有性靈有真詩,有真詩有真情”,“抒發情感可以怨而傷,也可以憤而怒”。真性情就是真性真情也。其實就是晚明社會普遍流行的感官享樂與自然情欲追求,也就是袁宏道自己所言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的生活。真情,是人之自然喜怒哀樂嗜好情欲,質樸率直的情感。唯有出自真性真情之詩方為性靈之詩,也是他所說的“出自性靈者方為真詩爾”。
袁宏道從抒發性情出發,反對易古道今。主要抨擊后七子“以擬為復古”,以格調縛手縛腳的創作方式,他指出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強調“世道既變,文亦因之”,所以“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他認為,要做到文不拘格套,全從胸臆間流出,首先要有自己獨立特異的見解與胸襟懷抱。就是“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因此,他在《答李之善書》中說: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之所不能發、字法、調法一一從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所以,袁宏道為文靈機活轉,不蹈前人一矩,不習古人一語,既創新意,又發新言。只是,袁宏道總是矯枉過正、過偏過激。
到了清代袁枚筆下,“性靈”這一說法既吸收了前輩諸多詩家的理論,由發散了自己的枝椏開出了不同的果實發展為一個具有豐富意蘊和特殊指向的學說。袁枚詩學通常被稱為性靈派,它與格調派,肌理派并稱為晚清詩壇的三大詩學。同為性靈說,在明代是趨風氣,到了清代則為反潮流。明代性靈說關心的是改變文風,而清代則要求是改變學風。“理學家從善惡出發,將性情割裂,主張滅情復性;性靈派則從真假著眼,將性情合二為一,提倡直抒真情”。[1]袁枚的性靈說,性指的是真摯自然的性情,靈是表現靈活性靈即性情,就是內心的情感體驗與人生體驗,可直接抒發,也可借物抒發。性靈強調表達性情,詩中有我,詩求純真,詩貴神韻,詩尚自然。
袁枚的詩學是自我表現的詩學。他認為詩關性情是詩應表現詩人各自天生而成的個性、方情,就是說應“著我”。袁枚針對沈德潛的格調說,進而提出詩應抒寫“我”之性情為本,以擬古格調為末,貴乎獨運機抒,自成樊籬,而不可隨人俯仰,寄人籬下,或囿于古人尺尺寸寸,作繭自縛。并把步亦趨之擬古派譏為:“抱杜韓以凌人,而粗腳笨人者,謂之權門托足,仿孟以矜高,半吞半吐者,之貧賤驕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之韻者,木偶演戲,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迭韻,次韻,剌剌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 一字一句自注來歷者,謂之古董開店。”[2]
晚清詩話中的“性情”說在某種意義上為即將到來的新文學做了一種思想上的準備。“性情說”自有不可磨滅之處,因為詩本身就是一種特殊文體,在內容上應該和個性相結合,在形式上應該有特殊的表現。“真性情”、“不俗”、“立誠”、“我”、“本色”、“因時”等與“性情”說聯系緊密的因素時常出現在新文化運動代表者的詩論中。可以說,晚清詩話中的“性情”說為現代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一些理論先聲。
二、格調論
“格調”概念的第一層,是眾所周知的,是指詩歌的體制聲律等形式上的法度。所謂體制的法度,是指在較長的詩歌創作傳統中建立起來的有益于詩歌創作更完美的規范。具體來說,就是認識到不同的情誼必有合意的體制來配合。
明代中期,前七子發起了一場聲勢浩蕩的文學復古運動,在詩歌方面主張“詩必盛唐”,明確提出宗法唐詩的詩學主張。前七子主張以詩人性情作為詩歌的本質,最推崇盛唐詩歌性情,這種詩學思想正是受到了前期詩壇宗唐性情理論的啟發和影響。明代七子派被后人稱為格調派,是因為他們標榜古人作品的格調,并力倡師摹古人的格調。這種“格調”,以“高古”為特質;這種“高古”,主要表現為以下美學特征的完滿融合:發乎情性,文質相兼,意境渾成,氣勢沉雄,聲調宛亮,神韻流動。重情、追求“情真”,是明代格調派詩學的重要特征。但辨析相關觀點所處原始語境后可以發現,該派很多重情言論,以不同方式呈示出對傳統儒家詩學“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認可,與“真詩在民間”一類觀念在價值立場上存在差別,不能混為一談。格調派情感觀中體現“真正合一”、“以正律真”精神的內容與其格調論在思維方式上均有重規范、明限度的傾向,在價值理想上均以儒家人格典范為歸宿。因此,該派“重情”與“尊格調”具有共生的必然性。
明代七子都是主情論者,因此他們被列為較為典范的詩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發乎性情,凡是被視為格調一類的詩歌就一定具有抒情的特征。“感觸突發,流動情思”(《缶音序》)是李夢陽描述詩歌發生狀態時所用的詩句,“歌之心唱,而聞之者動”是他在描述詩歌審美效果時候所做的詩句。此后的格調論也都著眼于性情的抒發。在明初文壇,李東陽創立的茶陵派,以格調作為詩評的手段,對其后詩學走向影響頗深。李東陽把前人詩論中屢屢出現、但多單列的“格”、“調”兩字,合鑄為一個相對穩定搭配的“格調”一詞,形成特有的格調論詩學,對七子以后復古主義文學創作、理論生成及批評實踐,意義重大。李東陽的“格調論”,以對作品的精讀默察為基,以“具耳”和“具眼”為途,來辨別詩文的“格調”與“時代格調”,進而辨析各種詩歌體裁的思想品質、藝術風格,具有明確的辨體意識,對人們更為細微地把握古典詩歌的美學特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此外,格調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是對前人詩學思想的傳承,與詩歌自身的發展規律相一致,自然會成為明代的主流詩學。
沈德潛論詩,承襲明七子,既重思想規范,又重詩法、聲韻、氣格等。雖然他與七子都重格調尊盛唐,但詩學目的不同,沈德潛企圖由盛唐格調上窺風雅遺意,發揮詩教功能,強化儒學規范,抵御神韻末流的才力單薄、冷清枯寂。“格 調”用語的基本含義是指“體格聲調”。具體地說,“格”是指詩歌體制上的合乎體式、規格;“調”則是指詩的聲調韻律,所以“格調”也稱之為“格律”。沈德潛的“格調說”,以崇奉漢魏盛唐雄渾悲壯詩風為顯著特色,這一點,其門人王昶《湖海詩傳》有個極明白的說明:“蘇州沈德潛獨持格調,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詩”,“以漢魏盛唐倡于吳下”即是說,“崇奉盛唐”、“以漢魏盛唐為宗”是沈德潛“獨持格調”的根本宗旨。
沈德潛在論“格調”時,往往把“格調”與詩人的人格品質聯系起來。他尤其心儀那些志行絕塵、人格方面足以流芳千古的詩人。同時,把“格調說”與詩歌內容聯系起來,主張要言之有物。在他眼中,詩歌必須面向現實,為現實人生服務。正是出于對詩歌內容的重視,他同樣遵循先內容后“格調”的思路。沈德潛的“格調說”是在其詩教統攝下的論說,它使歷來側重于體現體制聲律的“格調”不至于不如形式主義的老路,有助于促進作家提高品質修養,充實詩歌的社會內容,從而提高詩歌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
注釋:
[1]黃珅.清代學術中的性靈說[J].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第6期;
[2]袁枚.隨園詩話[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三、參考文獻
[1] 何文煥.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1;
[2]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袁枚.隨園詩話[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