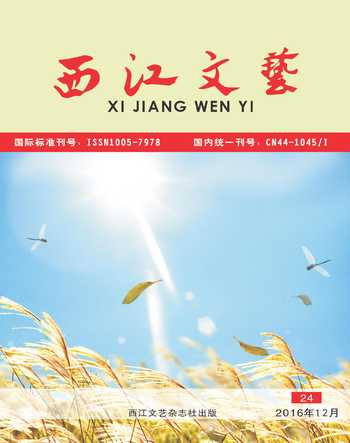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詩經》中的桃文化崇拜
陳新新
【摘要】:中國人對桃的偏愛源遠流長,桃在中國被賦予很多美好的意義。它的花葉象征著春天、愛情、美顏與理想世界。子果融入了中國的仙話中,隱含著長壽、健康、生育的寓意。枝木用以驅邪求吉,在民間巫術中得以廣泛應用,因此在文化中,桃樹是一個多義的象征體系。早期的先民認為桃是神樹的一種,對桃充滿敬畏和崇拜。桃文化底蘊十分深厚,詩經時代亦有對桃的贊美,《詩經》篇什建立了桃花與青春、女性的關系,并成為中國文學中重要的主題之一。本文著重探究《詩經》中所體現的桃文化崇拜。
【關鍵詞】:《詩經》;桃文化;桃崇拜;桃果;桃花
在《詩經》中共有六首詩出現了“桃”字,分別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國風周南桃夭》
何彼秾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何彼秾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候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候之子,平王之孫。——《國風召南何彼秾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國風鄘風木瓜》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國風魏風園有桃》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大雅抑》
予其懲而毖后患,莫予荓(ping)蜂,自求辛螫(shi)。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周頌小毖》
上述詩句中,除最后一句“桃蟲”是指鷦鷯鳥外,其他均把“桃”作為客觀的表現對象,可見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桃夭》一詩,《毛詩序》說“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1]“后妃所致”,“不妒忌”及“國無鰓民”云云,顯系牽強附會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的說法,倒是與全詩的內容和意境較為接近。今人一般認為,這是一首輕快活潑、熱情洋溢的祝婚詩。詩的首章,詩人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用鮮艷的桃花隱喻經過梳妝打扮的美麗新娘,的確有一種“人面桃花相映紅”的韻味。詩的次章,詩人以“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作遞進式的比興。《毛傳》:“蕡,實貌。”[2]《玉篇:“蕡,草木多實。”[3]指草木果實繁盛的樣子。“有蕡其實”明著是按桃樹先開花后結果的生長規律敘寫桃子的繁多,實則暗示了對新娘婚后多生子女的良好祝愿。古有多子多福之說,詩人恐怕正是借桃樹的果實繁多這一意象來表達了自己發自內心的祝愿。詩的第三章,則以“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作比興,明著是寫桃樹的枝繁葉茂,實則暗含桃樹壯大、根深葉茂之意,喻示了新娘出嫁后使夫家的家族興旺的前景。另外我們還應當注意到,“葉”與“業”諧音,因而茂盛的桃葉這一意象也容易使人聯想到家業的發達。總體來看,詩人以桃樹為整體意象,以花、果、達。
互送桃果或其他水果是當時青年男女表達愛情的一種方式,甚至是選擇對象的一種手段。聞一多認為,《木瓜》和《摽有梅》二詩,其實是年輕女子在某一節日中尋找意中人的真實記錄,他指出:“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時,會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投其所悅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報,即相約為夫婦焉。”[4]因此,“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清楚地表明,投物定情是達到“永以為好”(即婚姻)目的的必要手段。《摽有梅》則是通過女子向男子拋的梅由多至少的過程,表達了這位姑娘渴望在節日中找到意中人的迫切心情。從詩中來看,當時的習俗似乎是:一方要先向另一方拋擲水果(桃、木瓜、李等),而對方則多贈之以玉佩(瓊琚、瓊瑤、瓊玖)。如此看來,“桃”等水果是作為愛情的信物和獲得愛情的一種手段,這里出現的桃體現了其在愛情與婚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園有桃》一詩,詩中寫道:“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下與第一段同)。一般認為這是寫士人“處于困境,嘆息知已難得”[5]。
而《周頌·抑》中的“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與上述解釋類似,皆是作為一種交換的禮物。而《何彼秾矣》中的“何彼秾矣,華如桃李”句,《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一引鄭玄語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據《辭源》‘秾為“豐腴貌”,是對桃花擬人化的描寫,既突出了桃花之色盛,又顯現出桃花之態美,這是古人樸素的審美。
由上述材料可知,《詩經》中關于桃的記載多集中在它的花與果實上,桃的文學意義初顯。至詩經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已漸提高,對桃的著眼點不再僅限于其實用價值,而是開始轉向審美領域,這是桃文化崇拜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變,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言:“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詠美人之祖。”這樣,桃花就又具有了女性青春的內涵,桃花與女性的關系由此建立起來,成為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桃花與女性的主題原型。開啟了桃花文學的濫觴。漸漸地,“桃花文化”成為非常普遍的一種文化現象。
桃文化的分支之桃花文化的發展在歷史的演進中不斷豐富,在古代詩文中,寫春景、寫女子,大都離不開桃花的點綴、渲染和比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鑒賞辭典》和《唐宋詞鑒賞辭典》,收人523位詩詞家具有代表性的2623首詩詞,開卷觸目,多是“桃花”點點。民間吉祥喜慶活動,特別是戀愛、婚姻這類人生喜慶之事,有‘尚紅”的習俗,如相思之紅豆、牽姻緣之紅線、作媒之紅娘、題詩之紅葉。桃花是紅色的,飽含爛漫的春意,便常常被作為比喻、象征來引用,“桃之夭夭”,指桃花之艷,更喻女性之美是后代桃花文學的始祖。
桃文化崇拜在發展演變中逐漸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桃花漸漸代表著中國女性的悲慘命運,‘桃花文化”最悲慘的一幕,是集中國文化之大成的《紅樓夢》。
曹雪芹獨為黛玉安排了葬桃花的情節,一位命運最悲慘的女性和一種命運最不幸的花木被獨具匠心的安排在一起。她掩葬了桃花的殘花落瓣·為桃花也為自己堆起了一座芳冢。她泣淚吟著“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詩句,未待自己的青春消逝就與桃花一同魂歸黃泉。
由桃文化衍生的“桃花源”是中國文化中的經典。桃花源是人們理想社會的縮影,陶淵明代表文人構擬了這種社會圖景,“晉太和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描寫了一個只知秦漢、不知魏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剝削、無賦稅的桃花源。這一理想生活的模型,在后代詩人的詩作中不斷被描寫。這都是桃文化崇拜在不斷地演變過程中的逐步豐富內涵和壯大的體現。
結語
《詩經》篇什標志著桃花文學意義的初露端倪,桃花與青春、女性的關系也成為中國文學傳統中重要的主題之一。因此,研究《詩經》中的桃文化崇拜有利于我們更好的研究桃文化崇拜的源頭,為桃文化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材料和證據。
注釋:
[1]十三經注疏【M】.杭州:浙江占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頁。
[2]同上。
[3]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Z】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7頁。
[4]聞一多《詩經新義》,轉引自袁愈姜《詩經全譯》第29頁。
[5]袁愈姜《<詩經)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頁。
參考文獻
[1].〔英〕詹·喬·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M].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
[2].王焰安.桃文化研究[M]香港: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
[3].[清]方玉潤.李先耕校.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4].王衛東.桃文化新論——桃文化與上古巫文化[J]云南民族學院報.1999.7.
[5].王焰安.桃文化衍生試論[J].江西社會科學,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