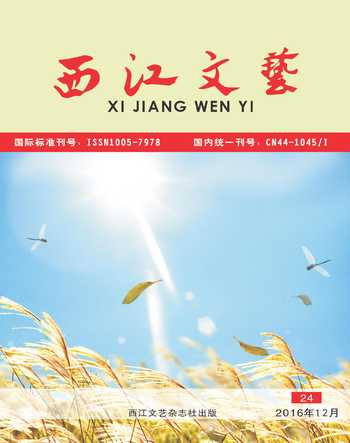淺析塞萬提斯與《堂吉訶德》主人公形象關系
徐夢琪
【摘要】:塞萬提斯是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堂吉訶德》是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文學作品的代表作,也是歐洲小說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作品。《堂吉訶德》中塑造了一個崇尚騎士道精神、復雜而矛盾、思想和行為極其荒誕的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形象。而塞萬提斯個人的經歷與堂吉訶德這一人物形象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說這個經典人物形象中滲透著了些許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與意識。本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介紹:一、品質——勇敢、堅毅的英雄氣概。二、識見——獨特、深刻的真知灼見。三、情感——主張平等、揭露社會現實。
【關鍵詞】: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文藝復興;人文主義
塞萬提斯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作家,他是遭遇磨難最多的作家之一。塞萬提斯從小由于家庭生活困頓,跟隨父親過著東奔西走的生活,后來作為紅衣主教的隨從,前往多地進行游歷,正是動蕩的生活讓他有機會了解西班牙社會所經受的文藝復興的影響,從而接觸到了人文主義思潮。他為了謀生,曾做過各種職務,還因許多原因入獄,這些豐富的生活經歷,讓他飽嘗人間冷暖,歷盡世態炎涼,也正是這些特殊的人生體驗讓塞萬提斯有機會接觸下層人民,目睹到當時社會的黑暗與貧民的疾苦。塞萬提斯的這些經歷讓他重新反思歷史,通過文字表達他想要實現的理想社會,他將60年的貧苦生活遭遇融合在他的著作《堂吉訶德》中,而從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形象中,也可以折射出作者本人的身影。
一、品質——勇敢、堅毅的英雄氣概
堂吉訶德沉迷于對騎士小說的英勇情節的幻想中,將現實生活設想為小說中的描寫。他把風車當作巨人,把羊群以為是兩支軍隊,把客店看做是富麗堂皇的堡壘,把裝紅酒的皮囊當作是巨人的腦袋,思想和行為上的荒謬讓他不僅沒有通過自己的游俠行為復活曾經的騎士制度,改造社會、主持正義,反而讓他受盡嘲弄、譏諷、甚至遍體鱗傷,看過他的人就會覺得簡直是一個行為荒唐不可理喻的瘋子。但是這個“瘋子”是值得敬佩的,他生活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人,利己主義在他身上完全不能發現。他經歷了無數次失敗卻還對他的可貴理想的實現抱有堅定的信念,他用他的生命來捍衛他心中的正義感,堅持他內心的信仰。堂吉訶德大戰他以為的風車巨人時單槍匹馬的英勇,在路上遇到運送獅子的車時也是毫不畏懼地想要與獅子進行一番搏斗,即使被風車卷下馬匹,或是被牧羊人用石子打掉半邊牙齒,挨自己解放的囚犯的痛打,他依然一片熱忱奉獻于他鋤強扶弱的騎士事業中,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讓他不再是那個滑稽可笑的瘋子堂吉訶德,而是一個值得同情與稱贊的勇士堂吉訶德。正如英國作家毛姆所說:“他是人類奇想的不朽產物,任何一個心地善良的人都會被他深深地打動。”
作者塞萬提斯1570 年棄筆從戎,參與基督教國家聯合艦隊重創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戰役,即使當時身體狀況不佳,但他奮不顧身第一個跳上敵艦,因此他失去了他的左臂。但是塞萬提斯一直將參與這場戰役引以為傲,直到晚年,他還感慨:“我的胳膊是在從古至今最偉大的一場戰役中殘廢的,假如我定有回天轉運的本領,對過去的事可以重新選擇,我寧愿傷殘了身體,還是要參與這場驚天動地的戰役。”[1]這與堂吉訶德在大戰風車巨人時的勇猛與奮不顧身是有著相似之處的,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在小說中是無所畏懼的,這般膽量和英雄氣概是作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想要賦予給堂吉訶德的英勇品質。塞萬提斯被土耳其海盜俘虜,在阿爾及爾做了五年奴隸,他曾多次帶頭逃亡擺脫他殘暴的主人,但是事情失敗后,他總是獨自承擔所有罪責,被罰以酷刑也絕不供出自己的同謀,而他的主人卻也因他的敢于擔當的氣魄和出人的膽量沒有凌辱他。塞萬提斯將自己的這段經歷融合穿插進了《堂吉訶德》中,戰俘上尉講述自己被俘虜的過程其實就是塞萬提斯將自己的經歷寫了進去,因此,塞萬提斯在創作這篇小說時,不完全是憑空虛構的,有一定部分是他自己的品質的體現和經歷的再現。他想通過堂吉訶德這個形象表達自己的英雄情懷,將堂吉訶德構筑成為一個具有英雄氣概的具有正義感,堅持維護自己內心道德與信仰的騎士形象。
二、識見——獨特、深刻的真知灼見
堂吉訶德只要不談論到騎士道,他是一個頭腦清晰、能言善辯的人。堂吉訶德能夠出口成章,在談及文武官時,他可以舉出諸多例子和運用多種方法來論證武職的可貴,將拿“槍桿子”的不易頭頭是道地表述出來。同樣在談及詩歌創作方面,堂吉訶德也能一五一十地有所講述,論教育子女和論翻譯,他也能條理清晰地表述,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作者總是通過侍從桑丘表現出的贊賞和欽佩來側面表達堂吉訶德見解的深刻性與正確性。他還在卡麻丘與季德麗亞的婚禮上幫助巴西琉調解,使得巴西琉奪回了自己的真愛還免受卡麻丘的報復,因為他贊同尊重婦女,主張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在桑丘即將赴海島任命總督時,堂吉訶德對桑丘多加囑咐,“你不能只聽富人的申說,該看到窮人的眼淚,可是也不能存心偏袒。[2]”“你執法而手下留情,不要是因為受了賄賂,應該是出于惻隱之心。[3]”這多達兩章對于桑丘的叮囑與告誡,表明堂吉訶德是一個深諳做一位盡職盡守,為民做主的清官之道的人。堂吉訶德堅守內心對于意中人杜爾西內婭的忠貞想法,面對阿爾迪西多拉的主動求愛可以做到坐懷不亂,而且他據此還對美做了清晰的闡述:“美有兩種,一是心靈美,一是肉體美,聰明、誠實、正直、慷慨和彬彬有禮都是心靈美的表現,而且丑陋的人也可以具備美的這些方面,如果一個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心靈美,不計較肉體的美丑,那么由此產生的愛情會更加堅定,更加真摯。”[4]這番話不論是對于過去還是現在或者未來,都是值得深思并銘記的一段話。由此看來,堂吉訶德是一位極有文化內涵的人,是一位文雅的學識淵博的學者。
但是,在小說中也不難看出,塞萬提斯對于某些事情的言論是借堂吉訶德之口說出來的。塞萬提斯因較早的游歷生活,接觸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主張追求人的自由,享受人的權利,反對君權與神權。堂吉訶德故意將那些犯了罪的囚犯釋放,是因為他說“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當做奴隸未免殘酷”,他對于美麗少女瑪賽拉的選擇表示支持,并警告那些有意侮辱她的人要敬重這個少女,讓她自由自在地享受牧羊女的生活。而面對公爵夫婦的款待與富麗的城堡,他都不為所動,直覺得像是一座牢房,從城堡中離開后,他大呼:“自由是天賜的無價之寶。”這些話語都表現了堂吉訶德追求自由的生活,是人文主義的表現。這些都與作者塞萬提斯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有關系,作者是有意識將自己的一部分才識與見解滲透于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形象中,使這個形象能夠更傳神地表現作者想要描繪的理想生活,能夠更貼切地閃現人文主義的光輝。
三、情感——主張平等,揭露社會現實
《堂吉訶德》通過主仆的三次游俠出行,展現了16世紀至17世紀西班牙廣闊的社會場景,暗示了當時西班牙社會危機四伏的實質。小說中通過寫各個階層的七百多個人物,展現了當時社會不同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刻畫了客店老板一家以及仆人和騾夫,還有一心向往自由的牧羊女,淪為囚徒的百姓,鞭打牧童的財主,想要救贖堂吉訶德的神父,喜歡戲弄別人的公爵夫婦等等惟妙惟肖的形象,揭示了當時西班牙社會各階層不平等的情況,并用諷刺的手法抨擊了當時上層統治階級生活的腐敗,也表達了對于平民階層的同情。小說中特意描寫了卡麻丘婚禮時的大擺筵席,“可以供一隊士兵放量大吃。”“燒肉的砂鍋,一鍋能吞掉屠宰場上所有的肉。”而代表上層階級的公爵夫婦一家,閑來無事以戲弄堂吉訶德和桑丘為樂,不惜花重金設置場景,制作各種怪異的服裝,甚至還特意找仆人來扮演角色,樂此不疲。官宦人家享盡榮華富貴的時候,卻有貧苦人在為生活所困。堂吉訶德在趕路中遇到因為窮困潦倒而去當兵的年輕人,李爾德一家因為被驅逐找不到安身之處,樹林中因要工錢而被財主吊打的小男孩等等,中下層的人們在承受著生活拋給他們的苦難,貧富差距令人觸目驚心。
堂吉訶德通過他的俠義行為鋤強扶弱,盡管很多場景是他自己幻想出來的或者他的有些行為甚至適得其反,但是他所有的行為都是發自內心的善意,比如他去樹林幫助小男孩,他的主張便是人人平等,財主沒有權利這樣對待這個孩子。雖然堂吉訶德在有些時候是瘋癲的,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荒唐至極的,但是他內心的情感是他要保護那些弱者,不能讓有權勢的人欺侮下層人民。正是這樣,堂吉訶德雖然瘋傻,但是他可以意識到社會是有問題的,是需要人來挽救的。而作者本人對于社會黑暗與統治者的專橫是非常氣憤的,他筆下的西班牙社會,是一個壞人當道,好人遭殃的“可惡時代”[5]。塞萬提斯是憎惡這種專制制度的,對于種種不公正待遇有強烈的不滿,而堂吉訶德正是和他有著一樣情感的形象,也有著不畏強暴,掃盡天下不平的理想,作者也將自身情感分割了一部分組成了堂吉訶德的人物形象。
《堂吉訶德》是塞萬提斯深厚的情感積累與豐富的特殊生活經驗的作品,他通過這部作品破除了當時的人們的騎士小說的沉迷,同時這部著作還具有更加深刻的內涵與意義。塞萬提斯創作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可能不是有意識地取材于他自己本身,但是堂吉訶德這個形象確實是與塞萬提斯本人有著密切聯系的,并且堂吉訶德擁有的部分品質、識見與情感是從塞萬提斯自身所分衍出來的。通過《堂吉訶德》這部作品,塞萬提斯揭示了當時社會的尖銳矛盾,也讓人文主義思潮更加深入人心,從而讓這部作品充滿豐富的文化內涵。別林斯基曾說:“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時代的人民,都一定要好好地讀一讀《堂吉訶德》。”經典作品隨時間的流逝會愈發顯現它的可貴,堂吉訶德現在是也將會一直是一個永遠前進的典型人物形象。
注釋:
[1]崔秀蘭,蔡敏. 單純的堂吉訶德與復雜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寫作動因初探. 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7年第25卷第3期.
[2]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87
[3]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87
[4]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87
[5]成良臣. 論《堂吉訶德》的人文主義思想傾向. 達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1年第1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