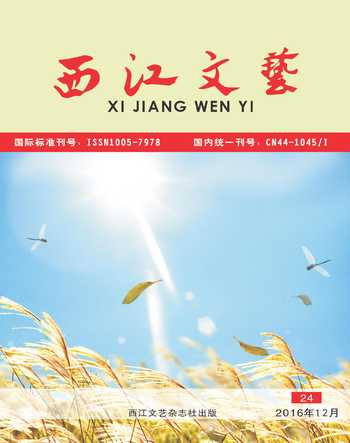錯到底,作為前車之鑒
陳玲
一個情字了得年輕的我,拋棄浙江大學的工程學習,寧愿降班,轉入了杭州藝專。從家庭的貧窮著眼,從我學習成績的優異著眼,從謀生就業的嚴峻著眼,所有的親友都竭力反對我這荒誕之舉。我當然也顧慮自己的前程,但不幸而著魔,是神,是妖,她從此控制了我的生命,直至耄耋之年的今天。
——吳冠中
去年曾無意中在微信上看到一篇關于吳冠中先生的推送,很美的散文詩:
細雨如織,細數回憶的時間,
似乎也變得很長很長,如同從未斷線的雨絲,無止無休。
在冬天之末,春天之始,手捧一片新綠,
眼前的黑瓦白墻,也似乎生動了幾分。
。。。。。。
下雪了,我們曾相約一起看雪,最后卻都食言了。
樹上掛滿了白色的花朵,這樣的冬天,好像會魔法。
銀裝素裹的世界里,只有這裊裊而起的炊煙,帶著生命一些活力。
從入冬開始,我就期盼一場漫天大雪。湮滅過去,也湮滅回憶。
這篇名為“我把四季用來等你”的詩歌當時風靡了我的整個朋友圈,也許是文字太過煽情,也許是配的吳先生的畫作太令人癡迷。可再細看時,發現好像又有些不太對勁:墨點與線條似乎都很刻意,畫面也太過復雜,顏色過分艷麗......后來我又對比了吳先生的一些畫作,如《網師園》:蘇州四大名園之一,雖規模不甚龐大,設計卻是極佳,曲折而雅致,素淡而恬靜。吳冠中多次故地重游,如訪舊友,更是從中提取多幅畫圖。八十年代,正是吳冠中畫作由色彩向水墨,由具象到抽象的探索期。這件作品尺幅巨大,是吳冠中在這一重要時期,'一切景語,皆情語之力作。黑瓦白墻江南清韻作品采用黑、白、灰三種基本色主導,統領畫面。以大塊墨色寫就黑瓦屋頂,以富于律動的淡墨線條畫出窗欞、曲橋、山石與池塘,留下寧靜的天空與白墻。寥寥數筆,江南清麗娟秀的情調便躍然紙上。古樹崢嶸虬枝張揚如果說黑白灰三種基本色,所描繪的房屋、天空與池塘,橫向的分割了整幅畫面,形成靜謐的氛圍。那么這份靜謐就是背景,是陪襯。所襯托的,是畫面正中四棵身軀碩大、姿態各異的崢嶸古樹。古樹一棵伏臥,身如巨龍;三顆挺立,或伸展,或虬曲,直上千仞,頂天立地,像大夫,像將軍,像神話中的天神。力爭上游的張揚線條,性格倔強,生命頑強,爆發出畫面的最強音。又如《交河故城》,用極為簡略的手法,將故地的自然地貌、城市風情展現在人們面前,顯得端莊、沉靜,充滿了從容不迫的大氣度。在色彩的使用上,吳冠中同樣做到了既簡約、又精確,畫中色彩既少且淡,但山頂城堡的一抹夕陽,畫面左下方的一方印章,巧妙地使整個畫面達到了完美的平衡,天空的淡綠則調和了整個城市的淡紅色,使畫面充滿生氣。眾人才恍然,所謂的詩歌,不過是借用吳先生的名聲造的一個噱頭而已。
這位被譽為中國畫壇的最后一位畫師,自新時期以來,吳冠中是突破美術僵化模式的先鋒,是中國美術走向現代的旗幟。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西方現代主義是中國美術界擺脫禁錮、爭取創作自由的有力參照。吳冠中作品中獨有的唯美意識,對長期不講審美、只講政治的中國美術,產生了強烈的批判意義,也最先具備了前衛傾向。1978年,中央工藝美院為他舉辦回國后的第一次個展,第二年,中國美術最高圣殿——中國美術館為他舉辦個展。他強化形式的風景油畫,與流行的深刻社會主題完全絕緣,令人耳目一新。該展覽在北京結束后,又受邀到多個省份巡回,他本人隨展覽到各地舉辦講座。
這是為吳冠中全集第九卷《吳冠中談藝錄》所寫的前言:
“從一開始吳冠中就不是真正的形式主義者和抽象主義者,在前面所引的留學考卷中他對明清山水畫‘趨向形式,徒有軀殼,而缺乏靈魂,就持批評態度。其實明清畫家對形式獨立價值的興趣,很可能是中國畫現代轉型的契機,只可惜西方古典寫實畫風襲來,中國藝術于另一種擬古中討生活,不論向東向西以及東西結合,都只能在為當前政治服務的桎梏中極其緩慢地行進。吳冠中及其他一些大陸畫家在風景畫中對形式的有限追求,對中國藝術的現代性過程而言,是一種連接,也是對藝術政治統治的抗議和對藝術創作自由的向往。我們很難設想,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歷和體會,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已經60多歲的吳冠中會斗膽沖破幾十年的藝術禁區,在美術界首先提出‘繪畫的形式美問題。”
吳冠中的形式理論是實踐性的,從表面上看,是強調形式美、抽象美對于美術家、對于美術創作和美術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但實際上吳冠中針對的是幾十年來政治對藝術的制約、針對的是高懸于藝術家頭上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長期以來,這種政治功利化的現實主義理論把文藝視為認識手段,把文藝反映現實生活的過程當作科學認識現實的過程,要求藝術家在這個過程中掩蓋其邏輯思維和科學推理,把現實生活的本質真實和普遍規律按照典型化原則以具體的藝術形象反映出來,使自己的作品區別于哲學和科學。這種理論一直被確認為是藝術創作唯一正確的方法,似乎藝術家只要持有這種方法,便可以達到藝術的客觀真實。但事實上,持論者在所謂典型化的過程中,著重提出了傾向性這一和真實性并不一致的要求,并以既定的傾向性代替真實性,以致文藝是客觀現實本質屬性的典型概括的觀點,導致了現實主義創作按照黨性原則來從事藝術活動,甚至徹底放棄真實性,僅僅以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為第一和最終的原則。吳冠中很敏銳地指出:‘問題的實質還在于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根據我們的習慣理解,內容是指故事與情節,多半是屬于政治范疇或文學領域的。‘我強調形式美的獨立性,希望盡量發揮形式手段,不能安分于“內容決定形式”的窠臼里。‘但愿我們不再認為惟“故事”、“情節”之類才算內容,并以此來決定形式,命令形式為之圖解,這對美術工作者是致命災難,它毀滅美!”
就他的一生而言,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美術家,就他最后三十年的杰出創造力和影響力而言,他為他的時代貢獻了所有,并且以他的思想和膽識,震撼和鼓舞了同時代的美術家。吳冠中是三十年來少見的具有文學情懷的中國美術家。他的“丹青負我,我負丹青”的文學情懷,在文學深度缺失的中國美術界,具有旗幟意義,是一種難得的清醒和人文悲愴。吳冠中是一個壯懷激烈的美術家。他在表達他的文學情懷的時候,甚至作出了“一百個齊白石比不上一個魯迅”這樣的判斷。然而,吳冠中心底盤旋不已的對于文學的景仰和敬畏的情感,整個美術界,又有幾人感同身受?吳冠中從來不曾輕看齊白石。他以他內心敬重的美術家去比試魯迅,這種極而言之的語言修辭,所要表達和大聲呼喚的,正是一種被中國美術界深深淡忘的文學情懷。寫了一生的文心絢爛的散文的吳冠中,他的絢爛的文心,要用絢爛的文心去理解。
就像他自己說的:“人生只能有一次選擇,我支持向自己認定的方向摸索,遇歧途也不大哭而歸,錯到底,作為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