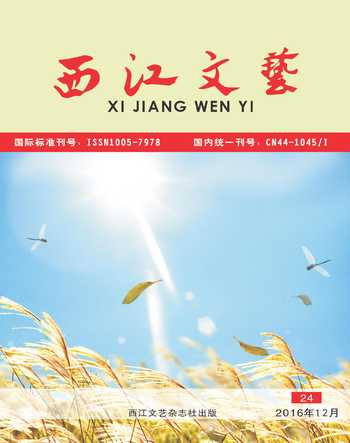喻紅——“女性”藝術創作
段敏
【摘要】:從喻紅的藝術創作,并結合中國歷史情境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出于什么理由,中國女性藝術家都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
【關鍵詞】:喻紅;中國;女性
著名女性評論家徐虹在其《女性:美術之思》有這樣一段話:“幾乎現有的一切規范制度,包括哲學、語言和圖像的建立,都是按照一種性別所設置的……”[1]。足見歷經千年封建禮教統治的中國女性和西方女性一樣處于諾克林所提及的那種男性話語權力之下的境地。中國藝術的發展中,鮮有女性藝術家,即使有也具有“附帶性”。那么中國女性將如何應對這種男性話語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是忍讓、繼續屈服還是奮起抗爭?1990年代后的新女性,“她們”正如諾克林在《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里所期盼的那般,不再去希冀完成“偉大的成就”,而是以“她”獨特的視角重新表達“女性”的藝術體會。其中喻紅的藝術創作就以體現女性個體思想而成為“她們”中的佼佼者。
喻紅的作品以表現個人情感著稱,立足于“女性”這個性別角度,并且她的繪畫生涯也始終被女性的個體經驗貫徹。喻紅的作品《玩具系列》和《目擊成長》(1999年開始)系列更是她作為“女性”“母親”這個身份做出的回應,以“她”的心態和視角來觀察和思考這些問題。《玩具系列》是喻紅成為“母親”后,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女兒玩玩具時的形態預設各種不可預知的危機,通過用玩具制造交通事故和各種危險景象來表達自己的憂慮。《目擊成長》是畫家通過反思自己成長的過程,來想像和考慮女兒的未來。這都是喻紅身為“母親”后對藝術不同的解讀,表現不同于男性的婦女經驗。《她系列》(2003年開始),是喻紅以不同身份、社會境遇和教育背景等的“女性”作為表現對象而創作的。這一系列的作品帶著強烈的真實感,將喻紅作為一名“女性藝術家”特有內心認知表露無遺。這系列的產生是因為,中國歷史語境的轉變,女性的社會地位不再是一味的被動,她們開始對本身有了強烈的“關注”,而不僅僅只是站在被“審視”的位置上,“她們”更多的想要關注“她們”本身的個體體驗,作為現代新興的女藝術家也將自己的眼光放置于社會各個層面的女性身上,這也就是喻紅《她系列》突出凸顯的主題。
迄今為止,喻紅的個人藝術創作總體來說已經取得了莫大的成就,甚至在如今時代已在一定領域達到耳熟能詳的程度。在諾克林那里的女性藝術家通常只有在與她們的父親或親密的人中才會取得成就;到了喻紅這里,已經有很大改善了。喻紅以她自己的藝術價值,而不是她丈夫——著名中國當代藝術家劉小東——的支持而存在,可以說,她們已經不需要男性支持堅定的站在那里。在這里筆者雖未對喻紅的繪畫總體作個梳理或說明,只是選擇性的加以引用。
喻紅的藝術創作是否受到劉小東的影響?為什么會在這里詰問這樣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在中國女性藝術家的潛意識中,“‘從男性話語模式中分離的觀念往往使她們感到惶恐”,[2]女性藝術家對這種狀態基本上是默許的。想要成為“偉大的女性藝術家”,想要改變父權統治的藝術世界,就如穆勒曾說的:“一切尋常的事看起來都自然,女人服從男人是一個天經地義的習俗;改變這一點便很自然地顯得不自然。”[3]這便是從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機制方面來對待性別差異問題。所以說,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值得深慮的,同時答案又是顯而易見。
筆者認為隨著自由化和開放性,給予了“女性”更大的包容度。女性藝術家是否受到與之親密的男性藝術家的影響的程度已不那般強烈了呢?對于同樣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活躍的劉小東和喻紅夫婦是怎樣體現這樣一種關系呢?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劉小東的作品主題集中在他的生活和他在現實中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在褒揚貶抑上把握了一種分寸,喻紅在其藝術創造上也秉持了這樣的傾向。在“他”和“她”的藝術之間,要談論是“他”影響了“她”嗎?喻紅自己給出的答案是這種影響是相互的,基于二人的教育、工作背景及個人經歷的異同,她認為盡管二人在傾向上是一樣的,可是由于“男女之別”使得“他”對人在社會上、社會的變化更關心,“她”對人、對個人內心的關心更強一些。這也是新時代的女性藝術家對“女性”的重新解讀所做出的努力。
在劉小東和喻紅相處的過程中,或者二者的藝術創作上,據喻紅自己來講是相互影響,平等相處的。盡管喻紅的藝術創作或多或少受到劉小東的影響,這種“影響”也不至于像以前那樣是侵略性的。最起碼,在某種方面來說,喻紅自己作為“女性”也用自己的藝術價值證明了自己的不同于男性的體驗。然而,這并不否定女性藝術家藝術活動環境的復雜性,比如1995年的“丈夫提名展”,意味深長地展示了這些女畫家們“戀家”的各種表現形態。所以說,盡管有很多像喻紅這樣在男女關系上算是“平等”相處了,也無法否定“男女平等”往往停留在口號上,只是一種教條。
喻紅等女性藝術家就用自己的藝術創作為“女性”開辟了一隅。誠然,她們的作品談不上成熟,還有部分局限的地方,但是她們正在不斷地去實踐。所以筆者認為,給予女性畫家更多的關注和機會,給予女性繪畫充分的話語權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參考文獻:
[1]徐虹.女性:美術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廖雯.女性藝術—女性主義作為方式[M].吉林美術出版社,1999.
[3]John Stuart Mill:The Subejetion of Women(1896),in Three Eassys by John Stuart Mill Worlds Classics Series,London, 1966
[4](美)琳達·諾克林等著.失落與尋回—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M].李建群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