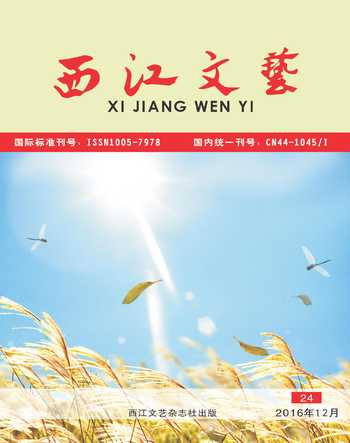試析男權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幸福觀
高勝艷
【摘要】:男權主義社會中,女性自身的生活體驗和價值觀往往被掩蓋和曲解,擱置在大的文化背景中,女性的的幸福觀由男性來界定并掌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的幸福多被框定在愛情與婚姻中,其實這是畫地為牢,是狹義的幸福觀和潛在的男性中心意識。幸福是個人化的、私有的,女性最大的幸福在于決定自己的命運。
【關鍵詞】:男權主義;女性幸福觀;男性中心意識;女權主義
一、曲解: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幸福觀
幸福始終是全人類的共同渴望和永恒價值,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幸福是生活的目的和意義,是人類存在的至上的目標。在談論女性幸福觀之前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全新的基點,以往我們總是無意識地把這個問題放在既定的社會背景中去討論,得出的結論也就大同小異。要真正理解女性的幸福,我們必須放棄一貫的男性視角,跳出當下的社會背景,把女性當作獨立的個人,通過女性自身的經驗和價值觀來理解其生活和需求。
首先要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對于幸福的理解存在很大的性別差異。男性視角下的幸福多與物質、金錢、事業的成功有關,幸福要靠自己主動爭取,要靠不斷地奮斗,另外,給心愛的女人以幸福也被囊括在男性的幸福準則之中,換句話說,男性通過扮演救世主或者英雄的角色來提高其幸福指數。而女性的幸福觀并非如此,她們的幸福多與感情、奉獻、家庭有關,尤其是在中國,家庭更是占有很大的分量。排除個別的拜金女,大部分女性認為,只要和心愛的人在一起,吃苦也是幸福的,她們愿意與愛人共同拼搏,創建屬于兩個人的幸福。“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聲有多甜;幸福不是你能開著多豪華的車,而是你開著車能平安到家;幸福不是聽過多少甜言蜜語,而是在你傷心的時候能有人對你說:沒事有我在……”[1]這才是對女性幸福觀的真實寫照。與男性相比,女性的占有欲要弱的多,因而她們更容易滿足,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渴望的是“小幸福”,一枚大大的鉆戒不見得比一杯她傷心時送上的熱茶更能打動她的心。從女性的角度講,“我在意你”或者“我需要你”的分量要遠遠勝過“我愛你”。
但在當今的男權主義社會中,對幸福感知的性別差異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在關愛弱勢群體的旗幟下,女性扮演者幸福接受者的角色,這甚至成了默認的社會道德。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正是這樣的角色定位,掩蓋了女性的個人價值,剝奪了女性被需要的權利,其實“被需要”本身就是一種幸福。男性在回答女人對社會的貢獻時,強調的是助人、輔佐的特性,尤其和家庭分不開。在男權主義社會中,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財產,或者附屬品,“男人常常說起話來好像他們擁有女人的身體,像是討論汽車或音響一樣對女人評頭論足——如同為買主提供購物清單”。[2]這樣,在男性中心意識下,女性自身的生活體驗和價值觀往往被掩蓋和曲解,發言權被剝奪,社會從男性視角來解讀并定義了一個時代的幸福,其中女性的幸福觀充其量算是男性幸福觀的附屬品。女性的幸福由男性掌控,體現的是一種潛在的男性霸權主義,就如同“女士優先”的口號本身就帶有貶低女性的意味,是對男女不平等的默認。
有學者提出當今社會出現男權主義削弱,女權主義復蘇的趨勢,壓迫女性的現象不復存在,相反男性更多地受到不平等待遇。但這一觀點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因為在經濟領域男性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這就決定包括政治、歷史、文化在內的一切領域都由男性來掌控。因而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男性是主動的,靠實現自己的價值來獲得幸福;而女性是被動的,只有依附于男性,憑借男性的成功來標榜自己的幸福,并且這種幸福還是在男性話語霸權下的幸福。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社會文化背景,尤其在中國,社會對男女各自的角色扮演有著嚴格的規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為男性塑造的是頂天立地的英雄角色,代表權威;而女性要遵從“三從四德”要甘于為男人、家庭和社會做貢獻,基本上沒有自我概念的存在。因而,為了達到男女在幸福觀上的平等,我們要喚醒女性的權利意識,把她們從男權主義中解救出來,還原成獨立的個人,賦予她們話語權,讓她們自己闡釋什么才是“女性的幸福觀”。
二、囚禁:婚姻設定女性的幸福標準
女性幸福的標準是什么?2010年3月份,一部名為《老大的幸福》的電視劇給出了答案,該劇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異、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各不相同,她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前廣闊的社會內容和當代女性的生存狀態及精神面貌,同時該劇將女性幸福的標準設定在婚姻愛情中,換言之,該劇認為一個女人幸福與否,主要在于她是否擁有甜蜜的愛情、美滿的婚姻以及和睦的家庭。因而女性獲取幸福的唯一途徑在于取悅男性走進婚姻殿堂,至于通過事業實現人生價值獲取幸福永遠是男性的特權。劇中,為自己的事業打拼的女性辛雯在其中是一個非常可憐和辛酸的角色。該劇,提出這樣的觀點,女性追求幸福的過程就是尋找感情歸宿的過程,而家庭往往可以給予女性情感上的安慰。
對中國而言有著異常神圣、嚴肅、莊嚴的信念不是個體,而是由個體組成的家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初級群體,家庭是一個絕對的整體,而家庭成員尤其是母親只具有相對的道德價值。三從四德的教條讓女性在家庭中扮演奉獻者、犧牲者的角色。女性的幸福與家庭、家族聯系在一起,中國傳統婚姻的本質是傳宗接代、香火永續。因而家族的延續對實現女性的幸福是至關重要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女性作為工具的價值要遠遠高于作為一個獨立人的價值。[3]
三、掌舵:女性最大的幸福
有關幸福的定義有很多,諾貝爾獎得主Daniel Kahneman在《重新定義幸福》中指出,幸福包括:整體的幸福感;積極的人格特質;積極情緒;愉快的感覺。心里學家Ed Diener則言簡意賅地指出,幸福就是生活滿意度高,積極情緒多而消極情緒少。從這些定義中可以看出,幸福是個體對自身及環境的滿意,既包括瞬間的快樂感受,也包括長久的意義體驗。所以幸福是個人化的,并且“任何一種生活都有它的快樂和悲傷,你不能用一桿秤,一把尺子,給幸福一個刻度,在此之上就是幸福,否則就是不幸。”[4]
同樣女性的幸福也是如此,沒有標尺,沒有刻度,是對個體自身和生活環境的主觀感知。并不像男性視角下所說的那樣,女性的幸福可以由男性給予,可以用于交換。女性的幸福也不應該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所羅門的故事早就告訴我們:女人的幸福在于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說,要真正實現女性的幸福,首先要把女性視作獨立的個人來尊重,具體講,是指女性有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定義幸福的話語權,并且在幸福的追求方式上有自由選擇的空間,有權控制自己追求何種幸福。
讓女性獲得屬于她們的幸福,從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放置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在男權主義社會中著手去做卻不是一件易事。但我們不能知難而退,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有擔當社會醫生這個角色的義務,有倡導實現全方位男女平等的責任,要引導女性改變在目前這個社會結構中的無權力狀態,喚醒她們爭取個人幸福的意識,促使她們采取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境遇,進而把握自己的命運,幸福的獲得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參考文獻:
[1]竇東徽,樊富珉.當今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幸福觀和成功觀[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11(1):14-16.
[2]雪兒·海蒂,林瑞庭,譚智華.海蒂性學報告(男人篇)[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9:94-97.
[3]蔣穎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幸福觀[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1,11(1):18-20.
[4]米江霞.德育的靈魂:成就人生,實現幸福——亞里士多德幸福觀啟示[J].Value Engineering,2011,34(3):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