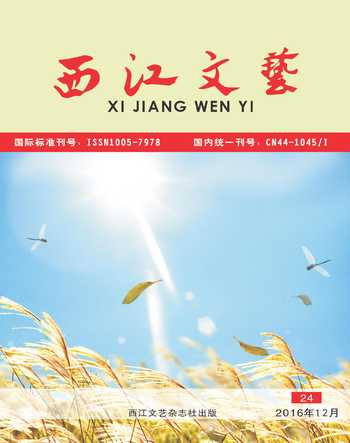從宋代花鳥畫談宋人審美趣味
李忻桐
【摘要】:中國的花鳥畫經歷了漫長的醞釀及發展,宋代成就了花鳥畫創作最繁榮的局面。宋代花鳥畫以其精深的美學內涵,高貴華美的風格,精研慎密的構思,來展示其特有的人文精神。中國繪畫自宋以來的精神淵源離不開釋家與道家靜觀無為、心領神會的思想傳統,宋代花鳥畫則處處滲透佛家注重內省的喜悅,并與儒家的現世思想發生微妙的交接,兼具感官認知與積極入世的特質。在宋代花鳥畫中蘊含了封建社會后期新的審美意識、審美風尚和審美理想,通過對宋代花鳥畫審美意蘊的探索,趣研究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
【關鍵詞】:宋代;花鳥畫;審美趣味
在宋代文人眼里,天地之物不只有聲色之美,更關乎人生之道,人們可以從自然審美中獲得理性智慧。由于宋人崇尚自然,倡導秩序,講究洗練,提倡美學,追求規范,這些觀念體現在花鳥畫上就使之呈現出各種不同韻味的美,也體現了宋人各個時期獨特不同的審美趣味。
一、華美濃麗 富貴雍穆
北宋前期,花鳥畫延續著五代寫實風格,以充滿富貴氣息的宮廷院體花鳥畫風為主,而且當時以溫庭筠和韋莊的詞風為典范,極具宮廷貴族審美趣味的詞風富貴奢靡,于這種奢華典雅的詩詞之風相呼應的繪畫審美觀念,也影響著宋人審美趣味所在。宋初花鳥畫雖受到宮廷貴族們的重視,但在花鳥畫的創作風格方面,僅限于來自西蜀的黃筌父子一派,同時黃家花鳥富貴氣象的畫風成為宋初畫院評定藝術優劣的藝術標準,體現出了院體畫審美理想的傾向性。院體花鳥有嚴格寫實要求和勾勒填彩畫法為主,但又更加細膩、華麗、柔媚、精美,是以形似為其主要特征,畫面設色濃艷富麗,充滿貴族氣息,恰好迎合了宋代皇室貴族們的審美理想。
宋代花鳥畫中所描繪對象多寫禁御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從而形成了造型準確、畫法嚴謹、色彩鮮艷、富麗堂皇、裝飾意趣濃厚的特點,黃筌的《寫生珍禽圖》畫麻雀、山雀、鹡鸰、白頭翁等十幾只鳥,蟬、蚱蜢、蜜蜂、天牛、蝗蟲等昆蟲,還有一大一小兩只烏龜,所畫形象都逼真傳神栩栩如生。在畫法上勾勒填彩,墨線的勾勒與色彩的渲染渾然一體,精彩體態呼之欲出,禽鳥蟲草的造型與刻畫無不體現為一絲不茍的寫實精神。蟲鳥的身子多取安詳的側面,神情端凝典雅,宮廷貴氣充盈全篇,八只鳥的側面姿態和翅膀的收攏舒展,形態各異,極盡微妙的變化,看似不經意的寫實手法,梳理出鳥兒周身毛羽極其有序的質地,既賦予翎毛輕盈的韻律感,又賦予用筆的韻律感。這種繪畫特征,流露出了宋人對這種富貴風格的審美傾向。
以帝王天然的雍穆氣度,趙佶遠承“黃派”的富貴畫風,將之推向極致。《芙蓉錦雞圖》歷來被看作趙佶富貴風格的重要作品之一。錦雞的神態高貴端莊,造型取其漂亮的背部,毛羽和尾翎上的斑紋排列都極具裝飾美感,而芙蓉花低垂側背的形態,使芙蓉花表現出含蓄內斂的氣質。畫面中富麗濃艷的特征,與黃家畫風一脈相承。趙佶以頭戴峨冠的錦雞來隱喻君子的德行、封建禮儀道德的標準,儒家重視文武之道、仁義之道、誠信之道和諧統一的美學境界。
二、清新野逸 自然樸素
北宋中后期伴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思潮的星期,藝術風氣與審美趣味出現了轉變,詩詞之風與繪畫審美之風的求新尚革的精神,引起了宋人新的審美趣味的轉變。此時的宋代花鳥畫在創作上氣勢野逸,清新自然,從根本上改變北宋前期花鳥畫壇華麗畫風。《宣和畫譜》指出:“祖宗以來,圖畫院之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1]有工有寫,活脫清新,瀟灑清麗的審美趣味其影響遍及于畫院內外。因此,花鳥畫在創作上既要符合花鳥畫的自然造化,又須得花鳥天真自然之趣。趙昌、易元吉的花鳥風格,及其后出現的崔白、吳元瑜的畫風,即體現宋代“理學”中“窮理”及“格物致知”的精神,極大的體現了宋代花鳥畫中對自然生命賦予人的情懷,更加盛行這種自然樸素的審美趣味。
影響宋代花鳥畫壇野逸之風的首當徐熙。徐熙專供花鳥魚蟲、竹木蔬果,即“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形容所能及也。”他在描繪物象時不僅追求單純的形似,而是更加注重對象的神似。徐熙所畫的《豆花蜻蜓圖》更是其野逸之風的代表。畫中蜻蜓造型斗滿,背部與腹部的結構經墨色分染后,產生毛茸茸的視覺效果。這對翅膀的渲染,虛實得體,白粉復勒主翅膀,用筆極其細膩,輕盈靈透的雙翅與墨染的身體虛實相生妙不可言。畫面也因性生趣,蘊含自然飄逸的審美理想。
三、委婉含蓄 空靈悠遠
宋代花鳥畫在經歷繁華般的燦爛后,逐漸走上低吟淺唱的沉寂與哀婉。“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2]花鳥畫發展到宋代末期大量出現了含蓄質樸小品畫的形式。兩宋更迭,給予人們的社會心態進而審美心態的撞擊時巨大的。國事的衰弱,及人們敏感的心靈必然受到動蕩不堪的時局影響,他們的思想感情的復雜性必然使繪畫轉向了哲學的思辨。“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有我之境”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無我之境”,審美理想上追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的美,但又是絢爛至極的平淡,于平淡中寓以無盡的深意。
林椿的存世作品《果實來禽圖》,此圖描繪林檎果一枝,枝上碩果累累,一只小鳥輕靈的飛來棲于枝頭,小鳥姿態生動,頭仰向上空,雙腳彎曲,先出就要飛上天的的情態,掛在枝頭沉甸甸的果實,仿佛使整個樹枝鼓動了起來。畫面的刻畫十分細膩,葉子上蟲咬的痕跡也表現的非常清楚,折枝花與枝頭的小鳥,猶如“稱”與“砣”般的均衡,傳達了“極寫生之妙,鶯飛欲起,宛然欲活”的審美趣味。吳炳的傳世作品《出水芙蓉圖》在團形的畫面中,以一朵花與兩片葉子充滿了整個畫面。畫家以一花而窺一池,這朵盛開的荷花豐盈而飽滿,嫻靜高雅蓬勃有生命力,同時又沉靜委婉,如同嬌羞的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荷葉與花的揚抑頓挫形成流動的韻律。在紈扇的的狹小空間被畫家經營的如此美妙,讓人發出畫外的無限情思。
宋人范晞文《對床夜話》說:“不以虛為虛,而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共難以。”[3]宋代花鳥畫將這種美學觀念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尤其南宋出現的大量小幅的花鳥畫作,畫面中虛實相攜悠遠空靈的意境,表達宋代后期人們審美觀念的轉變縹緲空靈之趣。所謂“境生于象外”就是要獲得象外之象的的意境,形成畫外有畫的效果。明畫家李日華說:“繪畫必以微茫慘淡為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以虛淡中含義多耳!”[4]笪重光《畫筌》講到“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追求形式中的空靈,使人們在塵世疲憊的心靈,憑此得以超脫,得到精神的解放,成就了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
宋代花鳥畫中蘊含了豐厚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內涵,與社會與人性和倫理巧妙融合,形成穩定的審美趣味和美學思想。宋代花鳥畫中創造型精神的無限性,構成中國傳統繪畫中美的不可言盡性。通過對宋人審美趣味的研究,構筑了中華民族審美精神,更是對民族傳統藝術的拓展和延續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注釋:
[1]俞劍華注釋:《宣和畫譜》,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頁。
[2]蘇力:《宋代詩詞美學》,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17頁。
[3]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頁。
[4]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版,第116頁。
參考文獻:
[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
[4]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三聯書店,2000(2).
[5]蘇力.宋代詩詞美學.商務印書館,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