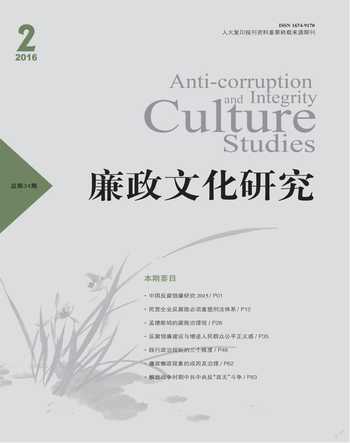權力瘦身視角下的新型政商關系構建
趙華英
摘 要:轉型期的中國政商關系一直受到政府權力邊界不清晰產生的影響。公共組織自我賦權的輕易性導致權力過多過濫,進而帶來尋租行為高發,是扭曲政商關系的重要原因;公共組織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相綁定”并凌駕于其上,使權力的清理愈加困難。因此,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清理不必要的行政權力,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同時建立更為嚴格的權力設定程序和權力退出機制,是從“不敢腐”向“不能腐”邁進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政商關系;政府權力;權力瘦身
中圖分類號:F12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170(2016)02-0023-05
從十八世紀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經濟”,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的管制或干預,一直是專家學者眼中的重要話題。由此帶來的政商關系處理問題,無論對經濟社會發展本身,還是政府自身的權力約束,都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轉型期的中國政商關系,一直受到政府權力和市場的邊界不清晰產生的影響。本文擬從政府權力瘦身的視角,對構建法治、高效的政商關系作出探討。
一、政商關系錯位源自政府權力邊界不清晰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保姆式”的全能型政府,企業與政府是無所不包的一體式聯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取向的逐步確立,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直接干預在不斷縮小,但政府權力邊界不清晰,權力過多過大導致的政商關系錯位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一)權力變現導致尋租行為高發
商人之所以有求于官員,是因為官員手里掌握了能夠帶來巨大經濟資源的權力。很多權力的賦予,初衷是出于宏觀調控、結構優化、環境保護等好的目的,但在權力行使過程中,“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只要權力能夠“兌換”為金錢,就必然導致大量的腐敗行為發生。這其中,有兩個值得引證的案例。一是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案。在鄭任內,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認證制度的推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為擁有超級權力的機關,任何藥品廠家要獲得生產資格,最終都要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作出決定。這其中,標準執行的寬與嚴,批準程序的快與慢,決定著一個廠家的效益甚至生死。鄭筱萸的一支筆,擁有巨大的含金量。在這種高度集權化的內部審批體系下,商人必然費盡心機去打點審批環節的各個官員。在強大的金錢攻勢下,鄭筱萸及其下屬的極度腐化也就可以想像了。二是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案。劉鐵男工作過的國家發改委,是宏觀調控的關鍵部門,有“小國務院”之稱,掌握著項目審批、資源配置等眾多權力。項目能不能批,早批還是晚批,都深刻影響著地方和企業利益。一個項目如果早日獲批,就能迅速投產、占領市場;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等批下來時可能早已喪失市場機遇。從已經公開的索賄紀錄看,劉鐵男一句話就能輕易左右化工項目、汽車項目的獲批,甚至中國鋁業這樣的大型國企也因有求于劉鐵男而牽涉其中。事后中央紀委的案件剖析也表明,劉鐵男正是通過控制審批進度,形成“拖—要—批”的三部曲,完成權錢交易過程。這兩個例子也足以表明:一項權力的設立,不管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不管有多么正當的理由,都有可能淪為政商交換的工具。
(二)賦權的輕易性導致權力過多過濫
2015年5月1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決定》,49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被取消,84項轉為政府內部審批事項,這距國務院2002年11月取消第一批行政審批項目,已經過去13年,期間共14次發文規范、取消或下放審批項目。這既說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又說明各級政府累積的權力之多。且不說那些涉及項目建設等領域的大的審批權力,僅國務院7月底下發的《關于取消一批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的決定》(國發〔2015〕41號)中取消的名目繁多的各種“職業資格”,如“飼料粉碎工”、“飼料制粒工”、“醫藥代表資格”、“商務文員資格”……如果不是公布取消,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么多稀奇古怪的“資格許可”。這些不必要的“許可”,人為抬高就業門檻不說,其認證、實施過程中,不知會滋生出多少權力尋租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職業資格認定的賦權依據,有的是部門一紙通知,有的竟是一些行業協會章程。中央部委尚且如此,各級政府部門還有多少自我設定的顯性和隱性權力?部門“自我賦權”,名義上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實則不可避免地摻雜進部門利益,成為相關部門以“表面合法的方式”來侵蝕企業利潤和民眾收入的根源。企業以行賄方式避免被“盤剝”,便成了合理的選擇。再以學歷認證為例,本來,學歷認證是為了打擊“假證泛濫”,但現在出國、提干、求職、入戶、職評、加薪,無一不需要學歷認證;本來,2001年之后畢業的學歷信息,均可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查詢到,整個過程不過1分鐘,成本2元。但因為有了“學歷認證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在各地的學歷認證中心取號、排隊、繳費,再等15個工作日甚至一個月,花去最少95元的認證費。而圍繞學歷認證,已經形成一條涵蓋認證代理、加急代辦等的隱秘產業鏈,而淘寶甚至有60多家辦理學歷認證加急業務的店鋪。[1]由此可見,當過多過濫的權力插手經濟社會生活時,為了消解權力的負面影響,為了榨取權力中的“含金量”,總會有商人以市場經濟原則,將權力轉化為金錢,成為錯位的“政商交換”。
(三)專項資金正成為政商交易的重災區
2006年,財政部出臺《規范財政轉移支付辦法》,提出嚴格控制新增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但這些年,專項資金規模卻不見縮小,甚至一度增加。“2008年下半年,4萬億投資催生了更多的專項資金向地方下撥,當年專項資金再一次超過一般轉移支付,占據總轉移支付的53.2%。幾乎每個部門都有專項資金下達,有的項目只有5萬元”[2]。從權力監督看,專項資金多由中央部門設立,但使用者卻遠在縣鄉,受益者在農村、企業,如此之長的管理鏈條,資金的跑冒滴漏及由此引發的貪污挪用等腐敗行為在所難免。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利用手中掌握的專項資金劃撥審批權,10年間大肆受賄2400余萬元。[3]再以中央財政投入累計已經超過200億元的農家書屋為例,全國已建成60多萬個,但據新華社記者2015年4月采寫的《農家書屋“空殼化”調查》表明,上級統一配送的圖書嚴重脫離實際,寧夏某地連群眾吃水都成問題,農家書屋書架上卻擺放著《無公害水稻安全生產手冊》、《大宗淡水魚養殖技術200問》等書籍,難怪一些地方的農村書屋會“3年沒有人借書,應付上級檢查還要找演員”。當農村書屋充斥著“賣不掉的書”,成為滯銷圖書推銷渠道,專項資金并非“惠民”,而成了書商、出版商分錢的盛宴,其中是否隱藏著大量的“政商交易”,令人生疑。在新華社記者2015年5月份一篇調查中,“北京一位曾參與文化資金申報的企業負責人表示,企業參與申報,必須削尖腦袋找關系,最終能否拿到項目資金,往往不是看做得好不好,而是看公關做得怎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文化產業研究學者張錚說,由于分配過程不夠公開,容易滋生腐敗,一些文化項目變成‘燒政府的錢沒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擔憂。”[4]在江蘇省句容市,通過查辦一系列生態環境保護領域職務犯罪案件,多部門公職人員協助多家企業套騙國家、省級各類專項補助資金高達1000余萬元。[5]在廣州科信系統腐敗案中,掌握專項扶持資金審批權的部門公職人員,“對科技資金的使用和分配、信息工程的發包等環節牟取私利;部門負責人行使職能時,自作主張,想給誰就給誰”,甚至有廣東省科技廳干部下海后成立了××信息咨詢有限公司,編制甚至假造申報材料,幫助企業打通關節,申請科技專項扶持資金,收取一定比例咨詢費,再從中提取部分錢款賄送主管該項業務的領導干部,金額達100多萬元。[6]在一些企業為直接受益對象的專項資金中,企業經過層層申報,就能獲得國家數百萬甚至幾千萬元的無償資金,政商勾結騙取專項資金的現象頻發,似乎是“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樣比辛辛苦苦掙錢容易多了。因此,只要專項資金大量存在,政商交易就不可避免。
(四)組織的“自生長性”與權力蔓延
歷史事實證明,權力在行使中始終存在一種超越界限、擴展行為范圍和規模的天然傾向。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說:“全人類共同的愛好,便是對權力永恒的和無止境的追求,這種追求至死方休。”在我國,權力行使受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約,但也不能排除權力的“自我擴張”屬性。行政部門有部門的利益,公共組織也有自己的利益,這使得任何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權力,不管其初衷如何,都會在行使過程中摻雜進自身利益。在全國范圍內,有多少權力、組織,在設立之時有其必要性,但存在多年后,已經異化為加重企業和群眾負擔、維持組織自身存在的工具?比如被媒體詬病多年的食鹽專營、煙草專營體制,連藥品、酒類這樣關系群眾生命健康的商品都已經放開經營,食鹽、煙草還有什么理由維持專營?在一定程度上,專營權力成了追求專營部門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專營權力為維護壟斷而對微觀市場的干預,既嚴重抬高了商品成本和售價,又成為政商關系錯位的根源。抑制公共組織的“自生長性”,堅決砍掉不必要的權力,已是勢在必行。
二、政府權力過度延伸的危害和后果
(一)扭曲資源配置
以成立于2013年3月的國家能源局為例,這個在中央各部委中級別并不算高的副部級單位,卻有核電司、煤炭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等多個核心官員落馬,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甚至被發現上億元現金。能源局的成立初衷本是服務國家能源安全,但其對能源領域審批項目的最終核準權不僅權力巨大,而且相對封閉,高度集中于一人或幾人手中,企業為了項目順利上馬,發動“金錢攻勢”,相關官員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不被“腐蝕”?當權力異化為自肥工具,宏觀調控、環境保護、結構優化等工作目標必然受到傷害,資源配置也被極度扭曲。
(二)滋生腐敗行為
政商勾結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雙向異化,權力靠資本變現為金錢,資本則靠權力實現最大增值。據歐盟委員會2013年發布的報告,政商勾結是導致腐敗的主因,每年給成員國造成1200億歐元的損失。在我國,由于政府權力邊界不清,權力極易成為腐敗官員的“提款機”。在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一案中,數千億元的高鐵建設合同,別說民企,連一些國企都不得不通過山西商人丁書苗支付數千萬元的“咨詢費”來獲得訂單,可見權力“租金”之高。
(三)擾亂政商關系
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與情婦合謀開辦“規劃咨詢”公司,專門為房地產開發商辦理調增容積率、改變用地性質等事項,從中收受賄賂達1790多萬元,并引出多達9人的腐敗窩案。[3]容積率直接關系到一塊地出多少房子,容積率稍微松動一點點,對于開發商而言,就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因此,各地開發商絞盡腦汁找官員“公關”,提高容積率幾成通例。這些年,各地規劃部門不斷曝出腐敗案件,容積率幾乎成了攪亂政商關系的“腐敗容器”。嚴格的容積率控制有沒有必要?控制容積率即使有一定好處,但在引發巨額腐敗風險且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有無必要適度放松容積率控制,改由市場調節,群眾監督?這實在值得相關部門反思。
(四)加重企業負擔
2014年10月,實施多年的企業年檢制度被取消,在此之前,一般性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限制也已被取消,由此減輕的企業負擔數以億計。企業年檢制度有無必要?在此之前,很多研究者指出,年檢制度已淪為工商部門創收的工具和“折騰”企業的合法途徑。此外,還有哪些年檢制度可以取消?比如網民一度強烈呼吁的取消非營運汽車年檢問題,年檢除了給車主帶來巨額年檢費用,排隊帶來的精力損失,現實生活中影響行車安全的車輛故障,有多少是通過強制年檢排查出來的?再比如建筑、醫藥經營等行業有“企業資質認定”的內容,其中將建造師、藥劑師數量與不同經營資質的掛鉤,在全國已經形成報考證書、出租證書、證書中介的“黑色產業鏈”。有沒有比這種簡單僵化的執證人員數量監管更為高效的監管方法?可以說,證書資質掛鉤的“監管權力”一日不取消,“證書掛靠”現象便不會杜絕。
三、從權力瘦身著手重塑政商關系
(一)對現有權力的清理應更為徹底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機構改革加速,國務院不僅加速削減行政審批權,而且將諸如企業工商年檢、不必要的職業資格許可等已經完全異化的行政權力果斷砍掉,這對促進政商關系正常化、增強市場活力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但是,幾十年來的計劃經濟沿襲,使各級政府部門“囤積”了大量不正常的“隱性權力”,或大或小,背后牽涉到強大的“部門(行業)利益”,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果斷予以清理。比如沿襲多年的“出租車牌照管制”,使“黑車”大量滋生、出租車公司合理剝奪司機的根源所在。以積極穩妥的態度放開牌照管制,才是出租車市場回歸正常的關鍵所在。
(二)權力的設定應更加審慎評估
在推進依法治國的大形勢下,各項法律法規規章起草、出臺進度會加快,其中每一條都有可能增加、擴大相關部門的權力。這些權力的設定是否過于草率,是否暗含部門利益,是否會讓一些“含金量頗高”卻難于監管的權力放縱開來,象“容積率”、“藥品定價”那樣,成為新一輪的腐敗“助推器”?官員的理想信念教育自然不可或缺,但如果權力過多過濫且能輕松變現,再多的正面教育、警示教育也靠不住。任何新的行政權力出臺,都不應忘記“小政府、大社會”的根本要求,要從完善公開討論、專家評估、社會監督等機制,更加審慎地評價權力設定對市場秩序、政府廉潔造成的影響。如果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不是很高,如果權力本身極易“脫韁失控”,如果沒有同步的監督措施,權力就不應盲目設定、出臺。
(三)建立行政權力的定期退出機制
很多行政權力出臺時,是出于促進公共利益,但時過境遷,當權力本身已經成為市場的牽絆時,卻沒有相應的權力退出機制。比如住房公積金的存廢之爭。當初,出臺公積金制度是為了幫助職工買房,但強制性的繳存制度,過低的收益率,既無法使大多數人受益,又成為變相的“強制儲蓄”,最直接的作用是養活了公積金管理機構自身。職工自己的錢,卻無權自由支配,于是想方設法找關系將“公積金”支取,甚至有的地方滋生了以幫助職工支取公積金為主業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公積金”的取消本無爭議,關鍵是背后的利益牽絆。我們的政府權力中,還有多少象“公積金”這樣應該退出的權力?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行政權力退出機制?這值得決策層關注。
(四)不斷健全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
近年來,一些地方實行了以找出權力廉政風險點、健全防范措施為核心的廉政風險防控機制,應該說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為關鍵的地方在于,沒有將內部監督、紀檢監察專門監督與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公開透明性差。如果權力監督僅限于行政系統內部,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就會逐漸實現“利益趨同”,極易“被收買”,造成監督落空。正如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要緊緊依靠人民參與支持,使群眾監督無處不在。這樣,才能形成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衡。
參考文獻:
[1] 羅歡歡,徐菲,席郁蘭.學歷認證,不合時宜?[N].南方周末,2015-04-24.
[2] 席斯.中央嚴管轉移支付 專項資金閘口收緊[N].經濟觀察報,2012-10-20.
[3] 陳金來,鄭瑞春.揭開“權力掮客”神秘面紗[N].中國紀檢監察報,2015-07-22.
[4] 數百億文化專項資金:“有些部門只為把錢花出去交差”如何讓錢用在刀刃上值得深思[N].新華每日電訊,2015-05-25.
[5] 檢察官揭環境污染背后貪腐利益鏈[EB/OL].(2014-11-10)[2016-01-20].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1110/c188502-
26000755.html.
[6] 林洪浩.科技精英“落馬”背后的“四個一”[N].廣州日報,2014-09-01.
責任編校 王學青
Towar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ating Government Powers
ZHAO Huaying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Hejian City, Hejian 062450, Hebei,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has always been troubled by the vaguely defined boundary between them. Public institutions have too readily granted themselves powers, which leads to the overflow of powers, and furthermore the abuse of power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distor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interest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are bound with social interests, the former transcending the latter, making it even more difficult to straighten them out. For this reason, it is crucial to clear out un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powers with uttermost determination, to mark the clear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o establish stricter procedu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owers and the mechanism of revoking powers, which will be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go from “not daring to corrupt” to “unable to corrupt.”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government powers; abating government p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