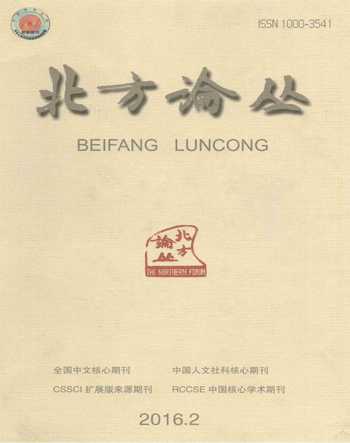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周易》文化精神對魯迅的影響
蔡洞峰
[摘要]《周易》文化精神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價值。其憂患意識,變革創新意識,以及獨特的思維方式,影響著包括魯迅在內的中華兒女,對魯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學創作、思維方式都產生了最直接和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周易》;魯迅;文化血脈傳承;創新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2-0052-06
一
作為中國20世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的代表人物,魯迅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將中國歷史的暗區暴露無遺。時過境遷,王元化晚年反思中國現代文化,認為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偏至的緣由是五四時期那一代學人的革命激進主義造成的。在他看來,由于激進而導致文化發生了逆轉,結果出現了文化的荒漠化[1](p.28)。
如果以直線思維理解,這話不無道理,但以當今眼光來打量過去的歷史,似乎不免有隔。以魯迅的學識與胸襟,他是知曉中華傳統文化分量的。置身于20世紀初的中國,當魯迅面對一個危機深重的古老民族,那些曾經讓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傳統,再也不能哺育出新的民族精神來拯救危亡中國;相反,它的存在使“老大的國民盡鉆在僵硬的傳統里,不肯變革”[2](p.47),而不能革新的民族,是無法立足于世界的。
面對著民族危亡的現實,魯迅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當時社會流行復古思潮進行了嚴厲地抨擊:“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么,去翻專夸本地人物的府縣志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2](p.118)
但是,始終以“立人”理想為自己一生追求的魯迅,在為“立人”思想開出的藥方卻是“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3](p. 57)。魯迅對待故國傳統遺存是以理性批判精神和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因此,我們分析魯迅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不能只從一些文章表面判斷其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而應該剝去外表的蕪雜,窺其思想內核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間的血脈關聯。
從發生學角度看,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是復雜的,從小接受博雜的經史雜著和鄉邦野史,這些接受傳統文化的“前結構”使他更能理性地對待故國傳統的遺存。在以后的為人為文的道路上,這種文化身份對他是有著影響的。
綜觀魯迅一生的思想發展與生存足跡,我們會發現其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始終是辯證務實的: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一直都珍視并積極傳承,而對那些傳統文化糟粕,“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散丸,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2](p.47)。因此,魯迅“全都踏倒”的是傳統文化中那些無益于現實的人生的糟粕,而并不是儒家經典,以及中華民族傳統的精華部分。
確實,以《易經》為源頭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傳統文化血脈孕育著以孔子、李白、陶淵明、曹雪芹、魯迅等不同歷史時期的中華文化代表人物。
古老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恰如“文化根”為魯迅文學生命和思想提供養分,但卻如“厚德載物”的大地那樣,不露聲色。“文化”與“生命”的互動,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需要載體的,那些從遠古流傳下來的文化典籍就是這種文化“化生”的載體。
冠群經之首的《易》,即后來的《周易》是探討“范圍天地之化”,闡釋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其知識是周密的并具有普遍性意義。《周易》作為“人更三世,世歷三古”的偉大經典,“它是我國‘上古(伏羲時代)、‘中古(周文王時代)、‘下古(孔子時代)無數先人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最古老文明的顯著象征”[4](p.12)。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作為幾千年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周易》對中華文明,以及民族思維方式和國人心理等方面的潛移默化影響是全方位的,深入脊髓的。《周易》思想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的危機意識,“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的理性精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的變革創造意識,影響了一代代中華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和行為實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產物,魯迅思想中對老大的國民不肯變革的絕望而產生的憂患意識、對科學與民主思想引領的國民自強理念和理性思維方式,以及對中國固有的文化與思想進入現代性的創新精神和革命意義的企盼等,無不體現了魯迅作為五四文化先驅的優秀代表,對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和內在血脈淵源。
二
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那種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是有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魯迅說他讀過“十三經”。周作人在他的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更明確地提到魯迅“在家已經讀到孟子,以后當然繼續著讀易經,詩經……”[5](p.801)。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道有變動,故曰爻”[6](p338)。“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6](p.336)。文中《周易》原文皆引自該書,下同。描述了《周易》所倡揚的易理,包括天地萬事萬物,人生日用不可須臾遠離、遺忘。教人為人處世,不管出入、內外,都必須遵循綱常法度,使人悉知戒懼。它又明示什么是人生憂患,察往昔而知未來。憂懼之心貫徹于始終,立人行事的關鍵,在于沒有咎害。這就是易道的作用。由危亡憂患意識產生的“《易》之興也”是教人常懷危懼之心,能致平安;慢易輕忽,必遭傾頹之厄運。教人警俱而不輕慢的易道發揚光大,天下事物就不會廢而不立。
《周易》中的卦、爻辭多含警戒危懼的意義,憂患意識一直貫穿其中。如《乾卦》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但白天要時時小心謹慎提防不測,就是夜里也要不放松警惕,這樣才可能化險為夷,確保平安。這是孔子對“危機”的辯證觀點,認為禍福相依,人們要時時有一種危機意識,而危機意識中又包含一種進取精神,只有這樣,才能保持自身安泰和家國運長久。
《周易》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源流和結晶,有高度的智慧,懂得天道的變化來作為民用的先導。這種先天的危機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浸潤在其中的仁人志士。從古至今,屈原、杜甫、梁啟超乃至魯迅等,都有著那種“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這種文化是饋贈給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在歷次危機深重的關頭能夠涅槃新生,不致亡國滅種的本質所在。
作為精神界戰士,魯迅從小就受到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浸潤,使其思想乃至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傳承關系。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人生的經歷和世故人情的省察是在互為互動中成熟和通達的,其人其文在自身的曲折經歷和深厚的傳統文化的化生之下變得較同時代人遠為深刻和超越。
少年時期家道中落,使魯迅很早就將人生內化為自身的閱歷:“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3](p.437)少年時代的魯迅,面對家庭的突然變故,使他對這段危機經歷刻骨銘心,看盡了世態的炎涼和復雜,那種無以為繼的憂患意識促使他“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3](p.437)。一個過早承受苦難的人,在精神的世界中,只有野草,不生喬木,這些弱小的存在給人以微茫的希冀,這種悲苦的意味,也許成就了他一生都將自己作為一名“戰士”去“反抗絕望”的精神底色。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之俱。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每一個六爻之卦都提醒人們保持一種謹慎的心理,避免災禍。可以說,憂患危機意識始終貫穿在《易》之道中,這種危機意識對中國的文人學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孟子在《易》“其有憂患”后,發出“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孟子·告天下》)。那種“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至理名言,從個人的生存到關注民族國家命運,中國歷代知識分子都懷著接濟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從古至今的一個傳統。屈原那種“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為國為民的深深的憂患意識;以及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陸游、龔自珍、魯迅等,他們一脈相承而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
嚴復的《天演淪》中的進化觀思想是影響了魯迅那一代人的,在那里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如古籍中所描述的是異樣的。 在《天演論》的世界里,“進化”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存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世界上萬事萬物都遵循的規則。
《天演論》帶給魯迅的啟迪是:近代中國社會面臨著社會危機與民族危機是民族退化的標志,“落后就要挨打”是現實的法則。中國人淪為奴隸和被“開除球籍”的危機意識是他“仙臺危機”發生的關鍵。魯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實質“不是在奴隸與奴隸主位置顛倒的循環關系中,而是在人的永無止境的精神進化這條上升的直線上找到了救亡之路。魯迅所提倡的‘文學運動的核心,就在于創造出擺脫奴隸狀態而能體現新的價值之‘人”[7](p.85)。
在魯迅的文學想象中,他看重精神,倡導為人生的文學,因為“文學與精神、神思等原初性存在直接相關。二者的直接對接,一方面使它得以超越知識、倫理、政教等‘有形事物的束縛而獲獨立; 另一方面,它又與政治、倫理、知識等力量一道,對社會、人生發揮作用和影響”[8](p.323)。用文學來改良民族精神并重塑國魂,讓民族國家擺脫現代轉型中的危機成為魯迅一生的追求和實踐。中國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傳統是讀書不忘救國,關注天下興亡。魯迅雖然反傳統,但內心的深處卻有著儒家那種家國情懷。林毓生曾說,魯迅“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于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9](p.178)。這種判斷是有道理的。
魯迅對現實與歷史的精準把握和圓融貫通能力是讓人嘆服的,他觀察中國社會,對明與暗、生與死、過去和未來,明察秋毫,鞭辟入里,成為國民性觀察最透徹的行家。《周易》將大化宇宙濃縮為太極六十四卦,天地乾坤無所不包地容納在黑白象數之間,宇宙人生盡在此中真義。由此看來魯迅血脈中是得《周易》思想真傳的。
關于文學的本原,劉勰在《文心雕龍》上說道:“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即是說文學的根本是承接《周易》的“自然之道”。而“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認為人文的本源就是“自然之道”,“天地之心”。魯迅通過文學來作為“立人”的手段,是與《周易》思想契合的。
魯迅思考中國危機的原點,“人的精神”危機,是將處于現代轉型危機的舊中國這樣的“沙聚之邦”變為正常的現代國家,“精神”的更新是關鍵。 由此,他提出“首在立人”的現代轉型道路,是對中國近代危機以及如何擺脫危機的實踐思考。
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體系不同,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征是將道德作為立國之根本。儒家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核心主張就是從完善個人道德開始,從而擔當“平天下”的神圣偉業。
在魯迅這里,個人的獨立與精神自立被認為“立國”的前提和基礎。“對個體精神契機以及文學契機的雙重把握,則預示著十年后‘五四的風雷。魯迅隱沒十年后的第一聲吶喊,實際上遠接十年后激揚文字的聲音”[10](p.175)。意識到危機是解決危機的第一步。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憑借自己的慧眼,在東歐被壓迫民族的詩人的詩中,發現奴隸覺醒的聲音,在其中蘊含著從奴隸變為“人”而所做抵抗的契機。這種發現毋寧說是魯迅天才的發現與《周易》思想有著“道”的契合。《系辭》中認為:“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突出強調了人在“道”與卦象變通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只有人,才能讓道發揚光大,成就“盛德大業”。
《系辭》中提出的“窮神”觀點與魯迅的“立人”觀有異曲同工之妙:“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所謂“窮神”,就是通過精神的感通而理解世間萬物的規律和聯系,從而能達到對萬物的體察而成為圣人,就能“通天下之志”,成就于國于民都有利的事業。前文說過,魯迅立人的核心觀點是對人的精神的啟蒙,只有“立人”方能“立國”,即“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這不正如《周易》“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的思想相一致嗎?
在魯迅的世界中,憂患危機意識總是時時籠罩著他,“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面對民族危機,魯迅通過理性的思考尋求解決之道,希冀通過文學來振拔國民性,重塑民魂,從而避免危機的真正發生,才能“身安而國家可保”。這充分體現了“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的《周易》危機意識和拯救的措施。
三
《周易》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源泉,承續著中華文化的血脈淵源,對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模式及特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它孕育的意象思維、整體思維以及陰陽思維都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影響著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從發生學的視角研究魯迅思想,就要考察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聯。也即作家的“文化根”的問題,它是一個人思想的原點。如同一棵大樹無論怎樣的枝繁葉茂,終究還是要立足于大地。大地的“厚物載德”的品格承載大樹的枝葉無限的向天地延伸。
《周易》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及坤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品格包含天地“化生”智慧,滲透進中國人的天地哲學中。中國的哲學觀是“道”的化生之說,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即是《周易》所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在中國哲學思想中,文化與天地萬物是同構的。《周易》說卦傳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作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靈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創作吸取與融會了古今中外各種有益營養,塑造了魯迅偉大的精神品格。 劉半農評價魯迅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當時人們認為此評價很恰當。從這個視角考察, 魯迅是最新的,但同時也是最舊的,他的文章越過桐城派、唐宋古文而返回到“魏晉”,但同時卻為新文學開辟出新境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國文化正是在不斷的創新中發展與延續著。“傳統文化”是豐富復雜的,并不只是孔子與儒家,它既是一個幾千年來不斷發展的過程(如“經學”中的漢學、理學、心學、樸學),也包括諸子之學與佛、道及民間文化。通過這種“外化生”與“內化生”,使外在的生命元素與內在的傳統血脈有機地扭結在一起,呈現出獨特的思想魅力與文章品格。
魯迅在對外來思潮的承接和內在血脈的傳承間,是處于一顯一隱之間的。在文學創作上,他坦言受到俄國果戈里和波蘭顯克微支,以及日本的夏目簌石和森歐外的影響。而是否受中國古代作家的影響,魯迅似乎沒有談及。但沒談及不等于不存在,讀魯迅的文章,那“格式的特別”,是有著中華傳統藝術精華的。
獨特的品格和思想來自獨特的思維方式,林非先生說:“魯迅并不是一位系統探討和專門研究某一種學科的學者,他從未在概念的界說方面下功夫,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和剖析也同樣是如此。”[11](p.1) 這說明魯迅的思維特征是直觀感悟性的,通過細致觀察與深刻的感悟,做出簡潔和概括的見解。
直觀思維方式是指對客觀存在的感悟性認識。在《易經》中的卦爻辭,大多是前人處理生活中所遇事的經驗記錄,屬于個人的體驗,而不是一般的事理與原則。
《易經》的作者將這些體驗匯集起來,經過篩選和編輯,作為后人判定事物和推測未來的比照范例,這就是《易經》直觀思維方式的表現。這種思維方式,純粹是以卦辭為卦象的驗證結果,以此卦卦象為此卦卦辭的先驗征兆,作為后人求得此卦時預測兇吉的比照例證。
將這種記錄的驗證情況作為一般的、帶有普遍可比照性的事例與卦爻象相應。將直接體驗轉換成相關卦爻象的內涵展示,與此相連,也變成了算得相應卦爻者預見未來事件的參照標準。
由此可見,在人們頭腦中已經形成了這樣判定事物的思路:為了判定事物而算卦,由算卦獲得卦爻象,再由卦爻象找到相關的卦爻辭所記錄的直接體驗,最后直接判定所要判定的事物。這種思維的基本原理是用了相似事物,應用相似辦法去判定與處理。
魯迅這一點的思維方式,是與《周易》相通的,比如,他在《狂人日記》中將中國幾千年歷史概括為兩個字:“吃人”,而在《阿Q正卷》中批判國民性時,用了“精神勝利法”來概括國民劣根性,這些思維方法既形象生動,又深刻易懂。
魯迅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感悟最深刻敏銳的人之一,他通常用這種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和創作,啟迪國人的心智和精神,讓其擺脫奴性,成為自覺的人。
《周易》提出的“圣人立象以盡意”的命題,認為外在的形象能夠表達圣人的心意,并且進而認為文字和語言不能充分表達心意,但圖像即卦象卻可以充分表達心意。在《易傳》作者們看來,思維不能脫離形象,形象的內容比語言文字所表示的更為豐富。如乾卦卦象所蘊含的內容可象征一切陽性的事物和性能;爻象的變化也不限于象征某一具體事物的變化,而可以包括一切有關事物變化的過程。因此,判斷吉兇之義不能脫離卦爻象。所謂“極天下之賾者存乎通,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行而行之存乎卦,神而明之存乎人”(《系辭》上傳),說明人依賴于卦爻象的變化推斷吉兇,展示了形象思維的特色。
這種思維方式對中華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是巨大的。所謂“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說明古代人對思維賦之于形象的依賴。魯迅的思維方式與一般關注理論的哲學家不同,不以理論體系和概念來進行喚醒中國國民的工作,而是以形象化的思維感悟和塑造典型的形象的藝術方式,來喚醒民眾的覺悟和腐朽的勢力抗爭。正如胡風所說:“他從來沒有打過進化論或階級論者的大旗,只是把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神經纖維里面,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和舊勢力作你一槍我一刀的白刃血戰。”[12](p.501)
當然,作為世紀民族魂,魯迅的思想和思維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古今中外文化多元共生的產物。外國的尼采、托爾斯泰等思想家為他提供新的思想維度,而本民族包括《周易》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間野史等則哺育其血脈根底。這些“四海”和“四野”之雜學賦予他獨特的思維方式:新異、敏銳、深邃而富有詩心。恰如張夢陽所說:“個體精神自由,從本質上說,也就是樹立科學的思維方式,上升到理性的自覺境界。‘立人,就是立科學思維。”[13](p.11)
四
我們知道,人類的創造精神,要在人們擺脫對自然界的依賴后,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長而形成社會分工才能形成:“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14](pp.35-36)。這就是人類自覺的創造精神。
《周易》的創新文化精神體現在將“陰”“陽”的觀念對世間萬物進行解釋,確認“一陰一陽之謂道”,賦予“道”以無窮的創造性功能。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系辭上》)因此,“變”是世界上萬事萬物發生、發展的普遍規律。只有通過變化革新,才能生發出“生生之氣”。《易傳》中的這種“變化不息”與“鼓萬物”的創新精神,主要通過其陰陽恒變的思想闡發出來。
魯迅與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仁人志士一樣,為心中追求理想的“大德”與“大業”而奮斗。在魯迅生活的時代,西學東漸,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激活中國淵博的文化,重發剛健美上生機,這是魯迅一直思考的問題。為此,他對金石學以及漢畫像進行考證,以發現中華文化藝術的精深世界的魅力和精魂,對其進行傳承與創新。察其血脈,激活民族精神。
魯迅非常欣賞漢唐時期,能不拘一格吸收外來文化,他稱之為“漢唐氣魄”, 可以看出,他對這一歷史時期是神往的,在民族風雨飄搖的時刻,回眸遠古的藝術,也有奇異的存在。那些曾經的朗然大氣、直沖霄漢的磅礴氣韻,今人已不復存在,只能遙祭遠去的時光。魯迅在《看鏡有感》中,不無感慨地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無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駛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他因此推論:“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3](p.219)為了民族的未來和新生,必須放開肚量,大膽地,無畏地,將包括人類一切進步的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從而傳承中華文化血脈,激活漢唐藝術的新生。
漢代畫像呈現的獨特藝術氣質深深吸引了魯迅,從漢代畫像中洋溢著東方之美的力量中,激發了魯迅從古老民族文化中吸取創新的變革精神,取新復古。魯迅對漢唐藝術中大膽吸收異域文化而加以改造本國文化傳統的現象由衷地稱贊。并受此啟發,將優秀的民族藝術植入到現代木刻中,“用幾柄雕刀,一塊木版,制成許多藝術品, 傳布于大眾中者, 是現代的木刻。木刻是中國所固有的, 而久被埋沒在地下了。現在要復興, 但是充滿著新的生命”[15](p.365)。
傳統文化要獲得現代性的實踐品格,獲得新的生命。魯迅要求民族藝術“是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標本,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3](p.346)。對傳統文化古為今用,化作“立人”實踐,使傳統文化有了現代意義。這種思想蘊含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的《周易》智慧。
在S會館抄古碑期間,他還大量閱讀域外的作品 , 特別是一些美育與藝術作品。那些域外的文字與故國傳統文化在魯迅的精神中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如同太極陰陽交互運動,在現代主義藝術與古老的碑文拓片間,古老的存在與現代性的思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融為一體,使他有了天馬行空的精神境界,他的作品一直有著這種特質。在魯迅看來,在中國歷史中所值得稱道的藝術,都是與域外文明交融的結果。只有在開闊的視野中,才能有精神創造的自由。
魯迅后期的激進與積極參加社會運動,究其實質而言是想造就一個混血的時代,將多元的藝術與思潮引入中國,從而希望中華民族有自我創新的血液。在晚年的歲月中,他召集胡風、黃源等青年人翻譯作品、編輯書刊,推介版畫,在吸取他人精華融為自身血脈而行動著,有一種精神的渴望,為中華民族創造生生不息的文化氣脈。
綜觀他一生的足跡,從早年抱定的“實業救國”理想,到日本時期的“幻燈片事件”而決定拯救國民的靈魂,從而倡導文學實踐,魯迅思想可謂與時俱進,他這樣做的目的無不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與中興。“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不斷變革運行,改革就是要順應天的意志而又合乎“人”的意愿。革能取信于眾,變革得當,—切悔恨都將消亡。可見,魯迅一生的選擇正是合乎20世紀中國的變化與發展的要求,順應了歷史的潮流。
在魯迅看來,文化創新關系到一個民族能不能強盛和發展的問題。中國想要生存和發展,唯有吸收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一切優秀的文明。這樣古老的中華民族才能獲得新生,變為文明人的國家。在其早期文言論文《文化偏至論》他就疾呼:“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3](p.57)
魯迅面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他開具出“弗失血脈”,以及“別求新聲于異邦”的藥方,為承續中華固有血脈準備良性環境和新鮮活力,魯迅的文化創新精神就其本質而言,它與《周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有著內在契合。
五
《周易》中《賁》卦:“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關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對君子“人文”的“化成天下”精神的褒贊。
綜觀魯迅在20世紀中國,他無時無刻不呼應著時代的風云,始終站在大眾特別是底層民眾的立場為人或為文,這樣的人生姿態使他成為“中國社會的良心”。為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以及讓民眾“幸福的生活,合理的做人”目標而上下求索。而愿景的實現則有賴于魯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文化理想為軸心的。前提是需要依靠包括以《周易》為代表的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為根基,以及仁人志士當仁不讓的文化責任感共同參與建構。
在當今大力倡導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魯迅對待以儒學為中心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尤其值得重視,“反者,道之動”(《老子》)。魯迅的行為從反方向上開拓傳統文化的民間性與多元性,以揚棄的方式化生國學的現代性價值和內在活力,這是魯迅留給我們民族的一份寶貴遺產。
在中國當今的時代語境下如何振興國學?楊義教授則認為:“現代中國如果要建構生氣勃勃的國學,就應該珍惜這份遺產,不是拋棄魯迅返回孔子,而是在現代大國的文化總結構中包容魯迅與孔子。魯迅與孔子也能包容和溝通嗎?那就看你是否具有現代大國的文化風度了。有容乃大,這是現代大國文化風度的題內之義。新型大國學,應在博取和重組孔子、魯迅等相遞進而又不一定同質的思想家之后,以博大的胸襟融合創新,走上新的歷史發展臺階。”[16](p.283)
傳統國學如何轉化?魯迅思想的存在無疑對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有著資源的意義,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汪衛東認為:“傳統從來不是優劣不分的,他所批判的,是阻礙中國現代轉型的文化心理遺留,相反,對于傳統中的優秀部分,一直是珍藏并加以發揚的。魯迅的存在,是偉大中華文明的一副解毒劑,而魯迅的偉大本身,也正是中華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識、能夠自我更新、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證明。”[10](p.197)
魯迅通過否定、批判、解讀,實現以儒學為中心的源于中華民族傳統的創造性、自我批判轉換。而他的危機意識、理性的思考,以及銳意進取革新的精神,在當下正在轉型的中國,無疑是值得我們珍視的現代精神資源。
[參 考 文 獻]
[1]王元化.思辨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魯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陳良運.周易與中國文學[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5]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C]//魯迅回憶錄:專著 (中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王振復.周易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7][日]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M]李冬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8]壽永明,王曉初.反思與突破:在經典與現實中走向縱深的魯迅研究[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9]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10]汪衛東.現代轉型之痛苦“肉身”:魯迅思想與文學新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1]林非.魯迅和中國文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12]胡風全集:第2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3]張夢陽.魯迅的科學思維[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81.
[15]魯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6]楊義.魯迅文化血脈還原[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作者系蘇州大學博士研究生,安慶師范大學講師)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