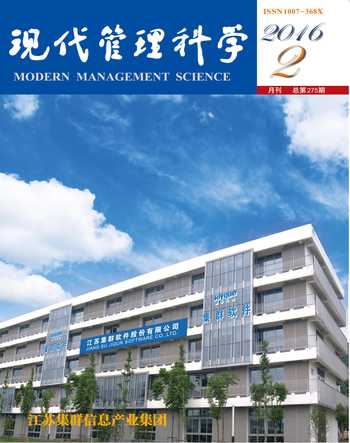顛覆式創新:一個文獻綜述
王麗 施建軍 鄧宏 夏傳信
摘要:顛覆式創新近來成為戰略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問題。顛覆式創新的研究很多,文獻研究的方面呈現分散、矛盾的現狀,對我們理解顛覆式創新造成阻礙。文章首先闡述了和顛覆式創新相關的基礎概念和支撐理論,澄清了對顛覆式創新概念的誤解,然后總結和批判性地提出如何從企業外部、內部、市場營銷和技術等方面發現和啟用顛覆式創新;然后總結了抑制和推動顛覆式創新的因素,為管理者提供參考;最后提出了關于顛覆式創新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顛覆式創新;文獻綜述
一、 顛覆式創新:發展、內涵和幾個誤解
1. 顛覆式創新發展、內涵。顛覆式創新理論的提出是在前人一系列技術創新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1997年出版的《The Innovator's Dilemma》關于商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的研究使得Christensen聲名鵲起,該書全面、詳細的介紹了顛覆式創新的基礎理論
顛覆式創新的概念代替顛覆式技術,顛覆式創新理論擴大到不僅僅包括技術產品好,還包括服務和模式創新,比如折扣店、低價且點對點的航空路線和在線商業教育。Markides(2006)批判性的指出,顛覆式創新不應只包括顛覆式技術,還包括管理模式創新。Christensen對顛覆式創新概念做了進一步的界定,他把顛覆式創新分為:低結點和新市場兩種顛覆式創新。所謂低結點,即該顛覆式創新獲得低利潤,在最低端價值網絡服務大宗消費者的顛覆式創新。新市場顛覆式創新指創造新的價值網絡,必須面臨開拓市場的困難。
學者把技術創新分為兩個主流:(1)革命性、不連續、顛覆、激進、意外或蛙跳;(2)變革、連續、漸進。每一個分類都是服務于特定的、存在差異的現象。例如最經典的從企業角度分類:能力強化創新和能力破壞創新,是為了解釋現存的企業在面臨顛覆式創新時,因此也與現存的在漸進式創新表現優異的企業在面臨顛覆式技術時一敗涂地的情景(Tushman,M. & Anderson,P,1986)。
Govindarajan和Kopalle(2006)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顛覆式程度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的標準。信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和統計檢驗都很好的支持了他們的測量。他們的測量顯示,顛覆式創新應該具有以下特點:(1)提供新的價值,吸引一個新顧客細分市場或者在現有市場上制定更高的客觀價格;(2)以較低的價格出售;(3)利用利基市場對主流市場進行滲透。
2. 關于顛覆式創新的幾個誤解。什么是真正的顛覆式創新?需要通過不同的視角進行分析和討論。我們需要辨明顛覆式創新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澄清關于顛覆式創新的一些誤解。首先,顛覆式創新是一個相對的現象;第二,顛覆式創新不總是代表現有業務將被新業務取代,也并不意味著必然對現有企業造成干擾;第三,顛覆式創新不等于毀滅式創新。一個擁有高性能、低成本的顛覆式技術創新能夠很快占領主流市場。
二、 顛覆式創新研究視角
實證研究發現不聯系的創新通常由新進入者創造(Anderson & Tushman,1990)。這是因為與現有的成功企業相比,新進入企業具有規模小、短的(路徑依賴)歷史和更多的有限成人的價值網絡和當前的技術范式((CM Christensen,2008;Macher & Richman,2004;Walsh et al.,2002)。有趣的是,少量的大型現有企業在辨識和利用潛在的典范技術通常被其他企業打斷(Paap & Katz 2004)。因此我們不僅要問為什么有些大型現有企業失敗另外一些卻生存下來?決定企業成功的因素或有助于企業成功顛覆式創新的因素是什么?本部分試圖從四個視角回顧以往文章在解釋上述問題時的因素:(1)企業內部視角,組織模式和現任企業面臨的挑戰;(2)外部視角,背景和環境;(2)營銷視角,在顛覆性變化下消費者定位。(3)技術視角,對顛覆式創新的技術戰略。
1. 企業內部視角。很多文獻從企業本身的視角闡述了影響顛覆式創新的因素。該流派的解釋可總結為四個方面:(1)人力資源;(2)組織文化;(3)資源分配;(4)組織結構。
(1)人力資源。關于人力資源的研究分為兩個子視角:管理者和員工。管理者子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企業在面臨顛覆式創新時,企業管理者能力的作用。首先,高級經理可能不理解顛覆式創新的承諾,因為他們的觀點根深蒂固,受經驗的束縛(Henderson,2006)。他們中的大部分受到常規業務訓練,管理有良好產品線的面向已有市場的企業。因此需要一個額外團隊負責收集顛覆式創新的思想,并把這些思想變成現實(Christensen & Raynor,2003)。另外對關鍵高管的管理,應以長期導向目標為基礎的激勵計劃取代短期導向,公式基礎的激勵計劃(Govindarajan & Kopalle,2006)。因此,高級管理者應不受限于剛性激勵和避免風險的顛覆性創新。第二,中層管理者也存在問題,在低等級森嚴的組織,大多數戰略要求他們采取最基本的形式處理創新,另外在資源分配方面,他們傾向于分配資源到有利于維持他們職權和封底的業務(Christensen & Raynor,2003;Denning,2005)。第三,創始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之間對顛覆式創新績效的要求存在沖突。創始人在鼓勵顛覆式創新方面有較大優勢,因為他們不但具有政治影響力也有自信(Christensen & Raynor,2003)。而關于管理者的研究,在探討高級及中級管理人員與創業者在對顛覆式創新不同的影響時,重點強調了管理者無能對顛覆式創新的阻礙。
該視角的研究也從員工的角度探討了顛覆式創新失敗和成功的影響因素。例如,關于NTT DoCoMo成功顛覆式項目的團隊研究發現,該團隊成員都是企業精心挑選的具有風險偏好的具有專業知識的人才((Murase,2003)。在決策制定方面Christensen認為,從直接接觸市場和技術的員工捕捉新的業務增長的方法比依賴于分析企業戰略或業務發展部門更有價值。接來下,實現顛覆性大想法而不是接受千篇一律的政策,管理人員應花時間確保有能力的員工的任務和工作過程與其價值觀匹配(Christensen & Bower,1996)。
(2)組織文化。企業的組織文化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文化是有效控制和協調員工的途徑,沒有精心制作的、僵化的正式控制系統(Tushman & O'Reilly,2002)。然而,文化是把“雙刃劍”,有時會導致創新的失敗。當大的變化比如顛覆式創新的發生,案例研究已經證明組織文化形成的文化慣性難以克服,也通常是一個管理者未能及時引進改變的原因,即使有時他們知道這是必要的(Christensen & Raynor,2003;Henderson,2006)。因此應時刻準備為顛覆式創新而發生的組織變革和放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然而一些積極的組織文化如:創業、冒險、靈活和創造力,應該被保留以培養顛覆式創新(Govindarajan & Kopalle,2006;N Sultan,2012)。
(3)資源分配。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也會造成顛覆式創新的失敗。其中最主要的抑制作用來源于結構路徑(Nelson & Winter,1982),如:財務匯報評價的關鍵因素(Christensen,2006)和傳統的市場分析報告。結構路徑限制了企業的行為和用評估現有業務的方式評估新興的顛覆式項目。結構路徑一旦建立就很難改變。另外一個類似的錯誤就是資源陷阱,企業受困于為現有業務投入的大量資源(Christensen,2006),繼而在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的業務上投入更多,結果導致企業應對競爭性的威脅技術時,通常采取通過現有客戶改善傳統使用的技術,失去了新的顛覆式創新的機會。總而言之,結構路徑、不完善的財務測量方法、資源陷阱阻礙了潛在的顛覆式創新的發展。
(4)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的研究包括組織規模、業務單元、業務單元拆分和二元化組織,以及現存公司與初創企業間的合作。
第一個子視角是業務單位的數量的規模與顛覆式創新之間的關系。創新領域的研究發現其與的或業務單元的規模是影響R&D效果的重要因素(Cohen & Klepper,1996;Tsai & Wang,2005)。最近一個傾向就是學者們普遍認為在生產新產品時,小企業的R&D效果優于大企業的效果(Lee & Chen,2009; Lejarraga & Martinez-Ros,2008)。特別是關于顛覆式創新的研究,案例和實證研究都證明了企業的規模與顛覆式創新之間曾負相關的關系(Christensen & Raynor,2003;DeTienne & Koberg,2002;Tushman & O'Reilly,2002)。這意味著大型企業應該通過更小的業務單元保持器靈活性,進而保持決策制定者的興奮度和把握重大新機會。另外在組織結構的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商業模式對顛覆式創新的反應。他們認為顛覆式創新分為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其中商業模式創新是最關鍵的顛覆式創新部分(J Hwang,2008;Yu D, Hang C C,2010;CD Charitou,2012)
2. 背景和環境視角。突破組織層面,學者開始從企業的北京和環境角度,研究顛覆式創新。結果發現,企業通常鎖定在投資者和分析師和預期、目標的承若,以及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Denning,2005;CM Christensen,2006)。例如,個人技術必須在其他先關技術以及開發或者同時開發才能夠實現商業化。因此與技術供應商和合作伙伴的關系對顛覆式產品的商業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Myers,2002)。
此外,早期研究發現大量技術、法律和社會的不確定的環境下,在有效的組織環境下,傾向于重新定位和創新,包括顛覆式創新(Tushman & Anderson,1986)。
3. 營銷視角。另外關于顛覆式創新的視角是營銷視角,該流派研究了企業在顛覆式變化中的顧客導向,試圖從顧客的角度出發需求解決方法。Danneels(2002)提出二級影響能力是能夠把新顧客到新的市場的能力。當企業對新的技術能力并非持思想僵化態度,而是因為他們在鏈接該技術的發展與市場之間的變化是失敗的。避免破壞式技術的負面影響關鍵的問題是關注顧客對業務需求的變化。Govindarajan和Kopalle(2004)發現一個月是一新顧客為導向,企業顛覆式創新的可能性越高。其他學者認為,主流顧客為導向還是新顧客為導向并不是相對的二選一的的兩個,他們是一個連續體的兩個端點,因此他們建議企業同時采取兩個導向(Baker & Sinkula,2005;Narver et al.,2004;Slater & Mohr,2006)。一個以客戶為導向的公司可以服務于現有的客戶并保持警惕在新興市場的非消費群(Chandy & Tellis,1998;Day,1999;Slater & Mohr,2006)。環境動蕩性越高的情況下,企業采用顛覆式創新使得小企業戰勝大企業的機會增加(陳錕于、建原,2009)。
通過上面的文獻綜述我們發現,再多的強調發現新顧客、市場都不為過。因為企業進行顛覆式創新失敗的障礙往往在于不能發現新興市場,并找不到適應該市場的新技術。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發現新興市場和發掘顧客的潛在需求?一些學者提供了幾種技巧,了解客戶的行為,而不是簡單地說他們會表現如何。一些流行的方法包括客戶拜訪計劃、移情作用的設計、跟蹤客戶消費流程、重視顧客體驗、開發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策略。
4. 技術視角。和其他視角相比,如:業務模式、組織挑戰、消費者導向和環境對顛覆式創新的影響,技術對顛覆式創新的影響,技術受到了很少、很有限的關注。這導致一些誤解,當企業發現一項顛覆性技術時,就能夠迅速把握住市場機會。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創造一定的顛覆式技術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特別是基于新的科學的發現。
除了Kostoff等(2004)和Walsh(2004),很少有人在顛覆性創新前公共闡明創建技術。在第一個研究中Kostoff等人強調識別或創造潛在的顛覆性技術的系統化方法的必要性。但是,他們認為顛覆式創新是能夠提供戲劇性改進,更有效和更高單元性能的創新。這沒有遵守顛覆式技術的本質,即最遜色與傳統技術。另外,他們制定了一個明確的路線圖,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個過于詳細的路徑圖可能適得其反,因為顛覆式創新是不聯系的,其前端是模糊的。第二個研究,Walsh為微系統和納米技術的顛覆式開發和商業化修概率藍圖工具。然而,在微系統和納米的技術的顛覆式創新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些方法皆在解決不連續的創新,不同的持續創新/增量創新。不幸的是,他們的研究結果并不能真正解決“最初劣質”的顛覆式技術。找到一個系統的為申請現有的技術或產品識別顛覆性機會仍然是一個難題。
三、 討論和展望
從前面的文獻回顧部分我們看到,顛覆式創新理論已經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在前面我們把以往文獻對顛覆式創新的研究分成三個邏輯清晰的主題。在顛覆式創新理論的演變、描述和澄清的基礎上對該領域做進一步的研究。在“破壞性創新理論視角”,主要的結論,破壞性創新理論可以應用到預測未來的公司支持的努力研究了如何啟用一個顛覆性的創新。
然而,也有很多關于檢測顛覆式創新的研究。盡管一些研究對非連續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價值的,因為顛覆式也具有非連續性,但是本文關注點在于關于顛覆式創新理論研究的發展。其中第一個建議是,一個完整的測量顛覆式方法應該是大規模精確的比較影響顛覆式創新各個因素的研究。第二,中層領導反對顛覆式創新和理由是,他們必須保護他們當前的地盤,避免負責有風險項目。那么是否存在一個鼓勵中層管理者支持顛覆式創新項目,還能夠維持他們在企業的地位的策略?此外,關于企業創始人在顛覆式創新項目上比職業經理人更有優勢,但是沒有實證研究能夠證明這點。此后的問題便是如何改善管理教育項目來裝備職業經理人在顛覆式創新上的能力。第三,以往的文獻已經證明,保持業務單元大小的合理性對發展顛覆式創新項目有積極的影響,但也增加顛覆式創新的成本和困難。因此,如何優化大型企業中業務單元的數量和規模是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第四,關于組織文化的視角研究發現,組織對顛覆式創新有消極的影響作用。什么時候應該努力忘卻?如果一些元素如:企業家精神和冒險應該被保留,那么哪些元素應該被拋棄?那么關于企業客服文化慣性和更新組織文化中的主要元素的縱向研究應該提供更多的見解。第五,關于管理者,應該創建一個核心團隊專門來收集顛覆性創新思想和把這些付諸實施(Christensen & Raynor,2003,281)。一個很好的建議是聽取一線員工是獲得顛覆式創新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因為他們直接接觸市場和技術(Christensen & Raynor,2003)。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比較核心團隊和一線員工之間的矛盾和互補性,我們認為其結果應取決于項目的階段和業務性質。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解決因為人才流失而導致顛覆性創新中斷的問題。第六,潛在的顛覆式創新不能商業化一般由于互補技術的缺少或者不能與合作伙伴(如:供應商)分享類似的潛在的顛覆式創新。因此未來需更多的關注組織之間的關系對顛覆式創新的影響(Denning,2005)。最后,研究在不同的上下文在不同的國家也可能是有用的在理解如何讓一個潛在的破壞性創新成功,考慮到語境因素如監管和創業文化。
參考文獻:
[1] Adner, R.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6,84(4):98-107.
[2] Christensen, C.M.and Raynor, M.E.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3] Markides, C.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need of better theory.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6,(2):19-25.
[4] Henderson, R.M.The innovator's dilemma as a problem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6,(23):5-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號:11&ZD00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號:12&ZD205);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項目號:10AGL00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號:71072019);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創新重點項目(項目號:201408)的階段性成果;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級課題(項目號:14YB23);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內外聯合培養研究生項目。
作者簡介:施建軍(1955-),男,漢族,安徽省無為縣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國際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企業創新與創業管理;王麗(1985-),女,漢族,山東省梁山縣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企業創新與創業管理;鄧宏(1976-),男,漢族,四川省眉山市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管理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企業創新與創業管理;夏傳信(1982-),男,漢族,江蘇省宿遷市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統計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經濟統計。
收稿日期:2015-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