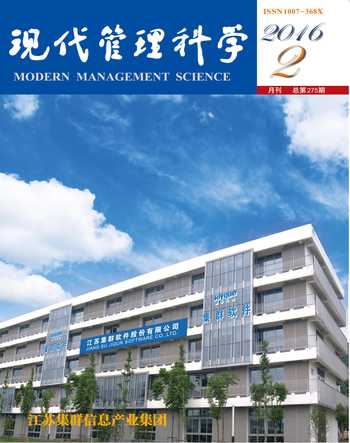分工、規模化經營與農村服務業的發展
王鐵成 朱恒鵬
摘要: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發展見證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不斷壯大,農業則長期被視為一個低效率的劣勢產業。兩百三十九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生產效率的提高有賴于分工的發展,而分工又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因此,農業以及農村服務業低效率的關鍵原因就在于,相比工業,其分工潛力很小。文章的分析表明,農村服務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要依賴分工的深化,而服務業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則與農業規模化經營之間存在著天然聯系,以小農為基礎的互助合作的經營模式難以推動農村服務業走向專業化和高水平。
關鍵詞:分工;規模化經營;農村服務業
一、 分工思想的發展
亞當·斯密最早將分工思想引入經濟學研究中,在斯密看來,正是分工和“看不見的手”導致了一國國民財富的增長。斯密認為,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這主要是由于:(1)分工和專業化促使勞動者技能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得到了逐步積累;(2)分工降低了勞動者轉換工作的次數,節約了勞動時間;(3)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提高了勞動者發明新型生產工具的可能性,物質資本得到了積累。
針對分工發展的原因,斯密認為,分工是人類內在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互相交易。交換傾向決定了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以分工為基本形式,而不是自給自足的形式,而交換的能力和潛力則決定分工發展的深度,代表交換能力和交換潛力的是市場的范圍,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市場范圍太小,分工便難以獲得發展,市場范圍不斷擴大,分工則會逐漸深化。斯密進一步分析了制約市場范圍擴大的因素--運輸成本,比如水陸運輸對陸路運輸的替代降低了運輸成本,導致市場范圍的擴大。
繼斯密之后,楊格(Young,1928)進一步發展了分工理論,其主要貢獻在于從動態的角度來考察分工的演進。楊格指出,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將會創造出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實現是以資本積累為前提的,這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和物質資本積累,也就是采用迂回生產方式(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一方面,迂回生產方式受到市場規模的制約,市場規模有限將導致大規模的投資無利可圖;另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的實現,迂回生產方式將會降低單位生產成本,進而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最終擴大了市場規模,市場規模的擴大將會導致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在分工與市場規模不斷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經濟進步”便實現了。
“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開始走向新古典方向,對資源配置的靜態研究逐漸成為經濟學關注的重點,分工思想逐漸被邊緣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分工思想才逐漸復興,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重新將分工思想置于經濟學分析的核心位置。楊小凱在一系列文章中對斯密的分工理論進行了深化和擴展(Yang,1991;1993;1998),主要貢獻之一是分析了勞動分工與交易效率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新興古典經濟學指出,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因為分工的發展伴隨著交易費用的提高,如果分工的收益低于交易費用的上升水平,那么降低分工水平才是最優選擇。
二、 中國農業勞動分工的發展歷程
中國農業組織的演進過程大致可以歸納為:集體經濟→家庭經營→農業商業化→農業產業化→農民團隊化(向國成、韓紹鳳,2007)。從分工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業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 非市場制度下的分工:人民公社。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全國范圍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每個家庭都獲得了一定的土地,農業產出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增長,但在“一五”計劃開始后不久,家庭耕作便被集體化取代,人民公社成為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在集體化制度的安排下,農民被分為兩類群體:普通社員和管理者(生產隊隊長、會計等),普通社員按照管理者的安排進行勞動,管理者則主要負責組織生產活動和各種非生產活動,但也要從事一定的生產活動。在這種簡單的分工體系下,激勵機制的欠缺是最大的問題,這體現在兩個方面:(1)生產者缺乏激勵。對于社員來說,一方面對產出沒有剩余索取權,另一方面管理者很難準確衡量生產者勞動的努力程度,勞動質量與勞動收入難以匹配,因此生產者沒有積極勞動的激勵,“搭便車”行為難以避免;(2)管理者缺乏激勵。與生產者類似,管理人員對于產出也沒有剩余索取權,因此其管理和監督行為也缺乏激勵。
2. 無分工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始于農業領域的重大突破,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農業開始轉向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同時將剩余索取權賦予家庭,以此為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制度內涵:首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表著一種土地制度,農地屬于集體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屬于家庭;其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代表著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改變--個體組織取代了集體的生產組織方式(許慶,2008)。
從人民公社的生產方式轉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變了農業勞動分工的組織形式,由原來低效率的非市場化分工轉變為高效率的無分工生產方式。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度下,“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生產活動和管理活動合二為一,雖然從表面上看家庭聯產承包制使得農業的勞動分工水平下降了,但是農民的生產活動獲得了足夠的激勵,進而提高了農業的產出水平。
3. 農業內部分工的發展。趨向市場化的經濟力量必然導致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普遍實行使得農村的勞動分工退化為個體生產模式,同時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原來在生產中發揮作用的許多農業機械被農民的個體勞動和畜力所代替,這導致農業生產的迂回程度大大下降,但隨著農產品交易以及中間產品市場化的發展,分工必定向著更加深入的方向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大量中青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業生產必然要再次走向分工。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初期,人們往往是通過互助的形式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隨著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農村家庭越來越難以依靠自有勞動力來完成農業生產,因此產生了對各種中間生產環節服務的需求,從整理土地、播種、施肥到收割等環節都出現了專業化服務的供給。這種現象在發達國家早已成為常態,比如有專門從事農田耕作的農耕公司,專業防治蟲害的公司,代為收獲作物的收割公司,承包家畜防役治病的獸醫公司等,這種在工業中普遍存在的分工日趨細密的情況也出現在農業的發展中(樊亢、戎殿新,1994)。
4. 分工的進一步發展: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目前農業規模化經營的主要方式包括:龍頭企業帶動,專業合作社模式,種植大戶模式等,從表面上看,規模化經營并不必然導致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比如仍然保持原有的中間產品采購渠道不變,仍然從同一生產服務商獲取各種專業化服務,但規模化經營卻內在地要求這些中間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更加專業化,這是由于:(1)交易費用的下降。規模化經營使得原來的多個農業經營主體變為一個,這大大降低了農業經營主體與其他服務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2)中間產品和生產性服務企業的分工和專業化有了成長的空間。在分散經營的條件下,這些企業往往需要經營多種產品、提供多種服務,實現規模經營之后,這些企業有了走向專業化的空間和激勵,完全可以提供各種專業化的服務。
除了規模化經營之外,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一步提高了農業生產的分工水平。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本質是產業鏈的延伸,隨著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不斷完善,各種農產品加工與流通企業大量涌現,1996年全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的規模為11 824個,1998年上升到30 344個,2000年發展到66 000個,其中絕大部分是龍頭企業帶動的(牛若峰,2002)。
三、 規模化經營與農村服務業的發展
農村服務業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生產性服務,消費性服務,公共服務。上述三方面的內容對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改善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影響,雖然農村服務業的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但仍遠遠落后于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同時未能實現與農業規模化生產活動的良好互動。
1. 農業經濟活動的分散化特征。目前三個層次的服務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生產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水平低,農民消費服務落后,服務手段單一,農村公共服務市場化程度不高,供給效率低下(張穎熙、夏杰長,2009)。針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政府政策,往往對三個層次的服務業進行分別處理,就事論事,沒有深入思考農村服務業落后的根本原因--分工水平過低,而分工水平又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這種有限的市場規模根源于農業經濟活動分散化的根本特征。
中國農業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集中化程度低,截至2013年底,全國農業合作社大約有98萬家,涉及農戶7 400萬戶,經營在5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為287萬家,平均規模200畝的家庭農場達到87萬家,還有30萬家各種各樣的產業化的經營組織。雖然合作社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平均經營規模并沒有顯著上升。生產活動的分散化導致農村的服務業難以實現集聚效應,技術、信息、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難以實現充分共享,每個農業生產主體都會在購買中間產品和各種生產性服務的過程中承擔大量的、重復的交易費用,這導致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難以發揮出來。
2. 農村服務業發展模式:“一對一”與“一對多”的比較。關于如何實現農業現代化,目前的爭論集中在兩條不同道路的選擇上:一是走規模化經營道路,通過土地流轉等方式實現土地的集中,二是在小農基礎上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兩種道路各有長短,規模化經營有利于提高機械化的效率,有利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但如果城市就業能力不能跟上規模化經營的步伐,那么農村將會出現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城市流民問題也會更加嚴重;互助合作的生產方式將小農經營與規模化服務結合起來,各種服務協會和組織可以使分散經營的農戶享受到各種規模化收益,這正是這些組織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但互助合作的經營方式面臨著巨大的協調成本和較高的交易費用,比如為了降低農藥的使用,轉向“有機”農業,各種互助組織可以發揮一定的指導和協調作用,但對農戶并沒有強制影響力,監督的困難導致農戶可能會出現各種機會主義行為。
上述兩種經營道路都能給予農村服務業一定的發展空間,主要區別是:服務提供企業與規模化經營主體之間主要體現為“一對一”的關系,而在小農基礎上的互助合作模式則體現為互助組織與農戶之間的“一對多”的關系。在“一對一”的情況下,農村服務業有著更為廣闊的專業化成長空間:從服務需求方來看,大規模的農業經營主體在選擇中間產品供應渠道以及各種生產性服務時,比如運輸服務、金融服務等,更愿意與一家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尤其是當長期關系建立起來以后,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費用,比如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價格調整成本等等,都會由于涉及較少的交易主體以及長期關系的建立而大大下降,此外,雙方長期合作關系的建立還有助于信用關系的建立,這對于難以獲得正規金融服務的農業經營主體來說尤其重要;從服務供給方來看,由于面對一個有著較大需求的農業生產者,完全可以專業化提供某項服務,同時提供多種服務不僅對資本投入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將導致企業無法通過專業化服務提供活動降低生產成本,因此,服務供給企業不僅有專業化的動力,也有專業化的壓力。
“一對多”的服務業發展模式鼓勵的不是專業化服務提供活動,而是綜合性服務提供組織。這種由一家服務機構向多家農戶提供服務的模式與小規模農業生產方式是相適應的,因為單個農戶從一家服務機構購買所有服務的成本要低于從多家專業化服務提供機構分別購買服務的成本,因此這種服務業發展模式在某些地區也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山西省永濟市的蒲州、韓陽兩鎮就活躍著一個提供綜合性服務的合作組織——“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這個農民自愿成立的農業協會不僅為農民會員提供基本的服務,比如農資購買,還提供技術推廣、合作金融、聯合銷售等服務,甚至還承擔著一部分社會功能,比如組織兒童夏令營、民間手工藝傳承、居家養老服務等(姜斯棟等,2015)。這種“一對多”的模式之所以也具有較好的發展成效,是因為農戶經營規模較小,從一個服務提供機構獲得各種生產服務甚至消費服務將會節省農戶大量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等等。但這種模式限制了服務業專業化和分工的發展空間,以蒲韓農協為例,其提供經濟服務和社會服務的業務范圍僅限于蒲州、韓陽兩鎮,如果要進行大規模的業務擴張,還要面臨如下問題:(1)更高的資本金要求。業務的大規模擴張要求設立更多的營業網點,同時要求雇傭更多的管理人員;(2)更高的管理水平要求。更大規模的業務范圍要求管理能力必須隨之提高,但這種專業管理工作往往會超出普通農民的能力范圍;(3)跨地區業務擴展的協調、信息問題。如果業務拓展到其他地區,如何協調不同地區的不同農民群體的需求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此外還涉及到信息問題,互助組織的管理人員可以充分利用“地域知識”來開展業務,比如可以依據對當地農戶信用的了解來提供金融服務,由于利用了近乎免費的“地域知識”,這種信息收集工作的成本很低,但一旦展開跨區域服務,則獲取信息的成本就將大大上升。
鑒于“一對多”服務提供模式存在的上述問題,服務業很難實現大規模擴張,而有限的規模則會制約分工的深化,而分工是否能夠進一步發展是決定農村服務業是否能夠走向專業化、高水平的根本因素,專業化和分工水平不能提高,其他旨在促進農村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只能在邊際上進行改進,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服務業落后的面貌。反觀“一對一”的農村服務業發展模式,規模化經營天然地要求相關企業必須提供專業化、高水平的服務,而不是綜合性的服務,分工和專業化不僅能促使企業不斷改進服務質量、降低成本,同時這些專業化服務提供企業也不受上述各種問題的困擾,比如可以不斷地將業務拓展到其他地區,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張可以承擔更高的管理成本,可以專門從事信息收集等工作。
四、 結論
中國城鄉之間存在的“二元結構”的表現之一就是農村服務業遠遠落后于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而農村服務業的發展與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有著重要關系,本文的分析表明:規模化經營更加有利于農村服務業走向專業化,而在小農基礎上的互助合作道路則與綜合服務提供模式更加匹配,但這不利于農村服務業分工的深化和專業化的發展。從長期來看,農業活動中分工的擴展空間確實難以與工業相比,但是服務業分工的深化和專業化的發展能使農業生產中“服務”的成分越來越多,將農業生產活動中原有的內部服務職能轉移出來,交給專業化的服務組織來完成,這對于農業生產活動和農村服務業來說是一個“雙贏”的過程。這正是“斯密定理”的力量,各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并不是解決農村服務業落后的根本之計。
參考文獻:
[1] Yang,Xiaokai and Jeff Borland.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60-482.
[2]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3.
[3]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Survey,in K.Arrow,Y-K.Ng, and Xiaokai Yang (eds),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London:Macmillan,1998.
[4] 樊亢,戎殿新.論美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J].世界經濟,1994,(6):4-12.
[5] 姜斯棟,崔鶴鳴,王小魯.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組織是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重要組織形式[J].比較,2015,(7):164-182.
[6] 牛若峰.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發展特點與方向[J].中國農村經濟,2002,(5):4-12.
[7] 向國成,韓紹鳳.分工與農業組織化演進:基于間接定價理論模型的分析.經濟學(季刊),2007,6(2):513-538.
[8] 許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變遷、特點及改革方向[J].世界經濟文匯,2008,(1):93-100.
作者簡介:王鐵成(1981-),男,漢族,河北省遷安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2013級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收稿日期: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