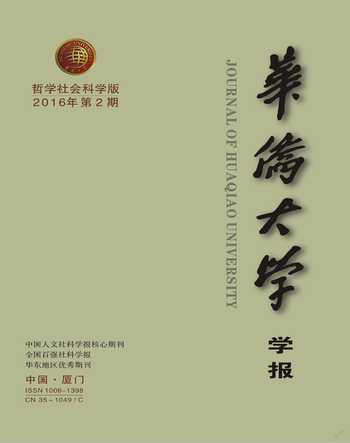中國經驗:海外華文詩歌的文化表征
摘 要:就海外華文詩歌創作而言,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經驗書寫存在的必然性。海外華文詩歌中內蘊的中國經驗內涵有二:一是指其語言、藝術表現等不脫中華文化的胚胎,這是中華文化的傳承性決定的;二是海外華文詩歌中的中國經驗與作者居住國的本土經驗相融,這是由創作主體的多重身份決定的,也是文化在異域傳播與族群傳承中必然伴隨的變異性決定的。
關鍵詞:中國經驗;海外華文詩歌;本土經驗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16)02-0119-07
一
新世紀以來,一些海外學者基于本土的華文創作實際情況,出于對文學創作形式獨特性的重視提出了一些主張。比如在他們看來,“不少新馬寫作人,從戰前到戰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學習某些五四新文學的經典作品”王潤華:《華文后殖民文學——本土多元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139頁。這使得這些文學創作沒有自己的獨特性,因此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有些學者提出要去中國化,弘揚本土化/在地化的寫作,像張錦忠即認為:“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馬華文學作者,有職責去尋找出和當代中國文學語言決裂的言說方式。”因為“海外的華文,總已是一種在地化的話語,一種道地海外的語文”。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中外文學》2000年第9期。另有海外學者擔心“中國性,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主體性,成為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為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張光達:《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史)觀》,《人文雜志》(吉隆坡)2000年第3期。
以上論斷反映出海外學者對文學自身、對自我生存境遇存在著一種焦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只要是以漢語作為工具的書寫,其中自然蘊含有中國傳統的因子,無他,只因為漢語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感染中華傳統文化的部分特質是情理之中的事,脫離語言母體文化的寫作,不僅不可能而且是不現實的。而擔心海外的華文文學喪失主體性也是沒有必要的。作為人類精神活動之一的文學活動,是一個包括創作、接受和研究等在內的復雜的自足自完的體系,在這個體系內討論文學的主體性,答案也相應變得復雜。20世紀李澤厚、劉再復等學者已初步建構了文學主體性的理論,但就海外學者的敘述語境來看,海外學者所說的文學主體性應更多側重于探討作為群體創作的、與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相對的,海外諸多國家與地區的華文文學的歸屬問題,即海外華文文學是不是中華文學的組成部分,能不能或應不應該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問題。不過不論這一爭論的最終結果是什么,海外華文文學中始終具有鮮明的中國性是無法抹殺的事實,而中國性在創作中的實際表現即是其中有關中國經驗的書寫。
海外華人的漢語書寫自其誕生之初起就已與中國經驗脫不了聯系。這里的中國經驗既包括由創作主體種族身份帶來的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積淀下來的中國經驗,即由集體無意識而繼承的那些屬于本民族的民族記憶、審美趣味等,同時又包括作為華人身份的創作主體在現實文化生活中不斷生成的經驗,這種經驗雖然是新興的,但因為創作主體的中國人的種族屬性,盡管新生代華裔的服裝可以改變、飲食習慣可以改變、語言可以改變,但膚色、種族是不能改變的,依然多少會帶有中國色彩。就如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雖然有不少華裔馬來語作者,他們用馬來語創作了不少作品,在作品中也吸收了英語、荷蘭語等外來語,但從文中雜糅的閩南方言以及漢語的表達方式來看,中華文化的影響清晰可感。
二
盡管在包括詩歌在內的世界華文創作圈內,中國的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無形當中自然形成一個以它為中心的創作圈,而在部分海外學者努力建構屬于他們自己的本土文學之際指認海外華文詩歌創作的最重要文化表征是中國經驗,并非是想強調中國文學中心論,就海外華文詩歌創作而言,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經驗書寫存在的必然性。
首先,作為文體的詩歌的邊緣地位與詩歌的文體特征決定了其中蘊藏著中國經驗。
中國文壇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詩壇曾經一度熱鬧無比,出現了朦朧詩、新生代、第三代、先鋒詩、后現代等眾多流派,但大多如曇花一現。在當代中國文壇,就文體發展現狀而言,相較于其他文體,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在新媒體中,詩歌創作人數、作品數量與讀者群都相當少,甚至可以認為詩歌是一種邊緣文體,詩歌創作已經成為一種邊緣書寫。這一情況在海外亦是如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海外的華文文學本身就是一種非主流的弱勢存在,面對他族的文化與話語空間,用漢語母語寫作也是華人在生存之外的一種邊際活動。而在華文創作的諸種文體中,詩歌亦是小說、散文之外的邊緣存在。
比如泰國的華文文學雖然在20世紀20至30年代,新詩的創作成就突出,但到了80年代以后,則是散文與微型小說成就突出。欒文華:《泰國文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65-170頁。而越南,在19世紀以前,越南文學直接受中國文學影響,進入20世紀,“這一時期越南文學仍然深受漢文學的影響,但越南漢文文學、喃字文學的創作逐漸衰落,淡出了文壇,繼之而起的是拉丁代越南語文學時代的新生”龐希云:《東南亞文學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印尼華文文學發展幾經波折,雖然出現了像白流、馮世才、黃東平、林萬里、袁霓、柔密歐·鄭、嚴唯真等作家,但因為印尼國家對印尼華人、華僑與華文有過較長時間的疏離排斥,華語一度被禁,用華文進行的文學創作發展也不是特別好。再如文萊,因1989年前沒有創辦華文報刊,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文萊的華文文學作家只能向離其最近的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地區的《美里日報》《詩華日報》等華文報紙的文藝版投稿。雖然從1989年3月“文萊留臺同學會寫作組”成立以后文萊的華文文學創作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像詩歌等創作依然是在初步發展階段。新馬華華文文學發展有起有落,盡管“總的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華文文學無論在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戲劇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發展”張旭東:《東南亞的中國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3頁。,但詩歌發展并不如小說、散文等文體。馬來西亞“由于華族地位的改善(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馬華文學開始走向振興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大量的文學作品創作出版,僅僅1986至1995年這十年,年均有50部各種體裁的馬華文學作品出版,總數達500部之多”張旭東:《東南亞的中國形象》,第204頁。但正如馬來西亞著名詩人吳岸說的:“我們曾有一些作品,包括詩、散文和小說作品,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如社會動亂、政黨斗爭、經濟風暴、華教處境以及移民事件等社會問題,但是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非常有限。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至今還未能產生既有時代性又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具有震撼性的文學作品。我們似乎落后于我們的馬來族作家,也不如我們的前輩作家在前一時代的成就。”[馬來西亞]吳岸:《馬華文學的再出發》,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1991年,第4頁。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外華文詩歌創作相較小說等文體發展相對較弱,這種存在的邊緣性一方面導致詩歌游離于文學中心之外,受到較少的注目與重視;但另一方面,邊緣性的存在狀態又保證了詩歌創作的純粹與情感的純真。詩歌是一種個體的自由意志投注相當強烈的文體。從詩歌的本質特征來看,中國傳統詩學對詩的本質特征有兩種觀點,一是“詩言志”,一是“詩緣情”。作為理想懷抱的“志”也好,作為“情”的個性情感也好,都可以統歸到廣義的“情”之下,這樣無論是“詩言志”還是“詩緣情”,抒情是詩歌的一貫追求與創作目的,詩歌作為私語化表征明顯的一種文體,強調的正是創作者獨特的內心經驗與情感表達。同時因為詩歌創作處在邊緣,詩人較少地負載時代賦予文學的沉重使命感,對生活的感受、對生命的體悟、對情感的表現、對細節的捕捉才可能更加細膩與真實,詩歌也因此具有強烈的生機,才能直抵人的靈魂與內心深處,詩歌也因此最大限度地保有主體的包括思想、情緒在內的本真性,詩歌中便有了屬于每個華人自己的體驗與經驗。
泰國著名華裔作家司馬攻說:“文化的吸引力包括:傳統、流行面、經濟價值,文字本身的科學化,文化母體國的盛衰等等。中華文化有數千年的歷史,占盡了傳統的優勢。至于其他條件,一百年來是漸漸地在失勢,尤其是最近的數十年,中華文化及華文(漢文),在海外地區更是很快地萎縮下去。幸得海外的華人、華裔,對中華文化的吸引力,除了上面所說各項之外,還加上情感及其他的關系,因此對中華文化的吸力是加倍又加倍。”[泰國]司馬攻:《文化的吸引力》,載《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380頁。司馬先生的這篇文章完成于20世紀,現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政府漢語國際推廣策略的全面展開,漢語在海外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增強,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漢語熱,中華文化及華文文學在海外的萎縮情況有了較大改變。而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海外華人華裔對中華文化發自內心的喜愛與親近是不會改變的事實,作為個人情感表達的華文詩歌內蘊作為中國人的情感與經驗就成為自然與必然。
其次,從詩歌創作主體與詩歌表現主體來看,主體“我”的存在、華人詩人的種族身份特點決定了詩歌即便是在海外文壇,也會內蘊相當多的中國經驗。
就詩歌中人稱的使用而言,詩歌中習見的是“我”這個第一人稱,詩歌中的“我”一般而言都是指創作者個體而非他人。有些詩通篇沒有出現“我”這一人稱,但讀完后我們還是能很明確地知道詩所表達的情感或描寫的事件是作者“我”的親身經歷,這就說明詩中暗藏著一個“我”。一般而言,“我”是極具獨裁性與主觀化的一種人稱,這種第一人稱的經常化出現表明“我”這一個人個體在創作者看來始終是第一位的,盡管這一個人個體同樣也屬于社會個體,但在詩歌中社會個體的一面常常讓位給個人個體。同時,又因為現代詩歌從形式到內容都缺少古典詩歌諸如格律、對偶等形式要素的約束,創作主體可以自由運用各種手段與形式只求充分表現自我、抒發自我,這樣就使詩歌表現出一定的主體自由與主體意志。海外華文詩歌在形式與內容方面較為靈活,對創作主體并無質的規定性。詩人可以選擇古體詩也可選擇現代新詩進行創作。但是形式的自由并不意味著海外華人作家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對創作素材不加選擇,相反,華人詩人作者對母語創作始終持有認真嚴肅的態度,有創作的自律性,他們堅持創作,有目標,會理性地擇選題材、體裁等。也是因為華人在思維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多少都會保有中國人的特點,因此詩作中自然會有帶有個人特質的中國經驗。
文學是一種創造,也是觀念的輸入。詩歌的目標應該是“心靈的藝術”,它采用的應該是知性的方法,而非理性的方法。當然,所謂“帶著鐐銬跳舞”有一定的道理,它指的是詩歌在遵循規律的前提下,自由地發揮。但總體而言,詩歌的作者既是形式的創造者(作者),更是意義的創造者。他通過他的藝術創作經驗向我們展示意義——作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關于作者心靈的本真的意義,關于存在的意義。盡管詩歌創作不能退出生活,否則詩就將是死氣沉沉、毫無意義的,而且對不同的詩人、不同的詩體來說,生活的面相當地寬廣,個人的生活、社會的生活、情感的生活、理性的生活都可以納入詩歌創作中。詩歌創作中的意象有些是常見的、具有直觀形式的,但更多應該是經驗世界中無法感知的、非實存的東西,比如愛情,比如某種我們稱之為情緒的東西。它們都是我們審美世界、審美觀念中存在的東西,而后者的出現更多于前者,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詩歌雖是理性的,但更應該是感性的。這種感性從本質上來說就在于它的主體性。詩歌如果說是寫景或抒情的,不如說是畫心,這個心就是詩歌創作主體的心。而在海外華人詩歌中即是身為中國人的赤子之心,比如澳大利亞詩人莊偉杰的《方塊字的祖國》一詩,表達的意思就很鮮明。詩人寫道:“寫祖國的詩篇/牛毛般多得不勝枚舉/就像祖國身上四通八達的大路小路/你算不過來/更像現代化大都市/密集的樓房/你無從盤點//我多想寫一首詩獻給祖國啊(寫了多年的詩卻未敢輕易下筆)/但我找不到一條通往靈魂出口的線路/也找不到一處可以讓自己詩意安居的住所//想想還是不寫的好,以免貽笑大方……搜索枯腸/想來思去/輾轉反復/我提醒自己不要如此這般自我折騰//其實 祖國就流淌在我們沸騰延續的血脈里/就在我們的五官感覺里在潛意識在夢境里/那是我們天天看著讀著摸著聽著書寫著的 方塊字//無論是一點一畫還是一波一磔/所有的線條都靈動構成為祖國的形象/哦祖國 屬于我的方塊字的祖國。”莊偉杰博客[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03db50100cek8.html那些身在海外的赤子始終不能拋卻的鄉愁在這里具化成一個個漢字,愛國的熱情找到傾泄的出口,而海外的赤子也找到一個心靈的棲居地。
第三,海外華人的邊緣社會地位導致了詩歌中具有中國經驗。
海外的華人在其居住國屬于少數民族族裔,華人也大多從事商業活動,很少從政,與居住國主流社會的融入程度不高,總體是處于邊緣化的社會地位之中。筆者認為:“當日常生活的被邊緣化程度越高,主體對自我處境的認識也就越深。這樣,當一個族群在另一文化環境中處于弱勢時,處于邊緣性的交流主體所有的文化自身的張力與彈性就會迸發出來,成為一種抵御他國文化的武器和捍衛自己話語權利的力量,以此保證自己文化與民族的獨特性,保全自己不被他國文化吞噬,成為沉默失語的那一個。從深層意義言,海外華人是用靈魂寫詩,以傳統中華文化作為載體,以此表現對文化中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抵抗和對文化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的認可。”沈玲:《流離散居 歸去來兮——讀〈莊偉杰短詩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2年第2期。所以印尼華人作家因巨大的政治壓力出現的“寫作焦慮”的表現之下就有更深層次的東西與悖論,即“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寫,那是來自族群之根的強有力的召喚;另一方面,他們又言不由衷,在敘述中所指與能指總是產生斷裂與分裂。實際上,這種文學的‘異質性就在于:它一方面無時無刻、不得不去迎合權力的召喚,另一方面又要頑強地堅守著本族文化的堡壘,一邊在忘卻,一邊在建構”王列耀、顏敏:《困者之舞——印度尼西亞華文文學四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6頁。
若就新移民來說,跨國的遷移使得他們經歷了一個脫離母體文化環境——剝離——試圖融入居住國文化——回歸的過程。移民在剛進入異質文化之初,因時間不長,尚處于不同文化交往的蜜月期,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并未產生,個體主體的母體文化與他本身仍融為一體,個體主體的文化身份意識并不強烈。隨著個體主體融入異質文化努力的加深,異質文化浸染程度的增強,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產生,個體主體意識到文化之間的深刻差異,意識到在與種族、民族相關聯的社會身份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從屬于文化的身份,而且這個身份根植于其社會身份所依附的文化,只有根據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它才能獲得意義。斯圖亞特·霍爾曾在討論族性認同問題時指出:“差異認同是新與舊的對立,其策略是從族性認同的差異建構為出發點去反思差異與認同之間的關系。族性認同與過去和歷史之間是建構關系,一種以故事、記憶、歷史敘事為基礎的文化贖救行為。”Stuart Hall.Ethnicity(1991).Identity and Difference.Radical America,轉引自姚文放:《審美文化學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49頁。當海外華人意識到文化差異后,個體主體的母體文化即從他身上剝離開來,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特征的符號,并在與不同文化差異加深的時候成為一種個體主體有意識表現自我、保護自我的力量。美藉華人作家嚴歌苓曾說:“在異國以母語進行寫作,總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邊緣的一個人。而只有此刻,當我發現自己被母語的大背景所容納、所接受;當我和自己的語言母體產生遙遠卻真切的溝通時,我才感到一陣突至的安全感。”嚴歌苓:《母體的認可》,《中國時報》,1998年3月30日第37版。澳大利亞新移民華人詩人莊偉杰說:“一方面,個人雖然希望擺脫固有的文化束縛,投入到一個以西人為主的社會之中,但由于語言、膚色、習俗等因素,使自己不得不依賴自身文化作為自我形象的扎根。”莊偉杰:《邊緣族群與“第三文化”空間——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華文文學為參照》,《華文文學》2003年第5期。馬華作家梁志慶寫道:“多少海外的中華兒女,雖然落籍為異國的子民,但是他們仍然向著民族和文化認同,知道有這條母親的臍帶,曾經哺育過他們。”[馬來西亞]梁志慶:《長城,我來了》,載梁志慶:《聽石》,柔佛南馬文藝研究會,1996年,第44頁。
語言是一種工具,同時,語言也是一種力量,當差異意識產生后,海外華人就會嘗試用漢語語言這種工具表現自身的處境、自我的欲望、未來的希冀和自我的愛恨愁傷。實際上,某種意義上,海外華人是通過華文創作來保持個體的種族身份,但因為身在異域,所以在創作中又不自覺地糅入其所生活的社會的文化,或者說是其所在社會群體的文化,而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個體種族文化身份的差異自然帶來的其他差異又會激發起海外華人對民族歸屬感、國家認同感等的自覺追求。就主題而言,無論是在東南亞華人詩壇還是在澳華、歐美詩壇,與小說、散文相似,有不少作品著力表現游子漂泊異國、思鄉懷人和羈旅行役孤寂的情懷。無論是懷鄉敘事的建構,還是家國想象的呈現、生存焦慮的剖白與抵抗,它們都是作為流散人的華人詩人在經歷流離之愁痛后的真實書寫。
海外華人詩歌與地理空間、文化邊界、族群身份相關,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沒有變得脆弱,相反卻變得更加突顯。因為文化邊界與身份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流動性。海外華人,尤其是新移民,初到他鄉,他們往往會通過詩歌或其他文學創作強化他們的文化身份與族群形象。因此,當其他藝術樣式可以剝離開創作主體的文化母體時,用中文創作的文學卻依然固守著作為身份象征的東方思維與民族認同。
三
海外華文詩歌中內蘊的中國經驗內涵有二:一是指其語言、藝術表現等不脫中華文化的胚胎,這是中華文化的傳承性決定的;二是海外華文詩歌中的中國經驗與作者居住國的本土經驗相融,這是由創作主體的多重身份決定的,也是文化在異域傳播與族群傳承中必然伴隨的變異性決定的。某種程度可以說,本土化書寫是中國經驗在異域的變形的外在表現。因為“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質,那毫無改變地置身于歷史和文化之外的東西。它不是我們內在的、歷史未給它打上任何根本標記的某種普遍和超驗精神。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不是我們可以最終絕對回歸的固定源頭”霍爾著,陳永國譯:《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載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22頁。
海外華文詩歌一方面體現出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作為華族所具有的本民族的思維、文化與生活習性等特質,另一方面,隨著海外華人在異域生活時間的持續增加,新生代華裔已日益融入居住國的文化中。與海外華文文學相伴相生的是多元的文化背景,伴隨著多元文化語境而來的文學書寫導致原先的個性化差異漸漸淡化,甚至發生裂變。文學創作從早期的僑民文學變成現在的華人文學,在東南亞詩歌創作中這一表現最明顯、最典型。“當代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與近代馬來亞華文文學的顯著區別就是:馬來華文作家的本土化意識增強,絕大部分的華文文學作品,不論是思想內容,還是文學創作技巧,都有著很強的本土化傾向,跟近代華文文學作品中的僑民意識相比已成天壤之別。”龐希云:《東南亞文學簡史》,第340頁。而“進入21世紀,文萊華文文學反映在作品中的本土意識增強,作者們開始把目光投注在自己生活的國土上”龐希云:《東南亞文學簡史》,第452頁。
盡管中國經驗作為海外華文詩歌的重要文化表征,但并不等于說海外華文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海外華文文學其實具備了故土與新土的雙重意義(也許這正是它與中國文學迥然有異的特質及其價值之所在),往往是兩者的摻雜交融,進而合為一體,即形成自己獨特的具有‘當地性色彩即本土化文學特色。這不僅是華人在海外生存的文化選擇,也是華文文學生存發展的基礎,更是海外華文文學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舍此就有可能失去其存在和生長的根基和價值。”楊匡漢、莊偉杰:《海外華文文學知識譜系的詩學考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36頁。
以泰華文學為例,筆者非常贊同泰國著名華文文學家司馬攻先生的觀點:
[GK2!2][HTK]現在泰華文學其身誰屬的問題,已經有了解答,泰華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它是屬于泰國文學的一部分。
……
泰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繼承和重建。它的繼承是立足于泰國的繼承,它的重建是在現實的情況下的重建。泰華文學要在泰國的土地上植根,就必須承認現實,適應環境。
雖然泰華文學屬于泰國文學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如果泰國的華文作者仍繼續用華文來從事創作的話,就不能脫離中國的文學傳統。避免不了受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在詞匯以及風格和體裁方面。泰華文學必須充分利用母體文化的文學財富,以及新的創作手法,這條文學的源泉是不能分割的。[泰國]司馬攻:《文化的吸引力》,載《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526-527頁。
海外華人詩人主張重回中國文學傳統之根汲取營養,對那些忘卻回歸的行為提出質詰:“我們現在有一種文化尋根熱,一直尋到三保山的墳墓里,尋到三皇五帝,到燈籠馬褂。但是在文學上卻很少人要尋回中國五四新文學與發韌于五四運動后的七十年歷史的馬新文學。馬華文學史展也舉辦過幾次了,但對今天的文學界,影響似乎微乎其微。這是為什么呢?難道那不是我們的文學的根嗎?”吳岸:《馬華文學的再出發》,第19-20頁。海外華人詩家在創作時也一直保持著對本民族文化與文學的關注、反思與批判,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作。在他們看來,“現代詩人的時代使命,不止于傳遞歷史的精神面貌,更要進一步深入探索現代人生意義,與人性在時代的輪轉中所激發的熱力與光芒”[泰國]李少儒:《畫龍壁》,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25頁。
海外華人詩人對中國傳統與本土傳統異同的認識相當清楚,如同樣是古典詩詞,“泰國的古典詩詞,與中國唐詩宋詞都有很大的相通之處,都是押韻的,但對‘起韻、‘承韻、‘尾韻,其繁富而彈性,極似中國的詞、賦、曲,不論‘獨句單元、‘雙句單元、‘八句單元都必須遵守固定詩的‘韻點與‘聯對的規約。”李少儒:《畫龍壁》,第26頁。“泰國的古典詩,多是一種延聲引曼的誦讀,又因為每首詩都有規定的‘韻眼,就很近于依照曲譜的‘吟唱。……中國對詩歌的朗誦稱之為‘美讀:從‘情動于中而‘形之以聲韻,詩語聲精,清流悅耳,所以說——朗誦是聲情的雕刻。”李少儒:《畫龍壁》,第27頁。正是在與居住國文學傳統的對比中,詩人對祖籍國文化傳統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當代海外華人在詩歌創作之初并沒有標榜以中國傳統詩學標準為標準,但在實際創作中,不少作者通過借用、化用、轉換等方式,不自覺地將傳統應用于現代詩歌之中,從而暗中顯示出當代詩歌藝術與中國傳統詩學諸要素之間的某種關聯性。而在現代與傳統對接過程中自然生成的審美空白則通過擴大想像、新增意象、情感深化等方式加以填補,從而使新生的詩歌變得豐滿與自足。可以認為,現代華文詩歌依然與中國古典詩學積淀而成的那些經驗連接,即便在海外,中國詩學的傳統要素也不曾隨著地域、時空的阻隔而成為被拋棄的那一個。
再進一步講,缺少傳統的滋養,不僅創作會暗淡無光,詩性精神無家可歸,而且存在的家園一旦失去,靈魂就會無處尋覓。當然,這并不是說,當代華文詩歌創作應完全尊崇并遵從中國傳統詩學的所有內在規定。這里,當代是一個時間的線性概念,作為當代文學中的一種存在,當代海外華文詩歌與這個時代共生,創作是一種當下的、真實的、活生生的行為,創新是其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必備要素,因此當代海外華文詩歌應當而且必須具有適應當代文學所需的新形式或新內容。中國經驗與本土書寫的連接與融合或者說傳統與創新的連接與融合是當代海外華文詩歌書寫中值得關注的特質。
【責任編輯 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