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死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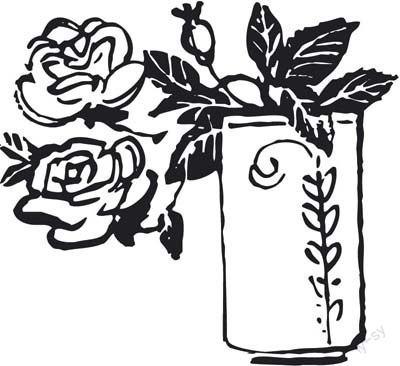
慈禧太后吃雞蛋
我們一般知道的慈禧太后,是威風八面的老佛爺,坐在金鑾殿上,垂簾聽政,只字片語就可以決定大清帝國的命運,乃至人民的身家性命。可是,這個擁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徽號的大人物,也曾因為剛愎自用,以至邦國瀕臨傾圮,本人則顛沛流離,朝不保夕,餓了兩天的飯,為之痛哭流涕。
慈禧貴為太后之尊,居然餓飯,還痛哭流涕,不是怪事嗎?沒錯,的確是怪事。不過,不能怪別人,要怪只能怪老佛爺鬼迷了心竅,耍弄著義和團打洋人,卻被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倉皇“西狩”(其實就是西逃)。當時任懷來知縣的吳永,出城迎接圣駕,見到的慈禧是“布衣椎髻”,化裝成民婦了。慈禧問他,縣城還有多遠?答說二十五里;問有沒有預備供應?答有。慈禧這才寬了心,說好,有預備就好,隨即就放聲大哭。
慈禧大哭,有兩個原因,都是由于委屈,一是逃亡了兩天,才有人來接駕,才有人理她。聽聽她是怎么對吳永哭訴的:“予與皇帝連日歷行數百里,竟不見一百姓,官吏更絕跡無睹。今至爾 (你)懷來縣,爾尚衣冠來此迎駕,可稱我之忠臣。”二是她實在又餓又渴,饑寒交迫,與乞丐也差不多了。吳永是這么記的:“太后哭罷,復自述沿途苦況。謂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有井矣而無汲器,或井內浮有人頭。不得已,采秫秸稈與皇帝共嚼,略得漿汁,即以解渴。”慈禧自己述說饑寒交迫,甚至連面子也不顧,直截了當要東西吃:“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且。曉間寒氣凜冽,森森入毛發,殊不可耐。爾試看我已完全成一鄉姥姥……今至此已兩日不得食,腹餒殊甚,此間曾否備有食物?”
她當然是餓壞了,才會在荒郊野外,向前來迎駕的小知縣討口飯吃。這吳永居然還真準備了一鍋小米綠豆粥,不愧是“忠臣”。
慈禧太后平時吃的是山珍海味,滿漢全席,極有排場的,吃個雞蛋算什么?可是在一百年前,庚子事變爆發,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倉皇西逃時,餓了兩天的飯,能得個雞蛋吃吃,真是勝過“玉食珍饈值萬錢”了。
吳永的 《庚子西狩叢談》 說他在懷來接到公文,言兩宮圣駕前來,要準備一桌滿漢全席,還要給王公大臣各準備一品鍋。懷來小地方,哪能提供如此奢華的宴席?有人建議置之不理,免得供應不如意,自取其禍。吳永想來想去,覺得守土有責,勉強置備了些食物,到城外迎駕,卻遭到敗兵搶掠。在榆林堡煮了三鍋小米綠豆粥,預備給隨從作點心,也被搶走了兩鍋。剩下的一鍋粥,本來以為是粗食,不敢獻上。慈禧此時已快成了餓殍,反應是:“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進。患難之中,得此已足,寧復較量美惡?”
于是,慈禧飽餐了一頓小米粥。不過,好像并不滿足,得隴又望蜀,因為李蓮英出來對吳永說:“爾 (你) 甚好,老佛爺甚歡喜,爾用心伺候,必有好處。”隨即就轉入正題:“老佛爺甚想食雞卵,能否取辦?”老佛爺喝完小米粥,想吃雞蛋了。好在她天縱圣明,體諒民情,知道滿漢全席是不可能的,退而又退,求其次而又次,提出了吃雞蛋的要求。
這吳永也的確是個大忠臣,擔負起兵荒馬亂中找雞蛋的重任。他在榆林堡中七找八找,居然在一家空肆的廚屜中找到了五個雞蛋。然后又生火燒水,費了不少勁,煮熟了五只蛋。最后覓得一粗碗,配上一撮食鹽,親手捧交給太監進呈。這一番努力,果然讓老佛爺滿意。李蓮英出來對吳永說:“老佛爺狠 (很) 受用,適所進五卵,竟食其三;余二枚,賞與萬歲爺 (光緒),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
什么好消息?慈禧一口氣吃了三個雞蛋,吳永勤王護駕有功,可以指日高升了。
情書與公函
章太炎在民國二年結婚,娶湯國黎女士,住在上海。此時民國雖已成立,袁世凱卻逐漸暴露其稱帝的野心,加以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國是日非,使得章太炎憂心不已。他聽信北京共和黨人的號召,以為聯合各黨的力量,仍然可以拯救共和體制,因此結婚才一個多月,便毅然離開新婚妻子,北上救國。然而,這一去便投入虎口,被袁世凱軟禁了三年。
剛到北京時,章太炎寫家書報平安,情意綿綿,卻用極為傳統的保守收斂文字,讀來十分有趣。全文如下:
湯夫人左右。不佞初十抵津,已有電報,十一早入京,駐化石橋共和黨本部。都下戒嚴,人情洶擾。聞南京又倡獨立,翻云覆雨。可謂出人意表。吳淞恐有大戰,家居務宜戒慎,一切可詢問嚴先生,庶無惶遽不安之事。夏秋代嬗,天氣新涼,宜自珍重。勿多啖瓜果涼水,開窗當風而臥。臨紙神馳,思子無極。章炳麟鞠躬。十一日夜。
現代人讀起來,是不是會感到別扭?怎么稱新婚的妻子“湯夫人”,稱自己為“不佞”呢?怎么落款是“章炳麟鞠躬”呢?豈不是冬烘先生寫八股家書,以高頭講章代替親昵的感情嗎?林覺民與妻訣別,都寫的是“卿卿如晤”,親愛的感情流露筆端。章太炎怎么板著臉寫家書呢?這怎么算情書?何來的情意綿綿?
像國學大師黨國元老章炳麟的話嗎?
然而,章炳麟的家書雖然沒有愛啊愛的字樣,卻實在是情意綿綿的。你看,他剛到天津,就打電報回家,一到北京就寫信。北京戒嚴,他就怕上海打仗,擔心湯國黎的安全。想到季節變涼,就怕她吃生冷鬧肚子,又怕她開窗睡會受涼。“臨紙神馳,思子無極”,不是刻骨銘心的相思嗎?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北京,長達三年之久。一九一五年九月,在北京陪伴他五個月的長女,抑郁自殺,使太炎十分激憤,在九月十日的家書中寫道:“仆則生趣久絕,加以悲悼,益不自支持矣。”又說:“兩日中連接浙中友人電報問安,蓋偽傳吾已死也。此雖虛語,然事實亦不相遠。吾人生死問題,正如雞在庖廚,坐待鼎鑊,惟靜聽之而已,必不委曲遷就,自喪名檢也。”
負責監視章太炎的京師警察廳大概感到太炎情緒不穩,怕出事,便在十月八日發了一封公函給太炎的夫人湯國黎,勸她以后寫信給太炎,“似應格外留意,多用慰藉寬解之詞,以開導其郁結”。京師警察廳致函湯夫人,是怕太炎再受刺激,用心可能是好的,但行文措辭粗暴無禮,更語帶威脅,完全鷹犬嘴臉。即使最初動機有一絲善意,公函的語氣則一掃其偽善的假笑,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信是這樣開頭的:“徑啟者。前因章太炎君患神經病癥,舉動乖張。政府眷念前勞,恐其罹于非禍,交由本廳特別看護,實出于保全太炎之意也。”是說章太炎有神經病,所以軟禁起來是為他好,是給予特別優待的保護。
“不意太炎先后徑寄女士二電,閱其詞意,異常荒謬,自非神經,別有感觸,安得有此種電文?”警察廳發現太炎有激憤之語,再次強調他神經病發作了。因此,要湯夫人多用寬解之詞來開導太炎,“使彼無所悵觸,庶幾悖謬言詞,不至形于筆墨”。否則,就開始威脅了:“否則擾亂治安,國有常刑。與其維持于后,曷若防范于先?”也就是說,最好勸章太炎少講話,不要亂講話,否則就嚴正典刑。等到出了事再來打點安排就晚了,何若現在就先防范著,別讓他胡說八道,“擾亂治安”?
我們很難想象太炎喪女之后的激憤之詞,如何會“擾亂治安”,但在京師警察廳眼里,這種感觸就有越軌的危險,以至發出公函,威脅湯夫人以后言詞要小心,否則……
蔡元培整頓北大
蔡元培新任北大校長時到處延攬人才,請了陳獨秀、胡適等人,并大力整頓北大的“腐敗”學風。據他本人在一九三四年寫的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一文說:“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他們平日對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 (興趣),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蔡元培對這種腐敗積習深惡痛絕,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說,就明確指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蔡元培不但開革中國教員,也開革有后臺的外國教員。當時不但有法國教員控告他,還有英國教員動員了英國駐華公使來談判,并威脅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蔡元培堅守學術至上原則,對各種社會勢力與輿論的明槍暗箭,一概置之不理。
我們贊揚蔡元培。至少要知道,他辦大學是有理想的。他捍衛學術的純潔,獨立與自由,義無反顧。
老舍在昆明
抗戰期間老舍到云南去游歷,大部分時間在昆明,其間也去了大理一趟。在他的筆下,昆明是很有情趣的。他跟音韻學家羅常培一道,住靛花巷,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鄰居有歷史學家鄭天挺、哲學史家湯用彤、愛唱昆曲的統計學家許寶骙,研究英國文學的袁家驊等等,又見到了聞一多,沈從文、卞之琳、陳夢家、朱自清……好像這條靛花巷是學術文藝中心似的。
老舍說:“靛花巷是條只有兩三人家的小巷,又狹又臟。可是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我看原因不是巷名的雅美,是這兩三人家,住的全是一時俊彥。就像劉禹錫說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不過,老舍說昆明的街名雅美,也有道理。靛花巷附近有玉龍堆、先生坡,都有趣。
老舍隨著羅常培下鄉,到了北大文科研究所住的龍泉村。這里又聚集了一批俊彥,馮友蘭、徐旭生、羅膺中、錢端升、王力、陳夢家、吳曉鈴,等等。快到中秋了,徐旭生建議,中秋夜到滇池去泛月,包條小船,帶著樂器與酒果,像蘇東坡游赤壁那樣,暢懷竟夜。商議了半天,毫無結果,因為:“一,船價太貴。二,走到海邊,已須步行二十里,天亮歸來,又須走二十里,未免太苦。三,找不到會玩樂器的朋友。”充滿情趣的計劃,沒能力實現。滇池月成了鏡花水月,不過,情趣還在。
最后,是吳曉鈴掌灶,大家幫忙,居然做了一桌可口的菜。在院中賞月,還有人唱昆曲,也是頗有情趣的中秋。
(選自《迷死人的故事》/鄭培凱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