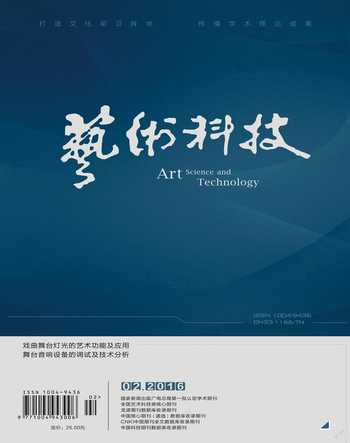基督教背景下伯格曼電影中的神話思維
摘 要:出生于瑞典的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他的一系列重要影片開辟了電影表現的新天地,展示出了電影藝術的新手法,對于現代電影藝術的發展和影視語言的革新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開創了“主觀電影”和“哲理電影”的先河。由于伯格曼受個人成長環境的影響,他的電影總是充斥著宗教意味,也使其作品有了其他導演作品所不具備的宗教內涵。本文將討論宗教背景下的伯格曼電影,探尋基督教文化和伯格曼電影之間的關系,解讀伯格曼電影中蘊含的神話思維。
關鍵詞:伯格曼電影;基督教文化;現代性
伯格曼出生于1918年的瑞典,父親是一位虔誠的路德派教徒,擔任過教堂和瑞典皇家醫院的牧師,母親是一位精通多種語言、教授法語的知識女性。在宗教氣氛中成長,對他日后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把自己對于生命的解讀表現在他的影片當中,并將基督教文化融入其中。
基督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對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基督教的世界觀及其經典——《圣經》中的題材、故事,甚至表現手法,都成為各個門類的藝術家創作的重要題材,電影也不例外。這一重要的母體更加深層次地體現在伯格曼的電影中。
伯格曼作為一個電影和戲劇導演,在他的電影里表現出了自我和一個時代的精神。更加可貴的是,伯格曼把他個人對基督教的思考融入他的電影中,挖掘人性、表現世俗的惡,追尋在當代西方社會基督教之于人的意義。在他的電影中,基督教的表現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們在探討多重主題之前,必須認識到伯格曼電影的三個基本的主題:存在的痛、個人的孤獨和失落感;生與死,善與惡的矛盾對立;人與上帝的關系,人在不斷的追求神靈。伯格曼在充當旁觀者的同時,對上帝的存在發出了無聲地質疑。這些主題和他的經歷是分不開的,白晝與黑夜、春夏與秋冬、歡笑與眼淚、睡眠與蘇醒、愛與恨,都通過極具風格化的作品展示在我們面前,凸顯了伯格曼電影個人化的色彩和他本人對基督教文化的深刻領悟。
1 “原罪”意識在電影中的反映
“原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據《舊約·創世紀》記載,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正是因為偷吃了禁果,違反了上帝的命令,因而被逐出伊甸園。從此以后,亞當的罪惡傳子傳孫,所有人與生俱來都有罪,這就是基督教所說的“原罪”。而在伯格曼的電影中,這種原罪意識集中反映在人物童年里。對童年的關注,以童年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是伯格曼電影作品的一個不變的主題,這和他特殊的童年經歷有關,也與他后來的電影觀念有關,即父母與兒童的關系,這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想法,使得伯格曼電影打上了風格化的烙印。在伯格曼的電影中,兒童總是生活在一個受折磨的天真世界中,被一群扭曲的成人包圍著,這些成人不愿意和兒童交流,由于對大人世界的不了解,兒童學會了用偷看偷聽來了解世界。于是有了電影中的獨特視角,兒童的好奇心和沖動使問題變得個人化。伯格曼電影中的孩子總是不斷地在試探,試圖了解這個成人世界并與之進行交流。從這一層面看,在伯格曼看來兒童的世界顯然比成人的世界要純潔得多。他認為,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兒童必須要去觸及成人世界的真實,要么向現實妥協,要么在恐懼和孤獨的陪伴下走向成年,直至孤獨終老。由兒童的視點切入成人的世界,并表達出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狀態,孤獨、痛苦、失落,急于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卻只能以悲劇收場,與社會的主流脫軌,少于交流的失落感等等,這些主題在伯格曼的大部分電影中都有涉及。即使是在那些看上去和孩子無關的電影中,也隱含著孩子對成人世界的批評,基督教的原罪意識也被詮釋得淋漓盡致。如果不是人的原罪,那么他們的童年是不是就可以快樂一些,陽光一些;如果不是與生俱來的原罪,成長的過程中怎么會有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堪?正是因為缺乏交流,兒童們才一次次地去探尋,從而引發不良的后果。這種內在的潛意識在《野草莓》《處女泉》《猶在鏡中》得到發展,并在《秋天奏鳴曲》和《芬妮和亞歷山大》中達到高潮。
1.1 生死對立的主題
關于生與死、善與惡的對立關系,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國的所有傳統主流敘事電影中,是一個無可厚非的二元對立話題。但是,在伯格曼的電影里卻有了另外一種獨特的表征,在他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如《危機》《夏日插曲》《處女泉》《芬妮和亞歷山大》等,并集中體現為人物在面對死亡時的精神世界和內心的矛盾糾葛,以此來構建出影片的戲劇沖突。由此可見,伯格曼偏愛的是人物的感情流露,他熱愛死亡,可是他又懼怕死亡,所以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都命運坎坷。伯格曼的主人公多半是中上層知識分子,教授、作家、畫家、音樂家、演員等等,透過人物的命運來描繪出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形象,并反映出自己對于人性的思考和現實世界的批判。不難想象到,一個從小就在牧師家里長大的人,一定從小就聽過很多的生死輪回的故事,他看著父親主持葬禮、婚禮和洗禮,看著人一出生就帶著原罪來到這個世界上,掙扎成長,結婚生子,最后死亡。死亡也是《圣經》的最基本的關鍵詞,關于死亡,圣經里說到三種,一是肉身的死亡,二是靈性的死亡,三是永遠死亡。《圣經》中這些關于死亡的論述非常具象地呈現在伯格曼面前。在《第七封印》中,騎士布洛克剛剛參加了十字軍東征回來,他認識到這場宗教的戰爭是多么荒誕,戰爭的毀滅感使他開始懷疑人的存在,然后他碰到了死神,并開始和了和死神的對弈。與其說布洛克早就意識到死亡一直在他身邊,不如說他對自身存在的懷疑使自己永遠擺脫不了死亡的陰影。布洛克試圖用理性超越死亡而感到罪惡深重,于是來到教堂,影片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騎士和死神跳起了莊嚴地舞蹈,他最終救出了魔術師一家,就好像是上帝的化身——耶穌,來承擔整個人類的罪惡。《呼喊和細語》則敘述了從瀕死的姐姐阿格尼斯到葬禮結束的這一段時間姐妹各自的生活,姐妹之間充滿隔閡,難以溝通,阿格尼斯企圖緩解姐妹之間的關系卻徒勞無功,直到她離開人世兩個妹妹才幡然醒悟。伯格曼大膽地深入人性里最黑暗的角落,直到人死之后才揭開這一層偽善的面紗,把觀眾帶進無盡的思考中。
1.2 在無盡的旅途中反思上帝的存在
“我的一生都在跟上帝的關系問題作斗爭,這些問題既折磨人也令人不快,信仰與信仰的失落,懲罰,恩典與拒斥,對我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1]伯格曼曾這樣說道。他在作品中不斷的論述人與上帝的關系,并且大膽質疑上帝的存在,這使得伯格曼的電影打上了哲學的烙印,從而也進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如果一個人信仰上帝,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不會有精神世界的痛楚,如果一個人不信上帝,又怎么去面對一個個抽象煩人的問題?而其中最為痛苦的,就是對于這種信仰的不確定感,作為一個公開的懷疑論者,伯格曼的世界觀正是以這樣一個不確定感為特征的。這種不確定感,在他許多影片中找到了發泄的出口。《第七封印》中騎士與死神的對弈,正是一個凡人對于信仰的大膽挑戰,騎士在信仰上帝與放棄之間掙扎,不斷地受到自己精神的折磨。他自言自語“為什么我無法殺死心中的上帝,為什么他要以這種痛苦的方式存在于我心中,即使我如此的詛咒他并想把他從心中驅逐?為什么,他什么也不是,只是我無法抖落的現實的幌子?我想要知識,而不是信念。”
與之相對應的是,伯格曼總是把質疑上帝的主題融入一段旅途之中。他的電影大多數都在講述一段旅途,在旅途的過程中,涉及他的個人思考:人與人的交流是否可能、自身的存在是否有價值、上帝冥冥中是否存在等等。影片主要以人的潛意識為對象,如《沉默》《裸夜》《羞恥》《處女泉》等。在《野草莓》中,觀眾看到了另一個在生命的晚年意識到自己荒蕪一生的人,伊薩克教授在路上搭載了兩個少年,一個女孩,那個女孩使他想起自己的初戀情人,他開始明白自己為什么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冷冰冰的、充滿野心的人,而兩個少年一個是神學學生,一個是醫學學生,他們一直在爭論上帝的存在。
關于上帝的結論,在伯格曼的許多電影里,只有在一個人物遭到打擊,以至于真的雙膝跪地屈從于上帝之后,對上帝的信念才能得到確認,這一點在《處女泉》中表現得最為直觀。女孩在去教堂的路上遭到強奸和殺害,這本身就是一種對于上帝的諷刺,女孩的父親發現后,他立刻拋棄了基督教信仰,成為一個發怒的異教徒,他不僅殺了那兩個牧羊人,還殺了他們的弟弟,盡管他與案件毫無關系。然后,他跪在女兒身邊,才意識到自己犯下了和牧羊人一樣的罪行,他跪下來向上帝禱告,女兒躺著的地方冒出了泉水。
總之,伯格曼從未停止過對于上帝的探討,無論是影片中的人物,如牧師、神學學生、死神;還是場景,教堂、鐘聲,他將上帝與信仰放置在了人與人之間,從而傳遞出一個極度個人化導演眼中的世界。
2 基督教文化中的神話思維與伯格曼電影的鏡頭語言
2.1 視聽語言的獨創性
基督教仿佛是人類給自己制造的一個幻影,從古至今,它左右著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反映在電影中,人性的問題也變得更加突出,這一切都是因為基督教的神話思維。基督教主張救贖,上帝為了拯救眾人,化身耶穌,為全人類背負十字架,用自己的鮮血洗凈人類的罪惡,并將上帝的真理告訴人類,使人類得到真正的救贖。除此之外,基督教的神話思維歸根結底是無罪的人升入天堂,有罪的人墮入地獄。這些都體現在伯格曼極度風格化的鏡頭語言中,《第七封印》開始,伯格曼不斷地進行革新性的探索,打破傳統的敘事方法,采取多線索的復雜結構。《第七封印》不僅繼承了傳統電影的手法,還吸收了德國表現主義風格。他把紀實性與繪畫性、神怪元素和生活的真實、哲理和隱喻結合起來,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雄鷹翱翔的畫面是與《圣經》的聯系,而黑白灰的色彩又映射出人物的內心,鏡頭中的騎士臉像雕塑一般,與死神平起平坐的對弈,表現出了時間、時空的對話。《夏夜的微笑》中,諷刺搞笑的情節,在蒙太奇的渲染下,成為遮擋傷口的工具,月光下的湖水和天鵝構成了極富浪漫主義的畫面。除此之外,伯格曼還使用鏡頭圈定人物的喜怒哀樂,人物的對話、獨白、手勢都十分夸張,表現出伯格曼對人物的關懷。《處女泉》采用了傳統的戲劇結構,通過緊張曲折的情節,尖銳的矛盾沖突,講究的畫面構圖,使得影片極富表現力,成為伯格曼少數令一般觀眾喜聞樂見的電影,而其中父親跪地的鏡頭更是背對畫面,引人深思,表現了對上帝無聲的控訴。
2.2 隱喻和象征的運用
隱喻和象征是伯格曼的重要表現手段,盡管他在自己的自傳中說,他從不運用象征。在《野草莓》中,“噩夢”象征著主人公末日的臨近,掛鐘沒有指針,表明人物的時間已經完結,指針對他已毫無用處。野草莓作為老人最喜歡的東西,象征著一切美好的事物:生命、青春、愛情、幸福、光明、理想等等。在《野草莓》中,伯格曼追求的這種超現實氣氛借由完美的攝影得到最好的表現,陰暗朦朧的照明、奇特的拍攝角度、色調的不斷變化,反映出主人公焦灼不安的心理。再如,《芬妮和亞歷山大》,作為伯格曼生命中執導的最后一部電影,一直占據著比較特殊的位置,自傳性的色彩有童年紀事的特征,也是處處充滿著隱喻。海倫娜和艾米麗的住所之間有一道門,象征著難以溝通的人際關系,劇院象征著與外界隔絕的世界,主教象征至高無上的上帝,艾米麗離開劇院的悲劇隱喻了伯格曼對宗教的看法,而那扇門在最后的時候打開,隱喻了人和人之間隔閡是可以被消解的。這不僅從宗教的色彩方面對人性進行了鞭撻,而且反映了救贖這一永恒的思想。
3 基督教文化對伯格曼電影的總體影響及其啟示
基督教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電影作為一門綜合性的藝術,承載著歷史,也寄托著未來,作為打量世界的一個窗口,它在某種程度上忠實地繼承著耶穌的主旨:引領人類走向光明。從基督教與人類的關系探索西方的電影語言,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有助于我們更好的認識宗教,傳播宗教的思想。從另一方面而言,世界大師們對于基督教的思考從未停止,從費里尼到希區柯克,從塔爾科夫斯基到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如此。而作為世界大師的伯格曼,其電影觀念典型代表著西方電影人對現實世界的困惑,是反思人類文化一個最好的表征。他一直在反復的思考,生命與死亡、性與死亡、上帝與死亡,在生存還是死亡的思考中,描繪出愛的真諦,闡釋出最普通的人生哲理。所以,伯格曼通過影像傳達的思考是其他電影人所望塵莫及的。他作為一位充滿了矛盾的藝術家,在電影的殿堂里,一直占據著一個不容忘卻的位置。他的作品伴隨他的一生凝固成了歷史,這既是他的影像歷史,也是他角色的歷史,同時,更是他自身的個人歷史。他一直走在自己所選擇的唯一道路上,通過光影書寫出自己的堅持和信仰,傳達出自己本能的思考,使幻想成為真實。他既說是也說非,祈求上帝的同時又辱罵他,使真理在謊言中誕生。他一生不斷的相信,質疑、肯定、否定,給電影藝術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他和上帝的“對弈”過程中,通過影像表達出了他對于所有世人歸屬感的擔憂。可以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伯格曼,他的思想意識源于基督教思想,盡管他的作品常常以反叛的思想出現,卻從未脫離基督教。所以,伯格曼并不孤獨。
參考文獻:
[1] 英格瑪·伯格曼.魔燈:伯格曼自傳[M].劉森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6.
[2] 英格瑪·伯格曼.伯格曼論電影[M].韓良憶,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3] 沈語冰.北歐電影哲人:英格瑪·伯格曼[M].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4] 邵牧君.西方電影史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 鄭雪萊,等.世界電影鑒賞辭典[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6] 約瑟夫·馬蒂.英格瑪·伯格曼[M].何丹,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7] 李娜.電影中的基督教主題[J].電影評介,2008(5).
[8] 林國淑.宗教背景下的英格瑪·伯格曼及其現代派電影[J].電影文學,2007(9).
作者簡介:張宇(1989—),男,甘肅天水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電影電視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類型電影和電影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