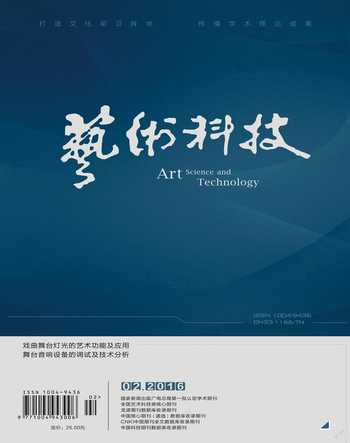對影視虛構的認識的變遷研究
白松旭 賈冬冬 張晨
摘 要:影視藝術其實如同傳統藝術一樣,都是以取材于現實的事物作載體,通過主觀的改造和創造來表達作者的思想。電影帶給人們的真實視聽感受,讓人們總是傾向于把影視推向技術分類,而不是藝術。人類確實經歷了不長不短的實踐和反思,才最終承認電影是一門藝術。在人類承認并發揚電影的藝術屬性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用先進的技術手段表達藝術思想,認清了人類自己的狹隘性在真理面前的渺小,僅僅因為對新事物的畏懼和對改變的排斥,就否認電影是藝術。即便是今天,這種狹隘性仍然在起作用,我們還是能夠看見很多以科學現實的視角來限制和批評藝術虛構的現象。因此,我們還處在影視虛構認識的一個過程中,只有借鑒曾經的歷史,才能讓我們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影視作品。
關鍵詞:影視虛構;觀眾認知;蒙太奇;審美心理
影視虛構意識的發展:
藝術創作不是模仿,不是復制,而是創造。影視作為藝術曾經被定性為機械復制的工具,被拒之藝術大門之外。影視所特有的技術性質,能夠為藝術家提供最有感染力的思想表達途徑。既然是一門藝術,影視的創作就必須帶有主觀性,作品需要取材于現實,但又不可能復制真實,藝術的表達需要虛構,更需要調節好虛構和現實之間的關系,密切實時地參考觀眾審美取向的變化。虛構和現實的沖突在任何藝術形式中都是必然存在的,這種現象往往會造成藝術參與者忽略藝術的審美這一首要功能,而用現實的、科學的角度來評判藝術作品中的虛構。虛構的程度取決于藝術欣賞者在借用可認知的現實來搭建作品的藝術性載體的需求,如果觀眾能夠通過虛構設計順利地理解作品,并觸及作品深層的藝術表達,那么此虛構設計便是合格的;反之,如果作品的虛構設計影響了觀眾欣賞作品的藝術性,那么此虛構設計就是失敗的。影視虛構的意識,經常被所謂的真實干擾,讓我們經常不能以自己的審美需求為第一訴求點來公正地評價藝術作品,人類對虛構的認識在影視發展史中,經過搖擺不定的過程,才逐漸趨于統一。
繪畫、雕塑藝術在發展為藝術之前,也都是以模仿現實為目的,人們把所見所聞盡量真實地重現出來。只不過傳統藝術作品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時間才能完成。因此,人們傾向于將有大量人力參與的創作活動歸類于藝術,而像攝影、電影這樣的由機器大量參與的創作活動,則自然不符合當時的人對藝術創作的理解。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帶有主觀目的而拍攝出來的作品,總是很有趣,總是具有獨特的意義。到了1916年,在電影出現22年之后,德國心理學家雨果·閔斯特堡出版了《電影:一次心理學研究》一書,這是人類第一次開始注意到影視對觀眾心理的影響,也是第一次論證影視具備藝術創作的條件。閔斯特堡指出:“我們的美學興趣集中到這樣一點,就是電影通過什么手段來影響觀眾心靈。”[1]這就是說,人類的藝術好奇心已經開始蠢蠢欲動,迫不及待地想使用這一新事物來搞出些有意思的名堂來。后來在1932年,德國著名心理學家阿恩海姆出版了《電影作為藝術》,阿恩海姆以電影形象與現實形象之間的差別為突破口,來證明電影是藝術。拍攝對象本身已經不再是首要受到考慮的。取代它的重要地位的是怎樣用畫面表現出拍攝對象的特征,如何闡明一個內涵的觀念等等之類的問題了。[2]阿恩海姆的研究把電影真正送入了藝術殿堂,人類終于承認了影視如同傳統藝術一樣具有巨大的藝術空間,也逐漸對主觀調整影視作品所產生的戲劇效果產生興趣。
隨后,匈牙利學者貝拉·巴拉茲進一步研究了電影影響心理的獨特魅力,歐洲又盛行了先鋒派電影運動,主張電影向繪畫學習,向文學學習。以現實的主觀視角來展現純粹的心理,如杜拉克的《貝殼與僧侶》和《一條安達魯狗》,里面充滿了肆無忌憚的個人幻想。
蒙太奇理論的出現給予了電影創作者理論性的虛構手段,蒙太奇的成熟,讓人們切實感受到了電影在畫面之外所能呈現的精彩。著名的庫里肖夫實驗最能代表蒙太奇所產生的夢幻效果,他邀請著名演員莫茲尤辛做的那個實驗,觀眾的反饋證明了畫面之間的租借能夠產生遠大于畫面內容本身的震撼效果。庫里肖夫的學生愛森斯坦將隱喻納入影片中使用,以符號的形式直通觀眾的內心,以一種切實地有效的辦法影響觀眾的心理。蒙太奇和符號是創作者通過影視虛構,在潛意識上聯動觀眾的創舉。
好萊塢戲劇化電影的出現促進了人們研究影響觀眾情感的方法的進程,好萊塢戲劇化電影包括的明顯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明顯的線性故事,善惡分明的人物設定等等,都是經過無數的實踐而得到的最直截了當地影響觀眾心理的手段。在今天看來,當年的好萊塢類型片雖然重復地按套路制作,沒有創新,但不可否認的是,只有做了分類對癥的研究,才是進一步將多樣化的主觀思想傳達給觀眾的重要保障,好萊塢戲劇化電影是影視虛構和觀眾心理研究的重要基礎。這一點很快得到了驗證,新好萊塢電影和歐洲紀實美學隨之出現。歐洲電影精于“找到故事”,好萊塢電影擅長“制造故事”,一個專注把夢幻變成現實,一個傾向把現實變成夢幻。[3]
在20世紀40年代,意大利出現了新現實主義運動,長期遭到法西斯國家機器壓制的意大利電影突然被解放出來,他們再也不想做自欺欺人的影片,他們對真實性的渴望達到了極點,提出了“把攝像機扛到大街上”的口號。柴伐蒂尼在《談談電影》一文中說道:“電影應當直接的注意各種社會現象,不要虛構(不管故事變得有多好);電影不排斥戲劇性,但是,是我感興趣的總是我們湊巧碰到的事情的戲劇性內容,而不是我們計劃好的戲劇性內容。”[4]巴贊還指出,攝影本體論完全不同于傳統各門藝術,因為傳統藝術都以人的參與為基礎,都是人工干預的結果,只有攝影和電影借助于先進的技術手段,才有了不讓人接入的特權。[5]當然,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產生的略微極端的主張。但即便是支持紀實美學的巴贊,也不完全反對虛構,他又提出,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的觀點,借此說明電影應當不斷地向現實靠攏,但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現實。
真實性是將觀眾引入影片的橋梁,它能讓觀眾識別影片,并快速在心里構建影片結構,能為夢幻般的觀影體驗提供條件。用心理學家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的角度來分析,就是觀眾會用自己的審美習慣去翻譯作品,同化作品,使之適應自己原有的欣賞習慣或審美趣味。另一方面,觀眾有追求新奇特的欲望,觀眾的審美心理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不符合自己審美習慣的信息,這就導致觀眾的審美心理發生了變異。[3]今天的影視藝術已經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目標觀眾的認知是影視藝術創作的舞臺,主觀的虛構不能逃離觀眾的認知范圍,優秀的虛構要在這個范圍里利用觀眾所認識的來制造驚艷觀眾奇幻。
參考文獻:
[1] 深度與運動[J].彭吉象,譯.當代電影,1984(3).
[2] 阿恩海姆.電影作為藝術[M].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53.
[3] 彭吉象.影視美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0,34.
[4] 柴伐蒂尼.談談電影[A].電影藝術譯叢[M].中國電影出版社,1957.
[5] 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