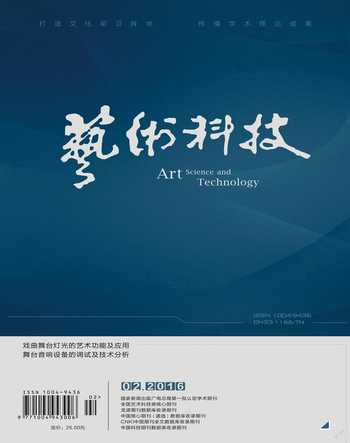網絡空間的社會研究
摘 要:計算機信息科學領域的知識生產,大多關切技術本身的推進,而較少從整體社會及文化的發展出發來建構研究問題。因此,文化觀念、情感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很難被納入既有知識體系的范疇當中作有效的討論。技術問題,同樣也是文化問題。為了強調網絡空間的生產性,本文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作起點,重新梳理了網絡空間的研究的理論問題。最后,本文以國內學者王洪喆對“草泥馬”文本的研究為例,說明特定文化的網絡空間如何被實踐和再生產。
關鍵詞:空間的生產;網絡空間;社會空間;文化與實踐
計算機的出現,對人類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大約在90年代初期,個人計算機走入中國的尋常百姓家里,并經歷了從撥號上網到寬帶聯網的技術完善過程。若起初的網絡使用僅僅算作人們的虛擬生活方式,那么,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起來以后,真實與虛擬的二分法顯然已經失效。如今,互聯網已經成為社會再組織和再生產過程的重要部分。然而,網絡作為生活方式的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仍存有距離。尤其在理論層面上,很多與互聯網相關的社會事件,都未被充分有效地說明清楚。這樣的困境,不僅與社會現實的復雜程度相關,也與知識生產的困境有關。
互聯網社會化研究的困境:
在西方的早期歷史當中,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出現,主要在自然科學領域彰顯了重大的意義。然而,在中國,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普及不單純是技術進步的象征,它還與后冷戰的歷史牽連在一起。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出現,提高了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機會和能力,也在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觀念當中,建構起了人們對現代化的具體想象和實踐。但是,對當時的中國百姓來說,計算機和互聯網都只是一種外在的、工具性的存在,而在今天,當幾乎所有的技術產品都能接入互聯網時,人們的工作、學習和日常生活,也在圍繞技術產品不斷重新組織。然而,計算機信息科學領域的知識生產,大多關切技術本身的推進,而較少從整體社會及文化的發展出發來建構研究問題。因此,文化觀念、情感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很難被納入既有知識體系的范疇當中作有效的討論。技術問題,同樣也是文化問題。
關于技術的理論主張大致有兩類,一類來自樂觀派,另一類是質疑派。樂觀派認為,互聯網與傳統媒介相比,有著不可超越的民主潛能。因為,同單向傳播的傳統媒介——諸如報刊、收音機、電視機相比,計算機及網絡能夠實現雙向的溝通,具有高度的公共性,代表了新的雅典民主時代的開創。①但質疑派以威權監控為例,質詢網絡空間的公共性程度。他們認為,網絡空間是圓形敞視監獄社會機制的延伸,因此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
然而,以上不同主張都受到了挑戰。當我們聚焦“阿拉伯之春”“查理周刊”等事件時,善惡二分的是非觀并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釋。樂觀派無法解釋為何互聯網審查在世界范圍愈發普遍且嚴苛,而不斷發生的網絡社會問題,似乎證實了質疑派的預見,但卻不能說明悖論為何存在。顯然,當下社會科學對互聯網的理解深度還不足夠。
就拿互聯網的諸多隱喻來講,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網絡空間的生產屬性的認知。學者胡泳曾說道,“隱喻會嵌入到我們的文化中,會塑造用戶對互聯網的認識,甚至影響互聯網未來的發展。隱喻因為彼此的不同會打架,這是一個斗爭的場域,每一個隱喻會在彰顯某些方面的同時遮蔽另一方面”。[1]在這里,“斗爭”指文化與權力之間的爭奪。然而,諸如“聊天室”“論壇”“圓桌”“郵箱”“翻墻”等隱喻,建構了“容器”一般的想象,這就讓互聯網成為了一類毫無生命的中性物質(neutral matter),如此一來,嵌在文化當中的權力關系被消解。因此,如何重新看待網絡空間的生產性?如何重建有關技術的社會生產理論?這些追問十分必要。
1 空間的實踐
若要談及“空間”時,人們往往要事先識別出空間的范圍和界限,并且人們對界限的理解,也主要是在物理或政治地理學的層面上作定義。若進一步推及至“社會空間”的討論時,識別界限的思維繼續發生作用。然而,在這些認識存在瑕疵,因它可能取消空間本身的生產性。在“空間的生產”被提出以前,社會空間被看作一個物質性的“容器”,它是歷史上演的物理場所,卻不與歷史形成因果關系。這種特殊狀況,在我們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有體現,就如我們能輕易找出生產歷史的時間詞匯,卻很難找到詞匯說清楚空間與社會之間的因果聯系。②
列斐伏爾的理論貢獻,讓空間與社會之間的因果聯系可被詮釋。他提出了空間的三個面向:“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性的空間”。這三個面向彼此參照,建立了辯證法。在這個基礎上,他還提出了社會空間、絕對空間等一系列概念。因此,在列斐伏爾的理論框架下,“空間”不再是中立的、停滯不變的,③“空間”成為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再生產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空間”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容器”,而是不斷被“生產”出來。
列斐伏爾強調“空間的實踐”,指人們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啟動了社會空間化的體驗。[2]因此,在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的解釋框架下,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將生產出自己的空間。這也是列斐伏爾對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進行分析的核心理論依據。
2 網絡空間的生產
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修正了以往的空間討論,但是,他提出問題的基點仍然是物理空間的研究。學者黛安娜·薩科(Diana Saco)將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推及至虛擬空間的分析。薩科同樣以生產的視角來看待網絡空間,薩科指出,當我們探索某一類特殊空間時,一方面,這種空間會不斷加固及再生產某種特定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也會暗示著一種新的空間秩序或失序狀態的形成,這些新狀況可能會反過來影響空間實踐的連續性。換言之,空間是實踐出來的,并且即便是在非物理形態下,這種空間的實踐也存在著。[2]
列斐伏爾本人也曾談及信息科學領域的問題,他認為,我們已有足夠的空間知識去質詢信息科學領域的空間生產,但不足之處卻在于,我們還不夠熟悉它,以至于不能充分地描述清楚這個領域。二十多年后,薩科認為,不僅是信息領域需要被更多了解,甚至關于空間本身,我們的認識也還不足夠。列斐伏爾所強調的是特定空間在歷時層面上的形成的過程,譬如資本主義空間歷史性的形成過程。然而,當我們討論虛擬空間時,則應更加關注在共時層面上的不同空間的矛盾關系。接下來,本文以學者王洪喆的分析為例,說明以上理論框架的展開可能。
3 不穩定的社會空間:以“草泥馬”事件為例
在《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一文中,王洪喆主要從傳媒理論的視角出發,考察了文本的原始涵意是如何在傳播過程中被改寫、遮蔽和占用的。作者以“草泥馬”事件為例,梳理出文本在傳播過程中,從“世俗性”轉向“政治”性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提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的建立。[3]
他認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是在互聯網審查機制、網絡語言與網絡亞文化、反審查等不同力量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草泥馬”為例,“草泥馬”起初并不針對某一具體的公共事件,而是被ACG愛好者(ACG,Animation,Comic,Game)娛樂的方式。然而,隨著“草泥馬”的文本傳播,它被不斷地重新闡釋、再語境化。最終,隨著更多西方媒體開始介入,“草泥馬”被迅速重建為自發的民間力量,又有崔衛平、毛向輝、郭于華等國內知識分子撰文,這些外部力量更加豐富了“草泥馬”的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的涵義。
盡管文本生產和使用的人群不同,但是最終達成了共鳴。作者認為,這一共鳴與后冷戰時期的霸權意識相關:它鼓勵道德冷漠、庸俗、埋頭于個人的生機、消費和其他私人事務。在這樣的背景下,互聯網同時滿足了人們參與和遠離政治的欲望,[4]從而構成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
綜上,學者薩科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對虛擬空間的研究,更加聚焦空間的實踐和生產過程。而學者王洪喆在對“草泥馬”事件的研究中,基于不同社會空間生產和矛盾關系,學者王洪喆提出了“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這樣的研究視角處理了空間生產的歷史斗爭關系。他的分析方法與薩科的理論框架不謀而合。這些研究視角具有啟發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和思考。
注釋:①這一觀點,由“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GII)組織機構在1994年公開提出。
②薩科在“Theorizing the Space”的章節中提到:起初,人們對“空間(space)”,以及與空間相關的概念,諸如“地點(location)”,很少進行問題化,好像空間就在哪里,不需過多解釋。當提問“什么是空間時”,可以尋求的哲學理論多來自于歐幾里德、笛卡爾和牛頓。拿空間和時間比較,則發現,關于時間的相關概念,更容易獲得因果聯系的認識,但是,空間就很難使用因果聯系的語言表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之下,列斐伏爾提“(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
③人們把歷史,即一種時間觀基礎的對人類社會進程的詮釋,看作是不斷變化,有各方權力正對且不斷流動的。但不同于歷史,空間卻常常被看作是中立的、停滯的。不僅僅薩科持有此觀點,在90年代左右,克里斯汀·羅斯(Kristin Ross)也提出了類似看法。
參考文獻:
[1] 胡泳.關于互聯網的10種隱喻[J].商業價值,2015(3):108-113.
[2] Diana Saco.Cybering Democracy:Public Space and the Internet[M]. 2002.
[3] 王洪喆.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J].二十一世紀評論,2010(119).
[4] 胡泳.眾聲喧嘩[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劉睿(1989—),女,陜西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技術,青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