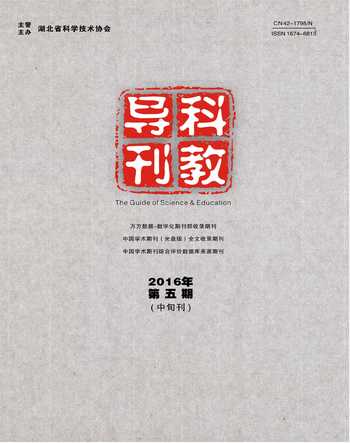《論語》“仁知(智)觀”探微
肖林珊
摘 要 《論語》仁知(智)觀,即《論語》中關于“仁”與“知(智)”的思想,主要內容包括:“仁”的內涵,“知(智)”的內涵及它們間的關系。在孔子以“仁”為核心的“仁知(智)觀”中,“仁”的本質是“愛人”,是成就其他德性的基礎,也是外在禮樂規范的源泉。“知(智)”既是意識對對象的把握,也是知識、智慧之意。“仁”與“知(智)”是統一的,“仁”統帥“知(智)”,“知(智)”促進“仁”往更高的境界提升。
關鍵詞 《論語》 仁知(智)觀 道德信念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6.05.080
Abstract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cept, that i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on "benevolence" and "knowledge (wisdom)",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benevolence" connotation, "knowledge (wisdo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Confuciu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benevolence (chi) concept, the nature of" benevolence "is" love ", is achievement other virtue based, and that of external ritual standard source. Knowledge (Intelligence) is not only the grasp of the object, but also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Benevolence" and "knowledge (wisdom)" is a unified, "benevolence" commander "know (wisdom)", "know (wisdom)" to promote "benevolence" to a higher level of improvement.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nd Knowledge (Wisdom); moral belief
《論語》是以記載孔子言行為主,兼記孔門某些弟子言行的儒家第一部經典典籍。《論語》全書共二十篇,一萬五千多字,是孔子思想學說的集中反映。雖然《論語》仁知(智)觀沒有西方哲學形式上的體系,但它有著實質上的思想體系。
1 《論語》釋“仁”
在孔子以前“仁”字的涵義是狹窄的,還沒成為做人的準則。孔子給予“仁”更豐富的內涵,涵義擴大,并創立以“仁”為價值核心的思想體系。這是孔子以前亙古未有的觀念,是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巨大貢獻。《論語》中“仁”的涵義非常寬泛,其中“愛人”(《論語·顏淵》)是其最本質涵義,也是其根本內容。“愛人”指人對同類的關心、同情與尊重,是人真實的心理道德情感。它發端于家庭內部、符合天性的親情之愛——“愛親”,這是仁愛精神和一切社會倫理道德的情感基礎,“仁”在這一情感基礎上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地推廣,把“愛人”推及到“仁民”。這是人性中善良的自然流露,是人性中發自內心的善念。
1.1 “仁”之本——愛親
“愛親”是仁愛精神和一切社會倫理道德的情感基礎。其基本內容有四:一對異性的愛;二對子女的愛;三對兄長的愛,即“悌”;四回報父母養育之恩的愛,即“孝”。其中“孝悌”是《論語》突出強調的重要品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正所謂“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①《論語》中將“孝悌”這一血緣之愛、自然之情視為仁之根基,善之起源。馮友蘭認為,孝悌是人的“性情的真的流露”,“這種真性情、真情實感……是自然的禮物。”②
《論語》中對“孝”的表述較多,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父引子繼。“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即父親在世時看他的志向,父親去世后看他的行為,能在長時間里不改變父親的行事處事之道,這樣就可稱得上是孝子。“道”指正確的、合理的“道”,這樣的孝利于人類社會代代相傳,符合人情世故。二是子不令憂。來自《論語》孟武伯問“孝”,孔子對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為政》)即父母愛自己的子女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子女應體會到父母的這種心情不讓其為自己擔憂。三是不違禮節。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不違禮就是不違由天道所及之人道,孝子應用禮來對待父母生命的全過程。四是恭敬事親。《論語》中,孔子對子游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對子夏說:“色難。”(《論語·為政》)其中的“敬”和“色難”都是強調真實的心理情感,要發自內心地親愛、關心、尊敬父母。
1.2 “仁”之推廣——仁民
孔子的“仁”是建立在血緣親情上的愛,并且是向外擴張的。《論語》有“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都是由“親親”層面進入到“仁民”層面的愛。在《論語》中實現“仁”的基本途徑是從身邊人出發由近及遠,從自身出發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由對父母的孝愛推廣到對長輩、上級的尊重和敬愛及對國家的忠誠等。“推己及人”思想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位置十分重要,康有為在《中庸注》中說:“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在《論語》中推己及人有正反兩種表述,正面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反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孔子正是想通過這種由遠及近,推己及人的富人情味的“仁”的修成方式,用“愛”將人與人牽引在一起,凝聚成充滿“愛”、人與人共同相處的理想社會,這是人性中發自內心的善念所期盼的理想社會狀態。
2 《論語》釋“知(智)”
“愛人”這是人性中善念的自然流露,但是《論語》認為人具備善良的品質還不夠,因為如果人只具備善良,很有可能會受到蒙蔽而陷自己于危難,或會做出出于良好意愿卻傷害他人之舉。因此要真正做到“愛人”,必須真正了解人,而“了解”則是《論語》中“知(智)”的主要涵義之一。《論語》中“知(智)”的含義主要有三,一是做動詞用,意為知道,了解,認識,領悟,是意識對對象的把握;二是知識,這是準確把握對象后,獲得的信息在意識中的沉淀;三是智慧,這是知識在意識中的升華,能夠進一步指導人的思想和行為。
2.1 意識對對象的把握
《論語》中意識對對象的把握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知道、了解、認識,“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矣。”(《論語·為政》)。二是領悟、體悟。在《論語》中,孔子更看重的是“領悟、體悟”,“領悟、體悟”也需要建立在“知道、了解、認識”的基礎之上。《論語·雍也》孔子從水的靈動與山的厚重悟出智者好動與仁者好靜的特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從滔滔不絕的江河之水中體會到時光的流失、生命的短暫,勸勉弟子珍惜光陰。孔子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體悟人生道理,培養仁愛生命的情懷與寬闊的胸襟。
2.2 知識
“知識”和“智慧”是通過“知”這一能力在把握客觀對象過程中經過思考和消化的所獲所得,“知識”在意識中沉淀,成為頭腦記憶的內容,孔子認為,不論從書本上學到的知識,還是從他人、社會和自然學到的知識,都必須有選擇地加以記憶。他對培養學生的記憶力也非常重視,《論語》有“溫故”(《論語·為政》),“月無忘其所能”(《論語·子張》),在他看來學到的知識若不認真記憶,當時過境遷即會遺忘以致后來無從記起,無從豐富自己的頭腦,無法具備廣博知識和多樣才能。
2.3 智慧
“智慧”不單純是對知識的記憶,而是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質聯系和規律,并達到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在意識中得到升華,進一步指導人的思想和行為。《論語》中有: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其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聞一以知十”正是達到了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的智慧。
3 《論語》中“仁”與“知(智)”的關系
3.1 以仁統知(智)
《論語》中,“仁”是全書的價值核心,《論語》中諸德均以“仁”為指向,“仁”統攝諸德,“知(智)”是諸德之一,自然毫不例外。如“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意思是放蕩不羈。《論語》中還有“知者樂水”“知者動”,“知者”一如“水”的特性,好動。但水沒有河道就沒有固定流動的方向,就會四處流溢。“知者”的思想沒有方向的指引,其“動”的特質若發揮到極致思想和行為就會放蕩不羈。“知”需要“仁”的統攝,才得以往正確方向發展。孔子還對弟子說過:“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意思是為人處世應以道為志向,以德為根據,以仁為憑借,活動于六藝。“藝”即才能,屬于“知(智)”把握的范疇。從此句可看出孔子認為“藝”的方向和依據是“道”、“德”、“仁”,孔子將這三者中與道德相關的放在“藝”之前,強調了“仁”對“知(智)”的統攝。孔子施教的目的是培養能夠治國安邦的人才,因此“仁”是孔子最為看重的品質,否則有“知(智)”無“仁”之人很可能會禍國殃民,“知(智)”必須在“仁”的統攝下。
3.2 以知(智)輔仁
在《論語》中,孔子認為“知(智)”對“仁”的養成有重要的輔助作用,“知(智)”對“仁”的輔助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是作為修成“仁”的途徑之一。達“仁”的重要途徑有:自省,博學,近思,是意識對對象的把握,可見“知(智)”對“仁”的修成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另外《論語》中有“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仁”這一發自善心的美好品質還需通過“學”完善,而“學”也是“知”其中一個含義,換言之“知(智)”可協助人往“仁”的境界推進。其二體現在人的智慧對德性的促進作用。如“知及之,仁能守之。”(《論語·衛靈公》)即只有首先對事物有正確認識形成的道德信念才會堅定不移,真正落實到現實的道德行為中。《論語》這些篇章中的“知”通“智”,即智慧。其三是在“仁”的踐行方面,需“知(智)”方不被愚弄。仁而無知(智)易被“善良”蒙蔽,有知(智)則不愚,不愚才可杜絕德的流弊。宰我認為仁者既然愛人,把“愛人”這一善心發揮到極致必然會舍身救人于患難,于是問孔子“如果有人掉進井里,仁者會為了救人而跳下去嗎?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修“仁”之人必須能通曉應變,不可陷入其中被人愚弄,不可茫然不知,“不可陷”與“不可罔”正是“知(智)”對“仁”在踐行中發揮的輔助作用。
由此可看出“仁”與“知(智)”之間是既辨證又統一的關系。首先“仁”為“知(智)”提供方向上的保證。按照孔子的教育思想“仁”確保人的行為堅定不移地朝著合乎道德的方向發展,即“茍志于仁,無惡也。”(《論語·里仁》)其次,“知(智)”對“仁”的修養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并在“仁”的踐行過程中發揮輔助作用。可見,“仁”與“知(智)”的完滿結合是孔子施教追求和培育人才的目標。
注釋
① 朱熹.論語集注[M].山東:齊魯書社,1992:2.
②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