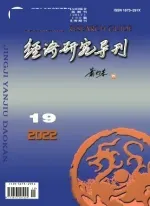中國古代勞動經濟思想探源
李巍
摘 要:從“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家入手,借助勞動經濟思想的基本理念,厘梳相關論述,從中挖掘我國古代勞動經濟思想產生的源頭,并闡述其對當代勞動經濟思想甚至經濟關系的啟發與借鑒作用。
關鍵詞:勞動經濟思想;中國古代;思想家
中圖分類號:F249.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2-0007-02
我國的勞動經濟學對古代勞動經濟思想的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為主,不存在勞動經濟思想產生的經濟和社會背景,直至市場經濟產生后方產生勞動經濟學。勞動經濟儼然成為一門學問,雖在近代,但其思想的產生有其過去的淵源關系,否則勞動經濟思想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有必要對古代勞動經濟思想進行溯源。
本文著重探索“春秋”“戰國”時期的勞動經濟思想,選取這一歷史時期的儒家主要思想家及其勞動經濟思想試作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勞動經濟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軻和荀況。從《論語》《孟子》和《荀子》中,我們可以窺見先秦儒家對生產、分配和消費等勞動經濟范疇的闡釋。
一、關于勞動生產與管理的觀點
農業是當時最重要的生產部門,而財富的創造者是“民”——勞動者,為了使社會整體財富增加,先秦儒家思想家無不對勞動者特別重視,提出了一些有關勞動生產與勞動管理的觀點。
義利觀是孔子一切經濟思想的基石,是了解勞動經濟觀點的門徑。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凡是不符合道義的利絲毫莫取,在求利的過程中要受到道德的約束,主張“見利思義”。
在勞動生產方面,孔子主張統治者在求“利”的同時要講“義”,即要施行惠民和富民的政策。核心觀點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一方面,從“小人懷土”(《論語·里仁》)方面看出孔子已經注意到土地生產資料對農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方面可以看出孔子在徭役上主張使農民不誤農時,以有利于農業生產。孔子的這種思想為后來的孟子所發揚光大。
在生產資料方面,孟子提出“恒產論”,以保證民(百姓)豐衣足食。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滕文公上》)這里的“恒產”主要指勞動人民的恒產,是勞動者能夠利用它可以生產出維持一家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資料。至于“恒產”的數量,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夫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畝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家之口足以無饑矣。”(《孟子·盡心上》)所謂“恒產”即指能維持八口之家所必需的五畝宅、百畝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桑樹、雞、豬等。有了一定的恒產,就有能夠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物質條件,孟子的恒產論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保障上較孔子更進一步。
在勞動生產管理方面,孟子較孔子的生產范圍遠遠擴大。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但農業要按照農時進行生產,而且其他的林牧副漁等領域也是如此。荀子也特別強調按照“天時”進行勞動生產,在《富國篇》中,孟子反復強調“無奪民時”“守時力民”“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后時”(《荀子·富國》)等,只有順時從事生產活動才能更好地發揮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提高效率。
二、關于勞動社會分工的觀點
孔子將勞動分為知識分子的智力勞動和勞動者的體力勞動兩種。關于智力勞動,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謀道”是指追求道義、落實道義,本身是一種腦力勞動;“謀食”是指耕種莊稼獲得飲食之類的體力勞動。二者是兩種不同的勞動,只不過君子所從事的是腦力勞動而已。
孟子對孔子勞動分工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孟子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這里暗示兩點內容:一是國家分“君子”和“野人”兩種。“君子”指一切脫離體力勞動的人們,包括國君、各級官吏、武士以及從事文學藝術、教育工作的各種文士。“野人”指鄉野之民,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二是孟子認為無論是勞力者還是勞心者,都是依靠各自的社會功能和社會需要而存在的,彼此是互相需要的,一個人不可能樣樣事情都由自己來完成。這可以通過孟子和農家許行的門徒陳相的辯論(《孟子·滕文公上》)中可以看出。此外,孟子認為,“君子”和“野人”的區別是“勞心”和“勞力”之分。他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勞心者”從事各種治國活動,是“勞心”的事,統治別人,應受別人的供養;“勞力者”從事百工、稼穡之事,是“勞力”的事,應被人統治,須供養別人。
荀子勞動分工的觀點在孔孟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荀子·富國》)荀子不但注意到了以腦力勞動為生的君子和以體力勞動為生的“小人”外,還注意到了百工和商賈之流:“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同時,荀子對因分工獲得財富給予肯定。
三、關于勞動分配的觀點
在諸侯和士大夫生產資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的主張。這里的“均”,并非主張將全社會的財富重新絕對平均分配,前面有“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之語,即按照“國”和“家”也就是諸侯國和大夫的等級地位均等分配,使臣民各安其分,和諧相處,既可以使社會穩定,又不會有亡國破家的危險。在勞動者生活資料的分配上,他提出了“足食”“所重民食喪祭”的觀點,認為百姓富足方能國家富足、政權穩定。
在分配上,孟子認同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對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現象極為反感:“皰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與百姓同之”的藏富于民的觀點,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孟子·梁惠王下》),盡量將天下財產平均分配。不但如此,孟子還提出了具體分配的方案:一方面,他提倡按勞分配,即按照“勞心”與“勞力”的不同進行按勞分配。對于“勞力者”,他們有固定的“恒產”,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取一份穩定的收入;對于“勞心者”,他們可以通過輔助國君治理國家等腦力勞動取得相應的俸祿與報酬。另一方面,孟子還提出國家救濟與救助的觀點:“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在春秋兩季視察春耕與賦稅工作時對“不足”與“不給”的地區給予適當的補助與救濟,這是施行仁政的一種,不可謂不是勞動社會保障機制的肇始。
在勞動分配方面荀子提出“明分論”,即“制禮儀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荀子·榮辱》)。“明分”就是通過禮來使貴賤、長幼、賢愚、高下等有所分別,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等級、不同的身份都擁有適合其階層的財富,通過這種“不齊”來實現“齊”的目標,這也是荀子的“維齊不齊”理論。通過各階層欲望的滿足以實現“上下俱富”的目的,這種分配當然是不均等的。在具體的分配策略上,荀子的觀點和孟子非常相似。一方面,他認為要按照自己的勞動來獲得相應的報酬,無論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農夫,還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士大夫乃至公侯,抑或從事商賈、百工這樣的勞動,都使勞動與他們的酬勞相對等。另一方面,荀子也倡導社會救助與慈善行為。他呼吁統治者將自己手中的財富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同時號召社會上的富裕之士慷慨解囊,行樂善好施之道,幫窮人解燃眉之急。荀子與孟子觀點的趨同性,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四、關于勞動力再生產(人口)思想
孔子在周游列國時,看到衛國人口眾多之狀發出“庶矣哉!”的感嘆,認為庶民是國家富裕的表現,相反“地有余而民不足”是一種恥辱,則應采取措施增加人口。第一種方法是孔子一以貫之的主張——施行仁政,使民歸附。“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論語·子路》)統治者尚禮、好義、崇信,那么四方人口沒有不來歸附的,這不失為快速增加人口的良策。第二種方法是促進人口增殖。提倡早婚,這是通過孔子主張的孝道來實現的。他強調:“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經·圣治》)“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孝經·圣治》)將繁育后代作為最大的孝道。至于婚姻的年齡,孔子認為,“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孔子家語·本命解》)孔子認為男子二十、女子十五就分別到了適婚的年齡,比西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禮·地官·媒氏》)分別早了十年和五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對增加自然人口的急切心情。增加人口對于發展生產、增加國家財富、提高國力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關于勞動經濟的觀點涉及勞動生產、分工、勞動分配、勞動保障等諸多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與包羅萬象,對后代及歐洲思想影響深遠,歐洲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就受其理論影響,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