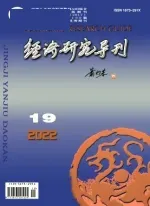花腰傣土地利用智慧研究
樊興麗 秦瑩 曹茂
摘 要:居住于紅河流域的花腰傣,長期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使花腰傣完整地保存著古代先民古樸原始的農耕方式。在千百年的生產生活中,花腰傣人民在稻作農耕過程、居住地選擇、村寨環境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花腰傣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實踐結晶,展現出了花腰傣在土地利用過程中的智慧。這些土地利用的智慧,對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花腰傣來說,仍然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關鍵詞:花腰傣;土地利用;立體農業
中圖分類號:F32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1-0027-03
花腰傣是傣族的一個分支,主要分布于紅河流域,大約有15萬人,比較集中于云南省新平縣和元江縣,其中新平縣約有4萬余人[1],是紅河流域的花腰傣最為集中地區。由于該民族婦女習慣于在腰間圍彩色的腰帶而被俗稱為“花腰傣”。花腰傣民族生活環境與西雙版納、德宏的傣族不同,長期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也沒有受南傳佛教的影響,保留了傣族原生的崇拜,封閉的環境使花腰傣完整地保存著古代先民古樸原始的耕作方式。花腰傣選擇河谷平壩作為居住場所,背靠青山面對江水,由此使得花腰傣的生產生活與其他居住在山區的民族有較大區別,形成了獨特的農耕文化,展現出花腰傣人民在農耕生產生活過程中的土地利用智慧。
一、稻作農耕合理用地
花腰傣居住于哀牢山中段東麓的紅河河谷,屬亞熱帶氣候區,雨季集中于夏秋兩季,雨熱同季,高溫高濕,冬春季則干旱。哀牢山河流水系切割較深,地面坡度隨河谷的深切而比較陡峭,是云南省比較典型的山地多平地少地區。花腰傣先民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根據高山河谷的地勢,依據地勢,開辟坡地梯田種植水稻。野生稻是水稻的原始祖先,中國至今發現野生稻有3種,在云南省都有分布,云南新平縣紅河流域(嘎灑江)就分布有疣粒野生稻[2]。花腰傣是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花腰傣與其他傣族一樣,主要種植糯米,在生活中也喜歡食用糯米。近年來由于提高糧食產量滿足市場和自己消費需要,糯米的種植已經逐漸減少。花腰傣人們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形成了以農耕稻作為主要生產方式、以稻米為主食的傳統生產生活習慣。
(一)因勢利導整地引水
花腰傣將坡地丘陵地帶改造成了種植水稻的梯田,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造河谷建設梯田是當地農業發展的一個關鍵,梯田之間互相溝通,田間修有道路,便于行走和運輸農作物。水田耕種,水的利用方式非常重要。要從溪流或水庫中引水泡田就必須先修通溝渠,花腰傣修建了相關的灌溉系統,將哀牢山上的水引到了梯田中。在放水泡田之前,各村寨都要組織人員清理溝渠、修補溝渠。花腰傣每個村寨都有自己的管水員來負責溝渠的暢通,形成了質樸的管理水利制度。土地最先得到開發的通常是便于灌溉的山箐邊,如新平縣花腰傣聚居的戛灑、腰街、漠沙、水塘一帶,最先得到開發的就是沿紅河西岸的平緩地帶,以及從哀牢山流入紅河的溪流兩邊。梯田農耕既是對坡地的充分利用,同時也能對水土形成保護。因坡地的自然傾斜,水土極易流失,尤其是雨季時節,大雨水流的沖刷,使土層流失更嚴重。修筑的梯田,形成層層疊疊的臺面,使水流得到緩沖,同時使水流里的土在梯田中能得到沉淀。水流從高處運送來的森林里的枯枝落葉、野獸的糞便等,是天然的肥料,提高了梯田的肥力。依地勢修筑的河谷梯田展現出花腰傣土地利用的智慧,增強了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花腰傣將那些水利條件好、土質肥沃的平緩低凹處的田地稱為肥田肥地,而將那些土層薄、灌溉條件差的山梁田地稱為瘦田或瘦地。哀牢山的花腰傣村寨周圍,自河谷至半山腰的梯田,形成了美麗的梯田景觀,具有較高生態旅游觀光價值。
(二)適應節令利用土地
紅河河谷雨量充沛、氣候炎熱,高熱高濕適宜種植雙季稻。花腰傣每年的農歷臘月和6月開始播種,早稻栽插后一般只需120天就可以收割,而晚稻至多150 天便成熟了,農歷的5月及10月收割早稻和晚稻。糯稻常作為6月后的晚稻栽種。由于桿葉表面生有絨毛,寒露和早霜只能在絨毛表面凝結,所以糯稻抗寒能力強。水稻屬精耕細作種植,蘊含了花腰傣人民土地利用的智慧。花腰傣是較早從事犁田、泡田、耙田的精耕勞作的民族,稻作文化構成了花腰傣社會文化的重要基礎。水稻在播種前要先平整和整理好秧田,整理秧田需泡田、犁田、耙田。
花腰傣犁田使用的傳統工具有生鐵鑄的犁頭,木制的犁架、犁檐。畜力通常是水牛,也有的用黃牛。繁重農活犁田由男子來承擔,男人們肩扛犁檐,手提鞭子,吆喝著水牛到田地上翻耕。犁田時將雜草、谷樁等翻入泥下,這些雜草、谷樁經過浸泡后腐爛形成肥料,提高水田的肥力。耙田使用的傳統工具是木制的,有單齒耙和雙齒耙兩種。耙田時牛拉著耙緩緩前行,人站在耙架上(雙齒耙)或用手按住耙手(單齒耙),已經被水泡爛的土塊,經過耙田就被整碎劃平。一般每塊田要耙2—3遍。犁田、放水泡田、耙田這3道工序相互交錯進行,最后一次就邊耙邊插秧了。每年農歷的5月及10月收割早稻和晚稻,割稻使用的傳統工具是鐵鐮。糯稻比其他水稻桿高,在收割季節,花腰傣為了方便收割,特制了木制的腳墊套在腳下墊高,在這個高度收割下的稻谷桿長度合適,便于下一步的稻谷處理。打谷用木制的摜盆,挑回的稻谷堆在土掌房房頂上,用竹制的揚扇或木制風車扇去茅草和秕谷。谷子晾曬到八成干后進行儲谷,最后是入倉,儲谷使用的工具有大木柜和竹蔑編制成大囤籮,在囤籮的里外用牛糞糊嚴[3]。
(三)立體農業生態和諧
花腰傣有稻田養魚的傳統,水田常年有水浸泡,為魚類的生長提供了條件。一般是在插秧苗結束后投放魚種魚苗。花腰傣喜糯食,種植的糯稻水田,由于糯稻桿高,不怕水淹,水位比較深,為稻田養魚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花腰傣也有稻田養鴨的傳統,在栽插的秧苗徹底返青之后,將小鴨放到稻田,任其自由入田活動。放養的鴨子吃掉秧苗上部分的蟲子和田里的雜草,利用生物多樣性原理控防稻瘟病;鴨糞便成為肥料,也為魚類提供了有機食物。花腰傣的稻作耕種形成了稻—魚—鴨良性循環的生態農業模式。大部分水田里都有田螺、泥鰍、黃鱔及魚等,構成了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經濟系統,例如,在嘎灑鎮曼李小組,實施了永久性稻魚工程30畝,著力打造稻田養魚示范區。
花腰傣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豐富的稻作文化,這種單一的經濟結構一直保持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現在花腰傣的坡地很多實行輪種,如新平縣大沐浴村水稻和苦瓜輪流換種,一塊田上半年栽種苦瓜或水稻,收獲后再種植水稻或苦瓜,實行了水旱輪作,既達到了傳統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又最大效益地滿足了經濟需求。此外,野菜采集作為稻作農業的一種補充, 不僅使花腰傣的食物種類豐富多彩,而且還可以節約勞動力和土地。生長于田間地頭的魚腥草、水葫蘆和田字萍為家畜和家禽飼料,也是花腰傣經常食用的野菜,它們具有清涼解毒的功效。田邊地頭的野菜采集方便,既有水土保護作用,又能構成物種的多樣性。
花腰傣居住于河谷平壩地區,以水稻種植為主,對于水的價值和利用有深刻的理解。因此,愛護環境、保護水源是其十分重要的傳統觀念,并形成大量種植果樹、林木的傳統。在每個村寨,都要選一片樹木高大、濃蔭蔽日的樹林作為龍樹。龍樹保佑著村寨村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畜興旺,這片龍樹是禁止砍伐的,砍伐是對神靈的冒犯,會給村寨帶來災難。在寨子里,會有一棵位于寨子中心的高大樹木作為村寨的象征,叫做寨心樹。寨心樹就是寨神靈魂的象征,大青樹、榕樹常作為寨心樹(寨神樹)。花腰傣的這種敬畏的信仰,形成了綠樹成蔭、枝繁葉茂的人居環境。花腰傣的每個家庭都有一棵家庭鬼樹,護佑著整個家庭的人丁興旺、五谷豐登;每個家庭都在家庭鬼樹的庇蔭下生活。家庭鬼樹有種在房前屋后的,也有種在田間地頭的,果樹類的較多,如荔枝樹、芒果樹、酸莢樹等。花腰傣種植林木的傳統,使村寨周圍植被、水土保護完好,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如新平縣的花腰傣聚居地腰街鎮傣卡南堿寨、漠沙鎮傣雅大沐浴村以及嘎灑傣灑大檳榔園等花腰傣村寨。在寨子內,到處看得到大青樹、榕樹、鳳尾竹、檳榔等,樹木高大,蒼綠碧翠。田間地頭有果實累累的荔枝樹、芒果樹、酸角樹、香蕉樹等。放眼望去,整個寨子被綠色景色覆蓋,營造了花腰傣特色的田園人居環境。花腰傣這種種植林木的傳統,既適應了紅河河谷干熱氣候,又能維護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實施,花腰傣地區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積極發展種植熱帶水果和蔬菜,如種植甘蔗、香蕉、荔枝、芒果等,在一些地區還引進了臺灣青棗、早熟優質葡萄等優質熱帶水果。積極發展冬蔬菜的種植,如辣椒、甜菜、豆類、瓜類等在冬季早熟的優質蔬菜。花腰傣利用土地的技能得到進一步提高,充分利用居住區的氣候環境,種植各種亞熱帶農作物與經濟作物,許多荒蕪的地塊都翻種上了各種經濟作物。
花腰傣在選擇村落的地址時,根據周圍環境的特性來進行合理的布局,要考慮到有森林、有水源,村寨一般都要背靠大山面朝江河。據說只有這樣村寨才能平安,村里人的生活才能豐衣足食。例如,新平縣的南堿村就是背靠哀牢山,前望紅河水,村寨建在地勢平緩、依山傍水的地方,在村寨的周圍修建了層層梯田,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的自然與人文融為一體的生態景觀。花腰傣居住的是土掌房,土屋頂、土墻體、土地面,冬暖夏涼,非常適于當地的氣候。土掌房的建筑材料主要是以土為主,直接取自于大自然。哀牢山及紅河谷地擁有充足的泥土資源,既能作為建筑的材料,也是制作土陶制品的材料。花腰傣住土掌房,使用土陶制品,如土鍋、土水壺、土碗、土杯子等。土掌房的建筑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拆除房屋時,土地又回歸大自然。花腰傣的土掌房背靠哀牢山,面朝紅河,充分利用山地地形,依山勢層層錯落分布,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塊塊平整的梯田。土掌房一家連著一家,房頂成了村寨人們聊天、串門的場所,增強了人際間溝通和交流。這種背山面水的選址使村寨與自然環境完全融合,順應水脈,保持水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態循環的小氣候,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4]。
四、宗教信仰敬重土地
花腰傣長期處于封閉的山谷地帶,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圍繞著水田稻作農耕,有相應的各種宗教活動。比如,每年的春耕時節,每個村寨要舉行春耕祭祀,祈求神靈保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祭祀活動就是祭祀寨神樹,寨神樹不再是一棵普通的樹,而是被人為賦予了超自然力的神樹,對村寨有庇佑作用。這是花腰傣每年最隆重的祭祀活動,第一次在農歷二月屬牛和屬虎的日子,第二次在屬馬的日子,殺豬宰牛,全村人在寨神樹下進行隆重的祭祀活動。儀式最后,全寨村民把避邪法器“達遼”插到秧田中。通過祭拜的行為活動,表達了花腰傣對農業豐收的渴望,也增進了人們的情感交流,以及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又如,農歷正月開始插稻秧,插秧的第一天要舉行“開秧門”儀式。每年農歷的六月初六日或六月十六日祭拜主宰糧食生產的土地神,土地神管農事莊稼,主宰著糧食豐收的還有其他神靈,如水神、田神、谷神、山神等。對這些神靈的祭拜,是人們對豐收的美好愿望體現。譬如漠沙鎮大沐浴村,每年各家各戶都要在江邊、水井邊、水缸邊殺雞祭獻水神,有了水,莊稼才能生長;祭祀田神,莊稼才能長得好;祭祀谷神,通常是用布袋裝上糧食,掛于糧倉的柱子上,家家敬奉;每年栽秧、收割谷子、谷子入倉時還舉行叫谷魂儀式。花腰傣認為,每一座山都有一個山神,要拿雞或飯菜等祭品到山前的一棵大樹或大石頭前祈求山神護佑獵人能打到獵物、山體不發生滑坡等[5]。再如,作為稻作民族,對于水田泥土的祭拜,是花腰傣農耕文化的象征和反映。水田泥也是房屋建造的重要材料,在取土之前,會先進行一些宗教儀式,請雅摩去水田里攆鬼。花腰傣人認為,取用的水田土必須是純凈的土,不能把水田里的惡鬼一起帶回,否則會對建房和居住的人不利,所以通過這個儀式來凈化取用的泥土。這些原始宗教中的祭祀活動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人們對獲得平安、豐收的良好愿望的反映。
土地既是農業生產主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大多數農民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花腰傣在長期適應紅河河谷自然環境的農耕生產過程中,積累了很多關于土地利用的智慧。這些智慧是花腰傣數千年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實踐結晶,對于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花腰傣來說,至今仍有實用價值。同時,秩序與和諧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思想智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保、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花腰傣在土地利用中體現出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正是我們今天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正確認知并合理利用花腰傣土地利用中的智慧,對花腰傣民族地區協調人地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崔明昆,楊索,趙文娟,周曉紅.云南新平傣族生計模式及其變遷的生態人類學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9).
[2] 朱慧賢,李紅梅.云南新平縣戛灑江流域的野生稻資源及其保護措施[J].安徽農業科學,2009,(2).
[3] 陶貴學.中國云南新平花腰傣文化國際研討會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 崔明昆.云南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的生態人類學研究[J].吉首大學學報,2004,(10).
[5] 柯賢和.新平花腰傣原始宗教信仰及變遷——以大沐浴村花腰傣信仰為例[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0,(12).
Abstract: Living in the Red River Valley of Huayao Dai, long-term in a relatively closed environment, make the huayaodai completely preserved ancient ancestors primitive farming methods.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huayaodai people in rice as the farming process, choice of residence, villag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these experiences are huayaodai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crystallization of practice, showing the Huayao Dai in land use in the process of wisdom, the wisdom of the land use, mainly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Huayao Dai, there is still an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huayaodai; land use; three-dimensional 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