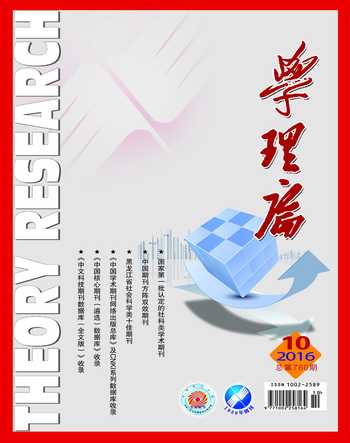司法改革——公正與效率之“弊病”與“診治”
方愛國 周燕
摘 要:公正是司法權建立以來最初的追求目標,追求人類最終的正義是司法存在的價值;而司法效率是指通過充分、合理的運用司法資源從而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司法公正與效率是司法改革的關鍵之處。
關鍵詞:司法權;公正;效率
中圖分類號:D920.4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0-0111-02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公正是司法權得以存立的主要價值,然而,緊隨著公正的另一價值導向——效率,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我國司法改革的目標著墨于司法公正,但是,沒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的司法活動卻是司法公正難以達至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兼顧公平與效率才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主要出路。
一、司法公正與效率的關系悖論
(一)孰輕孰重
公正作為司法權最初存在的價值且作為一直追求的目標而言,所有努力都是為實現人類的公平正義。從最初主張司法權從行政權中分立出來時起,就意味著司法權肩負著與立法權、行政權相異的責任。雖然這三種權力都是國家為了更好地管理社會,更好地體現公民意志,但相對于立法權與行政權而言,司法權更偏向于人民大眾一邊。因為司法權肩負著為人民的利益審查法律的合理性與可行性的重任,法權威的彰顯也要求司法權更好地擔當起為人民服務的責任。
經濟的飛速發展、快節奏的生活催促著人們用最短的時間去解決生活中的麻煩,因此,效率被引入到司法活動中。快速有效且最低成本地解決問題被大家推上首位,現代生活中的人們無法接受一個公正的結果需要等待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司法權不應該在等待中獲得最終的公平正義。因此,遲到的正義、非正義也被搬出佐證效率的優先性。
但是,公正是不可偏頗的一種司法價值,從法理學的角度來說,正義是司法任務,是司法權為之不懈努力的目標,而司法效率體現的是一種司法效益。兩者在司法權運行過程中并不是毫無關聯,司法效益彰顯著現代司法權的社會價值,司法公正承載著司法權的歷史價值。但是,孰輕孰重?
(二)孰是孰非
司法權一直閃耀著平等、正義的光芒,也時刻為人們從各種權力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努力,公正是司法權得以存在和運行的基礎價值。但是,在經濟社會中,平等的雙方才能產生交易,公平的交易才能產生共贏,公平正義如果不在市場經濟中運行是沒有價值可言的。效率,體現著利益當先,在單位成本內獲取最大利益價值,公平與效率利益大小,價值高低,不能一言以蔽之,也沒有一套完美的準則供參考。從歷史層面上來說,由于公正是司法獨立以來一直支撐并追求的價值,其歷史地位明顯高于由經濟社會的需求和人們價值觀的改變而產生的效率價值地位。
但是,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社會的進步也體現在司法實踐中,忽略社會對司法的作用,司法將進入孤芳自賞的病態之中并終將會被社會淘汰。隨著經濟社會的需求,追名逐利的緊迫感日益影響著人們對解決糾紛的態度。我們不可一味追求公正而忽略司法效率帶來的經濟效益,司法公正與效率無法用孰是孰非就能簡單判斷。
(三)孰先孰后
公正是司法權存在以來就追求的價值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減損其價值分量。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人們提升對效力的注重程度,故而那種認為公正是司法最高的唯一的價值目標卻隨著人們心中的那份利益訴求而磨損。公正是效率的目標,效率是公正的載體,兩者相互依賴,相互促進。
司法效率隨著近代社會的演變而逐步深入人心,散發著時代氣息的司法效率必然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在經濟學中,效率是現實生產力的基礎,公正在經濟學中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范疇,先有經濟基礎才談得上意識范疇。而從法理學角度來說,公正是司法賴以存在的基礎,公正優先于效率存在于司法中。因此,一味追求司法效率難免會造成公正的缺失,單從程序走向來說,一味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可能會跳躍司法程序而追求結果,不管結果是否公正,司法的過程價值或許已被司法效率所抹殺,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遭到忽視。因此,司法權并不能倚重一方而偏頗另一方,必須兩者都要“抓”,兩者都要“硬”。
二、司法公正與效率的改革弊病
(一)實踐性滯后
博登海默說過“公正具有一張海神般的臉,變幻無常,并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之下的公正是不同的。誠然,公正的基本價值是不變的,但在新時代要給予新解釋,方能為眾人所接受。有些價值理念在時代的渲染之下有了新的色彩,需要用時代語言加以闡釋才能為大眾理解和回應,也才能取得良好的司法效益。司法效益是指訴訟活動在滿足國家、社會及其成員的秩序、自由、公正等方面的需求時,所達到的最佳社會效果,它具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含義。司法公正如若在新時代里得到良好的實踐必然會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從價值層面轉向實際收益層面才是司法為人民服務的最佳狀態。
然而,前最高法院院長曾說過:“公正與效率是21世紀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這一個法治化的科學命題,其基本內涵是: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動,要做到審判公開、程序合法、審限嚴格、裁判公正、依法執行。效率作為審判工作的主題,必然擔負著樹立司法權威,彰顯司法進步的重任。但是,司法效率的提出與實際運用相差甚大,在追求工作“主題”的路途上實踐的滯后讓司法運行略顯尷尬。因為司法效率是在回應經濟社會的需求而產生,其在實際運行中沒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或者配套體系使司法效率步入正軌,加之原先的法院結構框架并沒有為司法效率的實現做出明顯而有效的調整,提高司法效率的實踐效果遠沒有司法效率的呼聲遠大。
(二)階級性尷尬
從馬克思的理論角度出發,法是由階級斗爭產生,必然有其階級性。法的階級性決定了法不可能絕對公正。但是司法權的設立是為了處理社會糾紛,以國家姿態居中裁判還人民最初正義,所以,司法權的社會屬性要求法必須公正,必須為社會大眾服務,為平等階層排憂解難。然而,階級性的司法權卻隱含著不公正,因為階級社會里無法做到人人平等,不平等的個體談不上公正對待,因此,法的階級性導致司法權的階級性繼而引出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正。司法權在追求公正的征程上,也只能做到相對公正,絕對的、永恒的公正是不存在的。
司法效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提出,既然效率引入到司法的運行過程中,必然得遵循司法運行過程的規則,這個規則是帶有階級性的人民而制作,有其階級性的本質屬性。然而,有階級才會有競爭、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和平時代的階級斗爭不是簡單粗暴的戰爭表現,合理有序的行業競爭卻能夠提升各自創造力。司法公正與效率因為其階級性的尷尬處境,似乎很難正名其應始終擁有著正義、理性之光。現代的司法改革也因此步履維艱,謹小慎微。
(三)意識性偏頗
時代的變遷、社會的更替,司法權在面對社會糾紛時能應付自如就必須面臨改革。司法公正與效率確定為司法改革的目標之后,司法工作人員便時刻牢記此目標,在工作過程中有意識地靠近目標,時刻提醒自己要以目標為標準進行工作。但是,司法人員有意識地下決心努力實現司法的公正與效率卻往往有失偏頗。我國長期以來的司法意識弊病已根深蒂固地存在司法工作的人員腦海中,面對新時期提出的新命題并沒有在實際工作中加以應用。正如上述提到在司法改革中并沒有為司法效率的實現做出具體的制度安排,制度設計沒有到位,實踐推行猶豫不決,人為的撥弄公正與效率這根平衡線難免偏頗。同時,人為意識層面的不穩定性和多變性與現今法院系統內的制度不健全、法官素質不高、固有的工作思路很難改變,無力保障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并行不悖。司法公正與效率難以深入人心,實踐中就難以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公正與效率只有在實踐中得以運用和有效調和才能彰顯司法變革的力度與深度。
舊有的制度理念在面對司法改革的新命題時有一個適應過程,司法權的運行在不同地域、不同人文情境中又呈現不同特點,所以這個過程不是大同小異千篇一律,不是短暫而是漫長。這個過程不僅涉及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面也包括司法結果的實際方面,不僅僅表現司法系統組織內部,也呈現在圍繞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實現而制定的配套制度層面;不僅僅體現在司法工作人員的意識層面,也涵蓋在司法運行的實際層面。
三、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對應措施
(一)理念更新與制度制定
我國傳統的司法行政合一理念在面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實現時進行有意識的更新與提煉。順應社會發展方向,把握司法運行的價值導向,合理有效地破除傳統的司法理念,接受并回應新時期賦予司法權的新理念。司法公正與效率作為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司法權獨立的基礎之上的。目前,我國司法權的獨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查收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律職責保護機制。”這昭示著法院審判獨立制度已經確定,那么司法權獨立問題已不再遙遠,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應當緊隨審判獨立的步伐,進入司法改革的征途。
“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司法制度的建立提出強有力的要求,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應該順應時代的要求,做出符合時代發展的制度變革,方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博登海默說過:“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能不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需要致力于創造秩序”。因此,在司法體制內部確立并健全效率制度是一種正義的追求,也是形成司法體制內部秩序的良好契機。
(二)價值的適當選取
價值具有多元性,不同的主體具有不同的價值標準與取舍趨向。在司法運作中,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所取舍的價值不同,刑事案件相較民事案件更加重大緊急,甚至關涉生命,此時如果追求效率必然會忽視公正,公正的實現需要時間證明,效率的等待是為了更好的價值實現。在美國和英國的刑事案件處理中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不管經過多長時間,人們也愿意翹首等待最終的正義。而在民事案件中,由于民事糾紛的繁雜且多樣,同一個事件會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糾紛,故而并不能將太多時間花費在同一件事情上,此時的公正并不能忽略效率。這就證明了公正不是永恒的、絕對的,具有多元性,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公正與效率在司法運作過程中,必須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制度的保障并不是硬性的不可變通,在能動的變化下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司法運行。
(三)司法資源的主動配合和有效互動
司法資源與司法效率的實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法院受理的案件僅僅符合立案條件,而隨著案情的進展需要的資料也越多繼而才能支持案件發展下去直至最后的明斷是非。在案件資料的收集過程中,不僅需要檢察機關的積極配合,雙方當事人的有效互動,更在于關聯的集團或者人物的支持配合。一個案件如果能快速準確有效地收集相關資料并運用將會縮短審理過程的時間,擴大到整個司法系統的案件審結時間計算,司法效率便會明顯提高。
司法資源的利用需要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主動、有效的互動,需要針對同一件案件同樣的辦案態度與辦案理念,力求積極地維護當事人利益。司法效率的提高不僅局限在審判機關內部,也需要在案件未送法院之前的其他機關的前期工作的妥當配置。
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在司法改革中不是一邊倒或五五均分的局面,而是天平的兩端,在面對具體個案時,偏向公正或者偏向效率都不是對正義的一種恰當解讀。公正與效率不是等同關系,沒有效率不等于沒有公正,而呈現效率也不意味著沒有公正可言,在波動中尋找正義的最高值才是公正與效率在司法改革中的真正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葛衛民.論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J].政法學刊,2005(12).
[2]王惠.論司法公正與效率[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2(1).
[3]■蒂生.論司法公正與效率的實現途徑[J].金陵法律評論,2002(2).
[4]王濟東.淺析司法公正的效率意識[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
[5]殷學儒,李偉茂.訴訟改革中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相關問題思考[J].檢察實踐,2005(2).
[6]萬鄂湘,從中美訴訟制度比較看司法公正與效率問題[N].人民法院報,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