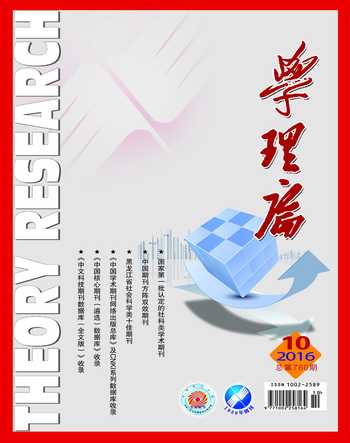港英政府時期香港民主探析
馮慶想 徐海波
摘 要:在港英政府管治的大部分時間里,受限于其政治建制無法消解的專制性,香港社會一直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直到20世紀中期,港英政府才漸漸推出形式民主,為香港民主發展提供了一定的養分。但由于缺乏大多數港人民主主體的參與,這樣的民主形同虛設。20世紀80年代,在中英兩國政治談判的歷史契機下,香港民主伴隨代議政制的快速推行,開始踏上迅猛發展的軌道。
關鍵詞:香港;民主;歷史
中圖分類號:D676.58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0-0146-03
香港民主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是香港特殊的社會歷史與迅猛的現代化發展相互作用的產物。本文以156年港英政府的政制演變為線索,把香港民主發展劃分為兩個歷史區間,依次呈現其變化脈絡。
一、香港民主的空缺與醞釀(1841—1982)
1.民主在香港的缺位
首先,港人群體缺乏民主意識的自覺。出于管治的需要,關涉民主的政治議題在香港社會中一直被港英政府視為“禁區”,“香港居民的順從和無可奈何的態度是支持現有權力結構的重要支柱”[1],因而,港人的現代民主意識與潛在的政治參與能力長期處于壓抑狀態。對香港社會大部分新移民來說,香港只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他們的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明顯,只關心經濟利益與自身的物質生活資料所需,并不在乎民主自由、權利義務、社會責任等政治話題與自身的關聯性。可以說,在大多數港人的集體記憶里,民主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空洞之物,它既沒有現實的民主生活體驗的銜接,也沒有傳統的文化情感的支撐。相反,他們的儒家政治文化情結深厚,間接成為抑制他們民主思想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英國管治的大部分時間里,港人的社會意識結構中并不存在民主的理性自覺,他們的世俗生活層面也缺乏民主存在的社會文化基礎。
其次,港英政府系統內外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英國自1841年占領香港后,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軍事大權于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權力結構的頂端,具有明顯的專制主義色彩。”[2]作為港英政府建制里的“民主功能”機構,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議對港督不構成任何的法律制約。由于港英政府建制的專制性、封閉性與排他性,港人議員長期在該政治系統中缺位,即使存在個別港人群體擠進港英政府體制內的民主秩序,也是沒有民主話語的主導權可言。作為民主外化的具體形式,民主咨詢脫離了民主自身內在的規定性,港英政府咨詢的對象并非絕大部分港人群體,而是極少數港人精英以及依附其政治體制輸送利益的買辦階層。因而,代表大部分港人的民意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民主渠道傳達到港英政府建制的權力頂端,也不可能在民主主體與權力中介之間建立平等對話平臺并形成良性互動的機制。可見,港英政府運行系統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吸納少數港人精英進入權力體制內,這種間接管治手段并非竭力于建構一個殖民主義的民主世界,而是在烏托邦式的民主外殼下遮蔽其專制主義的本質。換言之,它完全出于工具理性迎合社會管治的需求,是為自身合法管治清除輿論壓力與道德阻力的政治程序設計。因此,處于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無論是建制內還是建制外都不存在民主生存的土壤。
2.形式民主在香港的顯現
香港的形式民主最初顯現在二戰后港英政府提出的“楊慕琦計劃”,這份政改方案首次提出讓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和權力去管理自己的事務。但是,港英政府建制系統內部對香港政改的意見充滿分歧,并沒有實質行動。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初步展開代議政制改革,并就重大政策廣泛咨詢民意,吸引部分社會底層群體參與政治生活,為港人民主意識的塑造提供了一定的養分。與此同時,市政局先后發表《市政局未來范圍及工作特設委員會報告書》與《市政局地方行政改革報告書》,工作小組委員會發表了《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報告書》。這些報告書所構想的香港政改舉措勾勒出理想化的民主發展輪廓,客觀上為香港民主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它們觸及了港英政府建制結構變動的底線,最終沒有獲得港英政府的官方認可與推行。然而,港英政府不久在《市政局將來組織、工作及財政白皮書》中又對香港民主發展做出回應:“如果真要有新途徑,以便地方人士更廣泛地參與政府事務,順理成章的辦法是容許甚至鼓勵咨詢機構發展起來,使它們所產生的作用,能夠普及全港,而不是把更多的權力授予地區議會或市政局本身”[3]。民主形成的過程實質是絕大多數民主主體不斷獲取政治權力的過程,但從港英政府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謹慎保守態度來看,其不希望自身的權力發生轉移或受到制約。另一方面,即使港英政府設計出具有可行性的民主發展方案,假如沒有成熟的民主意識的支撐,那么所有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幻想也難逃破滅的下場。“民主意識的產生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先決條件。任何民主制度的構建都是以一定民主意識為指引的自覺活動。”[4]港英政府把對民主的主觀愿望投射在香港這個客觀沒有民主意識土壤的地方,顯然不符合民主政治發展的常規邏輯與一般規律。
從長期的民主意識的匱乏到形式民主的出現,無疑為處于醞釀期的香港民主發展提供了有益的養分與必要的條件,但是這樣民主表象只是為了掩蓋或暫時緩解英國管治與香港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它只能以虛假的形態存在,以虛假的方式傳達解決真實存在的社會矛盾的主觀努力,最終指向的是獲取占香港人口大多數的社會底層的道義支持,贏取香港民心的皈依,消解港人群體對港英政府管治秩序的逆向張力。進一步來看,港英政府自身并非民主政體,其內在的殖民主義性質決定了香港的形式民主的虛偽性。這樣“似是而非”的民主實際上是把英國議會民主進行“過濾”后,在意識形態的符號功能偽裝下,掩蓋了想象民主與真實民主之間的差距,潛移默化地誘導港人在概念認知、價值判斷、制度選擇與西方社會保持一致,實現民主主體在社會意識層面的同化,最終使得港人與英國管治方式相互妥協。因此,只要民主所倚靠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資源依然掌控在英國手中,港人所接觸的民主只能是民主的外殼,不可能擁有實質民主,也不可能擁有民主話語權,更不可能形成成熟的民主意識。
二、香港民主的形成與發展(1982—1997)
1.香港民主形成的歷史背景、組織條件與制度因素
香港民主形成的歷史契機源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中英政治談判。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奠定了香港前途的基本走向,這個歷史性轉折既是香港引入民主改革的時間窗口,又是推動香港政治主體性全面覺醒的導火線。香港政治發展自此被嵌入了民主價值的指針,民主政治成為香港意識形態中的顯性議題,港人的民主意識也日漸自覺與活躍。各種壓力團體、政黨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們都是民主發展的產物,也是民主價值寄存的物質形式與表達載體,港人的民主訴求往往通過這些政治實體得以實踐。這個時期,匯點、太平山學會、勵進會和民協等各種黨派組織陸續登上政治舞臺,為港人提供了直觀的民主觀感。但民主對于大部分港人來說是新事物,他們缺乏對民主的理性判斷與實踐經驗。因而,港人在這場民主思潮中明顯處于被動位置,他們更多地依附于香港社會中涌現的民主團體。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一反常態,極為主動地牽引港人所表現出的論政參政意向,在回應香港社會各個利益團體的民主訴求的同時,不斷加速代議政制在香港的發展進程。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提出逐步建立一個政制,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港人負責;1987年,港英政府對香港政制進行檢討,發表了《代議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提出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的意見;1991年,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機制;1992年,末代總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提出立法會的全部議席均由普選產生。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各種民主制度、政治組織與大眾媒介的出現,漸漸地強化了港人在香港民主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為香港民主的形成與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與外部環境。
從深層次來看,民主是歷史的,也是具體的,它產生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借助具體的制度載體、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培養民主主體的自由平等觀念,建構其政治責任與義務意識,塑造其政治行為模式。在各種民主制度對個體的政治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中,民主生活的實踐環節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轉化為“物質性”力量,推動民主的內在價值對民主對象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從而把民主秩序轉化為規約民主主體自身的一種規范。正如托克維爾指出,“民主制度就是要逐漸深入到人們的習俗、思想和生活方式”[5]。
2.香港民主飛速發展的緣由與動力
香港民主政治在九七回歸前的飛速發展是由英國內部力量所主導。“港英政治制度在英國撤退前的15年里,從港督集權、委任議局模式發展到三層代議政制模式;立法局從委任制發展到民選制,從間接選舉制發展到直接選舉制,從部分直選制發展到全部直選制,其速度超過了英國400年議會民主制度的進程。”[6]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本質是民主政治規律在香港所選擇的實現方式,但港英政府在香港所主導的“忽然”民主現象明顯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發展的階段性表現形式。它違背了民主循序漸進發展的一般規律,沒有充分考慮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以及民主主體的適應性,同時,它具有顯著的后殖民主義文化霸權意圖。“香港政府在1980年提出建立地方行政體制和在1984年提出‘進一步發展代議政制時,社會上其實都不存在這方面的強烈要求,發展代議政制,明顯的是與九七問題有直接關系。”[7]因此,這樣的民主改革本質上是通過政治權力關系的重構來置換長期的利益,可視為一種利益博弈的政治策略。它關注的核心是以政治動員和社會文化控制來影響九七香港政權交接后經濟利益在英國的分配;在可預測的政治結果下,為九七后香港民主發展的矛盾與分化埋下伏筆,也為激進民主政治發展做好鋪墊,從而“反哺”港英政制在香港社會的價值延續。換言之,普惠民眾、價值共享與權力制衡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但民主與民主對象之間搭建的價值關系剝離了民主內在價值維度,剩余的是抽象的民主概念范疇。代議政制本來就是民主表達的載體,卻異化為民主的本身,民主演變成一種宰制經濟利益、實現政治目的手段,而非超越具體價值的內在精神性追求。從長遠來看,民主自身發展必然要經歷“從手段到目的”的轉向,促使民主追求擺脫純粹作為政治和經濟生活附屬品的工具理性,回歸人本的目的,滿足人的高層次需求。但在世俗生活層面,由于超越價值維度的缺失,民主對于港人來說是一個可控變量,他們的民主訴求的目的性與指向性非常明確,追求民主并不是因為民主其本身的價值理念,而是取決于民主實踐是否有利于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許多香港居民不在乎有沒有民主制度;只要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能夠保持不變,便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8]換言之,在香港前途問題與港人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這個命題下,以民主方式保障經濟利益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九七回歸后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成為港人社會心理的期許與現實應對的策略,也是港人的政治實用主義得到實踐的一種現實方式。
香港民主的飛速發展背后顯然有港英政府的政治盤算。但不可否認,它在自身的擴張式發展過程中衍生了強化民主主體政治參與的激勵機制,客觀上激發了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與興趣,消除了港人歷來的政治疏離感,推動了港人對民主的原則、程序、選舉等形成較為理性的認識,在現實的政治實踐與情感體驗中助推香港民主的飛速發展。“總的來說,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內容和節奏主要由中英兩國政府和它們之間的矛盾所決定,但香港人所擔當的一定角色也必須予以肯定。”[9]
參考文獻:
[1]李明■.變遷中的香港政治和社會[M].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92.
[2]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
[3]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位置之戰——區議會的過去與未來[M].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5:5.
[4]吳家慶.民主意識——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助推器[J].湘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
[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357.
[6]劉曼容.英國對香港“民主發展”政策的歷史演變[J].廣東社會科學,2011(2).
[7]雷競璇.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M].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7:9.
[8]陳麗君.香港人價值觀念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227.
[9]劉兆佳:香港的獨特民主路[M].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4: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