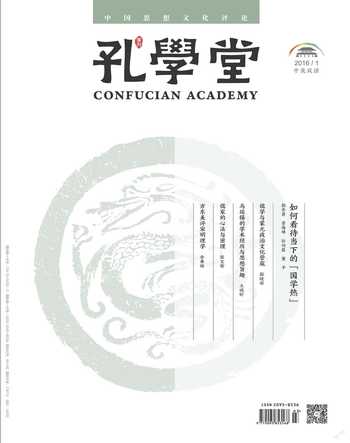朝聞夕可,不愧龍場
摘要:馬廷錫,學者稱心庵,與刊、應鰲、李渭并稱黔中王門后學“理學三先生”。心庵為學自始追隨陽明心性之學,尤以靜坐為其功夫,其歷學有三:一曰“師事朗州蔣信,講學于桃岡精舍數年”;二曰“與清平刊、應鰲等為性命交”;三曰“于漁礬構棲云亭,靜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然漁礬期間,心庵又以三事為其業志:一是教人功夫以靜坐澄心而體認天理;二是講學不輟而有“悠然自得之趣”;三是著《漁礬集》《警愚錄》,讀之使人卓然有“朝聞夕可”之意,以至于可以“不愧龍場”。
關鍵詞:陽明 心庵 蔣信 孫應鰲 朝聞夕可 不愧龍場
作者王曉昕,貴陽學院教授,貴州省陽明學學會會長(貴州貴陽550002)。
對于當今學者而言,相比較有關明代黔中王門“理學三先生”孫應鰲、李渭、馬廷錫之研究,對馬廷錫及其思想的研究尤為困難,其原因說來簡單,人們至今尚未找到其直接思想著述。除《黔詩紀略》中記錄的幾首小詩外,余幾皆為后人整理之“二手材料”,以為解讀馬廷錫及其思想特點的重要文獻:按時間順序,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五之《理學傳》,是迄今所見記錄馬氏的最初文獻;又有莫友芝于《黔詩紀略》卷四,除輯有馬氏三首詩作外,尚附有小傳,文字較詳;清人陳田撰《明詩紀事》,乃清陳氏貴陽聽詩齋刻本,其卷二十,亦輯馬氏小傳;民國以后,《貴陽府志》和《貴州通志·人物志》均輯馬氏小傳。這些文獻,所錄馬氏事跡大抵相符,語言表述略有差異,個別案例稍有出入,值得細致推敲。
郭子章在其《黔記》中盛贊:“當時龍場生問答,莫著其姓名,聞而私淑者,則有馬內江、孫淮海、李同野三公。云予嘗讀內江詩……真有朝聞夕可之意,嗚呼,可以不愧龍場矣!”子章所讀內江著述,今仍不見其傳,只知有《警愚錄》《漁磯集》名,而不知其物其述,如何會令子章有“朝聞夕可”之感慨,以至于“可以不愧龍場”?別的不說,足見內江為黔中王門之私淑者決不疑耳。按子章所見,其于馬廷錫所著《警愚錄》《漁磯集》,自然所讀一過,慨然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嘆,足見子章于馬氏二著之價值猶為首肯。莫友芝在《黔詩紀略》卷之四錄馬廷錫三詩前所附小傳,其中僅有“心庵著有《警愚錄》《漁磯集》,惜不傳”一語,更未予置評,留下諸般遺憾。
馬廷錫,字朝寵,學者稱心庵,貴州宣慰司人,《貴陽府志》載其“幼持性端方,舉止有異常人”,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中鄉試舉人。因曾知任四川內江縣,又稱馬內江。心庵知內江縣時,曾“洗冤澤物,甫二歲,即解組歸”。《黔詩紀略》云:“洗冤澤物以慈惠聞,遽棄官歸,講學不復出。學者稱心庵先生。”《貴陽府志》說他“選內江知縣,獄無冤滯,且多惠政。顧自以心性之學未澈,履任僅二年,棄之而歸”。之所以“履任僅兩年,棄之而歸”,文獻表明,心庵是為了從學于朗州蔣信而急于赴桃岡問學。心庵棄官奔桃岡問學蔣信的原因,郭子章《黔記》所述較詳:“貴州舊從學亦有往者。而心庵已謁選蜀令。在官嘗念所學不盡澈,每自嘆日:‘吾斯之未能信,無乃賊夫人之子乎?才二歲即投籍走桃岡,就道林居”。心庵原來就是道林提學貴州時的“舊從學者”,知內江時常常感覺自己“所學不盡澈”,于是決定棄官赴學。他決定問學于“心性之學”,這次赴學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主旨與學術趣向。無論郭子章《黔記》,還是莫友芝《黔詩紀略》、萬歷《貴州通志》、《貴陽府志》,述及馬心庵的學術經歷,皆有明確三段劃分的歷史記載:一是“師事朗卅l蔣信,講學于桃岡精舍數年”;二是歸黔后,“與清平孫應鰲等為性命交”;三則是“于漁磯構棲云亭,靜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一、師事朗州蔣信,講學于桃岡精舍數年
《黔詩紀略》不僅記載了道林師從陽明的史實,還詳細交待了心庵師從道林,如何從貴陽追隨至桃岡的前前后后。所謂“講學于桃岡精舍數年”之“講學”,到底是蔣信講學還是心庵講學呢?顯然是心庵自己講學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是聽取、參與道林講學活動為真。
這段經歷的大致時間,應從蔣信于嘉靖二十年(1541)任貴州提學副使起,至蔣信歿于桃岡之前不久。地點則是先在貴陽,后在桃岡。
道林是蔣信的號。蔣信乃陽明先生的親炙弟子。《黔詩紀略》記載了蔣信與冀元亨、劉觀時聞陽明謫修文龍場,三人從常德赴黔拜師陽明事跡:“王文成守仁之謫龍場驛丞也,見武陵蔣信道林之詩而稱之。時道林方為諸生,與冀元亨暗齋證‘大學知止是‘識仁體。暗齋躍曰:‘然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矣。而皆未敢遽是。”《黔詩紀略》里的這段話透露了如下幾條信息:一是蔣信三人此時已在陽明門下從學,“時道林方為諸生”;二是陽明對道林的詩作有所稱許,“王文成守仁之謫龍場驛丞也,見武陵蔣信道林之詩而稱之”;三則是更重要的一條信息:揭示了蔣信與冀元亨等在龍場從陽明先生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大學知止”的“知止”,就是要識得“仁體”。若要“識得仁體”,則《大學》中“定”“靜”“安”“慮”的功夫次第之至為核心的一條,就是一以貫之地“以誠敬存之”,其余“而皆未敢遽是”。
講求“定靜安慮”的功夫次第,他們從先師那里學修靜坐,此靜坐非為枯坐。《大學》功夫的“定靜安慮”須以“誠敬存之”,必得“以誠敬存之”方得能定、能靜、能安、能慮,終悟得“大學”之“知止”確確是“識仁體”。孔子之學必以仁為體,領悟其要,即識得仁體,這是自明道、陽明以后一貫的主張,亦是道林一向之所求。孫應鰲與馬廷錫皆從學于蔣信,孫在他的《四書近語》開篇引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又說“《大學》之要領也。格得此身,與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無有一毫疑惑障蔽,這便是識仁體。由此著實下誠意功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這便是以誠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學。識仁則大,不識仁則小。”
回過頭來,前面說到蔣信三人到龍場師從陽明,“相攜走龍場,受業文成之門。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三人回到楚中自成一派,亦即黃宗羲《明儒學案》所云“楚中王門”者。梨洲談及楚中王門之盛,以為大體由三個方面形成:一是由泰州流入的耿天臺一派;另一則是以道林、暗齋、劉觀時形成的武陵一派;再則就是徐愛《同游德山詩》中提到的幾人,不過這一派“尚可考也”。梨洲對此三派均有置評。
梨洲對道林為首的武陵一派給予充分的肯定,“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道林實得陽明之傳”。而對于由泰州流入楚中的耿定向一派,則指其“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黔詩紀略》的撰評者也認為“楚中傳姚江學者,雖有耿定向天臺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壞,不如武陵蔣、冀得其真醇。”道林與元亨輩如何得陽明真醇,待另文敘,至于蔣信后又從學甘泉,雜王湛之學而化之,則不贅言。
然馬廷錫從學道林,應視為接道林而“實得陽明之傳”,步武陵蔣、冀而得陽明真醇。他其實是先于貴陽,而后赴桃岡從學道林的。“心庵舉鄉后一年,道林以副使提學貴州,重整舊祀。陽明之‘文 明‘正學兩書院,擇士秀者養之于中,示以趨向,使不汨沒于流俗,教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時 學者翕然宗之,而心庵為之冠。”此時,蔣道林在貴陽教授了一批弟子,“為之冠”者當數馬廷錫心 庵。教學的內容當然是陽明所傳靜坐一類功夫,“使不汨沒于流俗,教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幾十年 后,心庵在漁磯教人功夫以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良知學脈,陽明真醇乃是。
道林還以事功啟示后學,“又置龍場陽明祠祭田以永香火”。為使貴州學子就近于鄉,時值“湖廣 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五衛,地錯貴州境,諸生鄉試險遠,多不能達,請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道林不久后以病告歸,“尋,告病歸。御使劾以擅離職守,削籍”。于是回到湖南桃岡,繼續授徒講學。看來與陽明一樣,熱衷于授徒講學,還真是道林一類學者的志趣所在,也得到了朝廷的理解與恩惜,“后奉恩例,冠帶閑住,筑精舍于桃花岡,聚徒講學,置學田以廩遠方來者。終日危坐其中,弦歌不輟”。于是貴州的學子紛紛跟踵而至,從學道林于桃岡,所云“貴州舊從學亦有往者”是也。據《黔詩紀略》,心庵并未在道林離開貴州時即刻前往桃岡,而是二歲后方至。當時“心庵己謁選蜀令”,顯然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官嘗念所學不盡澈”,每自嘆日:“吾斯之未能信,無乃賊夫人之子乎?”于是在蜀任官“才二歲即投籍走桃岡,就道林居”。
心庵于桃岡精舍從道林學,“即往師事之,居數載,心有所悟,乃辭歸”。《貴陽府志·耆舊》日:“朝寵師事道林,其學術猶為復絕,評者置之文恭、同野之間,夫豈多讓?”這段話語內含了三層重要的信息:一是進一步肯定了馬廷錫師從于蔣信的事實,“朝寵師事道林”矣;二是稱他因從學道林而致使“其學術猶為復絕”。“復”通“迥”,亦通“遠”。如說朝寵師事道林,而又學之迥異,顯然不通。故取“遠”意,以為通“原”長絕之意可順。“學術猶為復絕”的意思可作二解:一指朝寵接道林之旨長遠絕通,二指朝寵之學長遠絕通。誠然,“絕”亦可意為獨到,與前解總體上無大出入。至于將朝寵“置之文恭、同野之間”,此句也可二解,一解為三人有同等之學術地位,二解為朝寵之學位文恭之后,同野之前,排第二。筆者愿以前解為正說。其實,孫文恭何嘗不曾于師從徐樾之后,亦師從道林而往返桃岡數番。文恭曾記得有兩樁事情,明白地記載了心庵師從道林的事實。
第一樁,講蔣信于貴州提學副使期間,“貴陽馬廷錫從之游,粹然有成”。“從之游”一句,活脫脫顯現當年師生一路出入,有如當年孔顏洙泗一般的教學互動之活潑場景。
第二樁事頗讓人咦噓而充斥著吊詭,說的是馬廷錫有一書信致道林,為應鰲所睹。此事發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之前三個月,孫文恭以公事至辰州,歸來專道武陵,赴桃岡拜望道林,“侍蔣信桃岡三日,與論學”。三日后回黔。三月后文恭又返桃岡。短短三個月,誰想桃岡己人去日非。就在孫應鰲返回桃岡的前十日,道林先生己然長逝。就在道林的逝榻前,應鰲親手拾起了馬心庵委托貴竹汪君若泮帶給道林先生的書信一封。此信不僅證明馬心庵師事蔣道林的事實,且證諸師徒間常以書信來往,相與論學。雖然此封書信于今不存,但于應鰲當時寫下的《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志銘》中,準確記載了此樁事情的前前后后,以及所涉諸多學人學實:
歲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桃岡三日,期蒞官之便再侍焉。逾三月,某以蒞官,復道武陵,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壽七十有七,感疾時,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作詩二首,歌詠傳性傳神之微。貴竹汪君若泮,持馬君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月曰:“我化,柳孟卿侍我久,撰我行;志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瞑目衣冠端坐逝……始先生少與暗齋冀公元亨友善,交砥礪己。及陽明先生自龍場謫歸,先生見焉。陽明謂冀公曰:“作顏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噦血,于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默坐澄心,常達晝夜。—旦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盡屬一身,呼吸恫瘰,全無隔閡,虛白盈室,溘然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內外之旨,此身與萬有流通之旨,自悅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渙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后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契合,隨侍甘泉于南雍。
馬廷錫在貴陽文明書院、正學書院師事道林,早為確定無疑的事實,之后在知內江二年畢,又親赴桃岡從道林學,也為確定無疑的事實。無論是在貴陽還是在桃岡,心庵從學道林皆頗有心得,《黔詩紀略》錄心庵《登山》詩一首,抒發了他對學習的深刻體會,他把學習比喻為登山臨海,必須確立高大的志向,懷抱不懼艱險的巨大勇氣,雖然付出,必有所獲。他在詩中還寄寓了對老師的無比之崇敬和深切之緬懷。
郭子章《黔記》中還記載了道林先生向心庵講授心性之學的情況。道林示云:“萬物一體之義,不當求之于靜中光景。人與萬物同于宇宙胞胎中,何有彼我之分,為心所蔽,故只見得爾為爾,我為我。若心中澄然無物,便知宇宙渾然無物無我,此心便無物不貫,故學只在胸中無物耳。自今吃緊一著,只在澄心上用功,不必想象模擬也。”道林于黔中講學時,即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旨傳于弟子,而今又以“萬物一體之義,不當求之于靜中光景”示心庵,這一進路顯然與當年陽明示辰中諸生“求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之情形相況。不知心庵后來在漁磯教人靜坐時,是否接續了乃師教諭,此為后話。道林在龍岡師從陽明后,又于湛甘泉門下問道于“隨處體認天理”之旨,其云“人與萬物同于宇宙胞胎中,何有彼我之分,為心所蔽,故只見得爾為爾,我為我”之義,已與陽明“心外無物”之義相異,由此可以看出,作為楚中王門之冠的蔣道林,在他晚年傳播的心性之學中,已然包涵了較多甘泉成分。心庵后來身為黔中王學殿軍自所不疑,但明中后期各個學派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情形,實為常態。
二、與清平孫應鰲等為性命交
如要準確地說,心庵在道林那里學習了幾年,尚不能確知,但“數年卒業,乃歸,與清平孫淮海先生為性命交”,則是有據之實。心庵由此而步入他一生為學之道的第二階段。“性命交”,即通常所謂“生死之交”。“性命交”非酒肉之交,非利益之交,甚至亦非淡如水之君子交,而是志同道合,與之生死相付,相依相托,乃是人我之交的最高境界。
說孫馬二人乃為“性命之交”,有孫山甫幾首詩為確證。
早在孫應鰲山甫與心庵一同師事道林時,山甫就有《懷馬心庵》詩一首,回顧了二人拳拳之誼:
萬桃岡上共歌游,十載離心繞故邱。
得意煙霞令稅駕,有時風雨獨登樓。
東西南北知音少,泉石沙汀卜地幽。
折盡梅花難寄與,停云落月兩悠悠。
詩中描寫了在萬桃岡上與心庵“共歌游”的美好記憶,把桃岡故邱比作“心”之縈繞處,離開十年了,依然不能忘懷,特別是與心庵在一起的日子。真是“東西南北知音少”“折盡梅花難寄與,停云落月兩悠悠”啊!作為在桃岡師從道林的同門,山甫時時想著與心庵同隱而問學的快樂生活,其《聞心庵欲來同隱》一詩,更是道出了他的真情實感:
白頭愿得一心人,萬歲為期屬所親。
對榻平分孤月影,杖藜偕賞四時春。
蘇門嘯罷能同調,彭澤歸來不厭貧。
漫道漁磯煙水闊,玄亭風物更清真。
山甫詩中“白頭愿得一心人”“對榻平分孤月影”以及視心庵為“同調”的感慨,不難使人聯想到他們栩栩如生的游學場景。最后一句“漫道漁磯煙水闊”,顯然說的是多年以后在南明河畔講學的場景了。二人不僅在桃岡如此,更是在漁磯時依然是“對榻平分孤月影”“杖藜偕賞四時春”,從早到晚,春去秋來,兩個老學人,真真是大師老矣!尚能適否?
心庵不僅與山甫為性命交,且與李渭亦為至交。心庵作《漁磯別集》,同野即為之序。序中說:“心庵欲渭贅一語于卷末,且以為心法云云。”此序是心庵主動邀同野作。《漁磯別集》和《漁磯集》從其標題所示,應當均為心庵于南明河畔所著,故可知,心庵與同野的友情實已跨越兩個階段。彼此之間學問的切磋和思想的交鋒亦多所經年。從李序即可知曉,“心法”顯然是二人切磋的主題之一。“心法”之理路當從陽明而來,先生創“四句教法”后,“心法”功夫的有無成為后學們聚訟不己的話題,故有“良知現成”與良知“歸寂”之論的分疏。心庵顯然主“心有法”,且思同野與之唱和,然同野則以“心無法”回應,遂構成李馬二人的“鵝湖之辯”。李序:“渭日:心有法乎?”同野發出的疑問直截了當。“心”即良知,“法”即為功夫。“心”和良知皆為本體。肯定“心有法”,自是良知不離功夫,功夫不妄良知,是肯定本體與功夫一致的路數;反之,主張“心無法”,認良知為先天自給自足,勿須功夫始得,自然是龍溪、王艮等現成一派路數。同野原來也是主張“心有法”的,“向者渭亦斤斤謁人曰‘心有法可傳”,卻在讀了《論語》后改變了看法:“近讀《魯論》,竊睹記夫子教指,即心字,亦未見欠矣。”接著讀下去,漸漸就有了新的看法:“語次間,惟顏淵則日:‘其心三月不違仁。自語云:‘從心所欲不逾矩,兩言外不聞矣。”孔子稱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說到自己則是“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中除這兩句話外,鮮見有關“心”的提法。心是有法,抑或無法?同野主張:“法因人立,心無法。有法,即心也。”所謂法,即功夫,是人為后天而立,從這個意義上看,心本身是無法的;又從良知之自給自足上看,良知本體又是有其功用的,勿須后天外來添加,故心又是有法的。“有法,即心也。”同野的考慮尤為思辨,卻近于現成良知之論。他舉了《論語》中數個著名例子來說明圣人心法之固有,這些例子都是圣人因材施教而對“仁”的詢問的區別作答。如答顏淵,“語克己條目,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答仲弓為仁,“則語之以出門使民、見賓、承祭、在邦”;又如答“堯舜禹之執中”,曰“四海困窮”,曰“萬方有罪”,曰“四方政行天下歸心”,故同野曰:“為仁不離乎日用,執中不遠于萬方,圣人心法豈空懸摸索者哉?”同野的意思實際上是,心無成法,心無即成之法,心無固定之法。無固定之法,非為法之空無所有,要去作懸空摸索者。心法是因人而立,“因材施教”的,為仁之心法斷不能離乎日用,是具體而微的法,而不是抽象無端的法。同野的“心無法”實質上是“有法”,是“無法之法,乃為至法”,即“法因人立,心無法”。這種具體而微的“至法”就是“有法,即心也”。由此看來,同野的“心無成法”之“心無法”,并非是對心庵的“心有法”的反對,而是對心庵的“心有法”的深化和擴展。表面上看,同野的“心無法”似乎有落于現成良知之嫌疑,實質上看,卻有完全的不同。心庵和同野的“心法”之論皆于良知在本體和功夫的一致性上維護了陽明本旨的一貫路線,并有所深入和發揚。心庵為學的此一階段,不僅與孫山甫為性命之交,且與李同野在思想上有深度的切磨砥礪,交相發微的靈魂之契合。
三、于漁磯構棲云亭,靜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心庵在漁磯三十年,是他自己的學問——身心之學圓融無礙、悠游自得的最高階段。此時的心庵在貴陽講學,影響日盛,曾經有陽明的另一后學日馮成能,浙江慈溪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隆慶五年任貴州按察使,更是心庵的超級粉絲。《貴陽府志》卷五十七載:“貴州會城舊有王陽明祠二。貴陽之設府也,以其一為知府署,一為府學,而移祠于僻巷。成能至,則擇地于城東隅,請于巡撫阮文中,更新之,并作書院于祠內,延鄉先生馬廷錫講學其中,自為之記。”可見當時心庵的影響。莫友芝也談及“提學宜興萬士和、巡撫南昌阮文中、布政龍溪蔡文、按察慈溪馮成能,相繼延心庵主講文明、正學兩祠院”,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心庵已然成為一代宗師。
“漁磯”乃貴陽南明河中之_小島,當年心庵于小島上自構之棲云亭早己不見蹤跡,萬歷年間,黔撫江東之取“甲于天下之秀”意,于小島上建了“甲秀樓”,迄今逾四百年完在,遂使此樓成為黔省筑府之歷史地標。心庵于漁磯上之棲云亭靜坐三十年,他的《漁磯集》應該就是著于此時。通過靜坐之三十年,有悠然自得之趣,且自警略日:“必極靜、極清,以至于極定;始長覺、長明,以至于長存。徹頭方了道,入手莫言貧。”莫氏《黔詩紀略》:“其勵志如此,久之,悠然自得于道林所謂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者,更不思索,隨所感觸,渾是太和元氣。”故此可以認為,心庵的心性之學、天人_體之論,受蔣道林影響,是融貫了陽明血脈與甘泉因子的。他的《警愚錄》亦當著于此時。在漁磯時間最長,達三十年,既是他學術生涯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學術生涯最重要的階段。這一時段的心庵之學,可以三項內容加以概括:一是他的心學功夫,其重要特點就是靜坐,這一靜坐的功夫乃是當年陽明于龍場,又傳之桃岡蔣信,而深契于心庵之理路,實乃一脈相繼的路數。不過心庵這時的靜坐,已嵌入了“警愚”的反省,顯然是較為高明的路數;二是心庵于漁磯靜坐三十載的同時,亦伴隨著其三十年的實地講學,“南方學者爭相負笈請業,(一時)漁磯棲云間,儼嗣桃岡之威。”時督學萬士和延心庵入書院為諸生師,四方學者益仰之,按察使馮成能重修陽明書院,亦“延鄉先生馬廷錫講學其中”,甚而有巡撫王紹元謂其“篤信好學,妙契圣賢之經旨;默坐澄心,遠宗伊洛之淵源”,并立疏薦于朝。“撫按復連疏以真儒薦”,心庵卻“堅辭不肯起”。第三就是其立言為《漁磯集》(或又有《漁磯別集》)和《警愚錄》等,而萬歷巡撫郭子章拜讀之,有“朝聞夕可”“不愧龍場”之嘆。關于心庵漁磯三十年,較詳細的記載有見于郭子章《黔記》四十五卷之《馬內江廷錫傳》。
之所以郭之章有如此感嘆,完全在于心庵之思想旨趣與思想深度。心庵靜坐歸隱思想的特點,是喜好靜中求性,傾向于江右之“歸寂”說。他在貴陽南明河畔漁磯建棲云亭,于其中趺坐三十余年,由靜坐而生悠然自得之趣。將精通詩詞文章不過視之為小聰明,視之為細枝末葉,只有歸寂心體,做到一塵不染方是心性本體。—方面,心庵與李渭、應鰲一樣,皆對朱熹重外在性的知識論理路不予認同,而持陽明先生內在之路徑;另一方面,心庵對于如何把握心性本體、本根卻持有獨自的看法。心庵的“初心”,雖在陽明學語境中之一定程度上,可同于陽明的“良知”,因為陽明的“良知”的確有不學不慮之赤子初心層面之意蘊。不過心庵認為,獲取良知,務求心體之極清極靜以至于極定的境界,方能明覺心體存在,而求知心體存在之方唯在于靜坐歸寂,而后明覺心體方得,心體實存之道方通方達。心庵固然有主張周旋世務,即刻入世一面,或多或少消解了枯坐孤影的弊端,即“警愚”,較好地保有了靜坐之極靜極清以至于極定的高明狀態。有當地官員、學者認同于心庵“默坐澄心”的靜坐方式,意為其很好地契合了圣賢的宗旨、精神,有飄然物外的超然氣度,也有無纖毫分外之求的道德情操。其境界大有一種“顏似冰壺,形如野鶴”之氣象,體現了既鄙視功名利祿,又持修道德性命的儒門風度。如此脫凡去俗之高明氣象,著實可貴,故郭子章稱道為不負陽明龍場傳道使命(不負龍場)。難怪有人要請他出山主講書院,甚至把他與當年講學于貴陽修文的先師陽明相提并論:心庵在貴陽講學所形成之影響,被譽為“蓋自陽明、道林后僅見”。
書院這種教育機構形式已有極為悠久的歷史,其既有官辦,更有民間所立。作為一種民間教育機構,通常的觀點傾向于認為,書院的初始形態產生于唐代,到宋代漸趨成熟,明清逐漸向官學化發展,到清末改為學堂。王陽明所處的明代中期,民間書院與官辦書院各自設立,王陽明在黔期間,先是創辦了龍岡書院,后又講學于文明書院,這兩所書院,一前一后,前者為在鄉民們幫助下陽明白行創辦的民間書院,后者則是前后任職提學副使的毛科與席書舉辦的官辦書院。龍岡書院雖然極其簡陋,不過由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等組合而成,但卻在歷史上能夠留名,因為它與體現著人類價值與理想的王陽明的“龍場之悟”有關。“龍場悟道”之所以是王陽明一生求索中最為看重的一樁大事,在于它揭開了陽明“心學”體系之宏偉建筑之開端,所以龍岡書院的創辦,就成了陽明所極為鐘愛的事業,因為這兩件事隋關乎著陽明的悟道與弘道這一宏大事業(“人生第一等事”)的兩個重要環節。他在做這樁事情時顯得如此地主動。相反,陽明講學于貴陽文明書院,則完全出于被動(席書數番請益始出)。雖然他在文明書院開始提出他的“知行合一”之論,這在他思想發展的進程中無疑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但是他在這一官辦書院的短短幾月里并不像他于龍岡書院時那么暢快得意、心境裕如。據記載,陽明在文明書院至多只是一主講而己,雖然提學席書待他甚厚,但他在文明書院逗留了短短數日,難怪此書院之名之“文明”二子早已為人淡忘,連錢德洪的《年譜》等史料也只是以“貴陽書院”含糊稱之。陽明和史上絕大多數儒學宗師一樣,主動而愉快地悠游于民辦書院,被動而應付地講論于官辦書院。蔣道林也幾乎完全相似的經歷,即熱衷于自在的民間游學而也曾應付于官辦書院,由于對官學不甚用心,以至因“劾以擅離職守”而“削籍”。《黔詩紀略》《內江馬心庵先生廷錫三首》所附小傳,順帶描繪了蔣道林如何從學于陽明先生,如何又“大有所得而去”,如何于心庵舉鄉一年后以副使提學貴州,又如何以“尋告病歸”,“后奉恩例”而“冠帶閑住,筑精舍于桃花岡,聚徒講學”的全過程:
王文成守仁之謫龍場驛丞也,見武陵蔣信道林之詩而稱之。時道林方為諸生,與冀元亨暗齋證“大學知止”是“識仁體”。暗齋躍曰:“然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矣。”而皆未敢遽是。相攜走龍場,受業文成之門。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楚中傳姚江學者,雖有耿定向天臺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壞,不如武陵蔣、冀得其真醇。心庵鄉舉后一年,道林以副使提學貴州,重整舊祀。陽明之“文明”“正學”兩書院,擇士秀者養之其中,以示趨向,使不汨沒于六俗,教以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心庵為之冠。道林又置龍場陽明祠祭田以永香火。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五衛,地錯貴州境,諸生鄉試險遠,多不能達,請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劾以擅離職守,削籍。后奉恩例,冠帶閑住,筑精舍于桃花岡,聚徒講學,置學田以廩遠方來者。終日危坐其中,弦歌不輟。貴州舊從學亦有往者。
文中提到“陽明之‘文明‘正學兩書院”,皆為官辦,文明書院前已提及,正學則是后來所辦,與陽明關系不大。蔣信于這兩所書院講學時間并不長,便尋病告歸。回到武陵創辦了桃岡精舍,醉心于私人辦學,聚徒講學,置學田以廩遠方來者,以至于達到“終日危坐其中,弦歌不絕”的境界。原來在貴州受教過的許多學生也前往桃岡重新師事道林,馬廷錫就是其中之一。心庵甚至連縣官都不做了,也要前往桃岡。其時心庵知四川內江,職差應付難以安心,“嘗念所學不盡澈,每白嘆日:‘吾斯之未能信,無乃賊夫人之子乎?二歲即投籍走桃岡,就道林居。”心庵于漁磯講學之盛,不僅從影響上看“蓋自陽明、道林后僅見”,且從風格上也與陽明、道林趨同,也曾有分別就講于官辦書院與民辦書院的經歷。他在官辦書院講學,是因提學萬士和、巡撫阮文中、布政使蔡文、按察使馮成能出面請他主講之不得己而為。然心庵最為得意的講學生涯,則是漁磯時段,正如他自己所賦詩云:“悠然坐磯石,塵慮忽以祛。垂綸不設餌,淵鱗方躍于。亦知君子心,在適不在魚。君不見,沙邊鷗鳥解忘機,物類浮沉宜不殊。”果然是于漁磯構棲云亭,趺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心庵的思想源自道林,而道林之學思則源自陽明。由陽明而道林而心庵,一條黔中王門之傳承譜系之脈絡清晰可見。“悠然自得于道林,所謂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者,更不思索,隨所感觸,渾是太和元氣。”這正是心庵自析其理氣、心性貫通無二之思想深受道林浸育的自白。蔣信在理氣觀上認為:“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先儒卻以善惡不齊為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此處除有甘泉因子外,明顯吸收了關學張載一系的氣論之說,主張宇宙萬物只是一氣充塞流行。心庵受此影響,也認為“隨所感觸,渾是太和元氣”。
道林反對張載、朱子等宋儒以義理之性為純善,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的說法;不同意將義理之性于價值判斷上高于氣質之性,并獨立于氣質之性以外的提法。道林以為,既然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同出一個太和”,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就應原為一體,故而主張理氣合一的一元論,反對將理氣二分。道林關于理氣與心性關系的獨特詮釋,其要在于通過排除理氣二元之弊,而揚心性一元之旨。道林道:“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道林認為所謂理氣合一,其實質就是心性合一。理氣與心性,實指一也。這樣的闡釋為心庵所接受和認同。心庵所言“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即是直接承之道林而來。道林之論顯然又是上宗陽明先師。陽明、道林、淮海、心庵,在理氣與心性之_元論上,觀點一致而統一。陽明言“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應鰲則言“蓋性即此心。”就心性本體論而言,包括陽明在內的黔中王門諸家均站在完全相一致的立場上,與程朱之論形成鮮明的對照。不僅在本體論上是如此,在功夫論上亦同然。
心庵在理氣、心性問題之本體論上完全認同道林,但在功夫論上,他發展的也是道林靜坐功夫一面,這是他居漁磯三十年而名聞于世的獨特之處。心庵詩《山中吟》,表達了其對歸隱、自得、和樂的追求:“春陽律轉先深山,村村花柳回雕顏,鳥鳴高樹聲關關。幾家煙火自村落,春酒熟時相往還。”儼然一幅花柳鳥鳴煙火的山村美景,更是其自適心境的表露。在《磯上》則是希望在南明河畔“悠然坐石磯”,逸然自得。“亦知君子心,在適不在魚。”則是其隨應心境順適自在的感受。
鑒于陽明曾有過良知虛寂特征的表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這種關于良知的多重闡釋,為后學們留下了多選的路線和展開的空間。心庵強調要“抱守初心”“一塵不染可窺心性本根”,必然引入靜坐澄心的修養功夫,其路數更靠近江右之聶豹、洪先的“歸寂”說。雙江針對時下王門各宗分歧,日:“今之講良知之學者,其說有二。一日:‘良知者,知覺而己,除卻知覺別無良知。……一曰:‘良知者,虛靈之寂體,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發也。致知者惟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前者所指乃龍溪、王艮之現成良知之說,后者則指雙江與洪先等的歸寂之論。雙江認為良知本體不可能現成具足,往往被后天意念所污染,故需施以后天功夫以去其昏弊。這樣一來,主靜亦成為了心庵所主之思想旨趣及所持之修養功夫。主靜以涵養良知未發之寂體,直接充養虛寂的心體,使良知得以復初、復明,用心庵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警愚”。依筆者的理解,心庵的“警愚”具有如下雙重涵義:一是針對良知在“未發”時的警惕、慎獨;二是針對良知在“已發”后的警醒、蕩滌。羅洪先遵循雙江的“歸寂”說,言“此間雙江公,真是霹靂手段!千百年事,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真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而陽明公門下猶有云云,卻是不善取益也。”心庵的靜坐澄心,就是他從蔣信、雙江諸公手上接過的“霹靂手段”,在他看來,眾多的王門后學中,毫無疑問雙江的“歸寂”說甚為佳良,故言:“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直接通過靜坐、歸寂功夫,截斷意念的紛擾,才能使本明的心體不能遮蔽。心庵也同樣強調:“必極靜極清以至于極定,始長覺長明以至于長存,徹頭方了道”,靜坐到極致,以至于達到一種澄明的心理狀態,才是徹底地把握了心體之道。難怪郭子章要說他“講性命之學,其旨皆以靜養為主。”心庵主張的所謂心“有法”,此“有法”實質上就是他成就心性之道的“靜坐澄心”之法、“滌慮玄覽”之法。正因為有了他的這一“成法”,遂使心庵的思想旨趣每每安之于“悠然自得”之境界,這大概就是子章所云“朝聞夕可”“不愧龍場”之深廣奧妙之意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