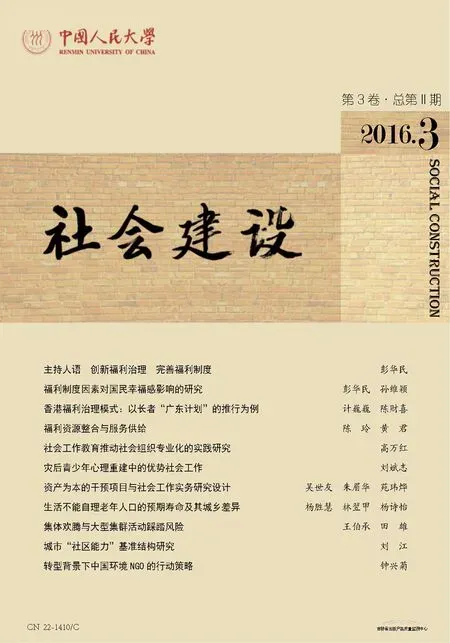轉型背景下中國環境NGO的行動策略
——基于重慶市L環保中心的個案研究
鐘興菊
?
轉型背景下中國環境NGO的行動策略
——基于重慶市L環保中心的個案研究
鐘興菊
摘 要:本文通過對重慶市L環保中心的調查發現,在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源于西方的“法團主義”與“公民社會”兩大視角在分析環境NGO行動中凸顯單一維度自主性的弊端,難以從動態視角解釋組織參與治理實踐過程中獨特的行動策略:即在夾縫中“做減法”成長,多策略聯動構建常態化互動機制,非對抗不合作的共生邏輯以及自我設限以獲得合法性生存與發展等。研究表明,宏觀政策變遷、市場體制改革以及環境NGO自身能力的不斷提升共同建構了社會組織的行動策略。在多元主體參與環境治理背景下,對照西方分析范式在本土化中的局限,筆者認為,在中國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環境治理從單純依靠政府的時代轉向推動政府主導、企業支持以及環境NGO與公眾共同參與的“后政府動員式”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環境治理;環境NGO;后政府動員
一、問題的提出:轉型背景中的環境NGO與國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環境NGO①在學術探討中,關于環境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沒有統一界定,如環境非政府組織(NGO)、環境非營利組織(NPO,日本普遍使用)、環境社會組織、環境第三部門(領域)、環境第三方機構、環境民間組織或社會團體、環境公民社會組織等,與之相對應的概念內涵豐富,且側重點不同,但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及志愿公益性是其共有的三大特性(salamon,1994;康曉光,1997;中華聯合環保會,1995)。在我國政府官方文件中“民間環保組織”使用比較普遍。同時有關非政府組織從事環境保護的討論中,又有“環境NGO”與“環保NGO”(英文均為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ENGO)的提法,有學者根據文獻計量分析發現前者比后者使用更加廣泛(何莉莉,2008),同時也被稱為環境民間組織或環保社會團體。在本文中,筆者將采用學界比較常用的“環境NGO”(簡稱為ENGO)概念進行統一,并且在不同類型的環境NGO中側重于與官辦ENGO相對的草根ENGO的探討。等社會組織的發展標志著中國“社會”領域出現,縱觀中國“社會”30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一方面社會結構轉型與體制轉軌為環境NGO發展提供了生存與行動空間。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一個加速轉型期,其總體趨勢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一個權力和資源高度集中的“總體性社會”向一個權力與資源相對分化的“后總體社會”轉型②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2)。,市場的發育和成熟以及社會的出現與成長推動了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的整合與配置;與此同時由于長期以來粗放型經濟發展導致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環境保護陷入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困境,組織創新成為超越“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第三條路徑,為環境NGO的發展創造時代契機;再者,基于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不再萬能,環境NGO成為環境治理的支持者。中央強調“重視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以及“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協調行動,推動生態文明”,為新常態下環境NGO發展提供了政策機遇。另一方面,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環境NGO仍熱衷于環保“老三樣”(即觀鳥種樹撿垃圾),較少關注環境污染受害者,從而在環境治理對組織化資源的迫切需求與發展遲緩的社會組織之間形成悖論。①馮永鋒:《邊做環保邊撒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第87-90頁;晉軍:《兩種環保小世界:社會轉型期中的民間環保組織》,載郭于華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面向社會轉型的民族志(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32頁。
環境NGO在轉型期政策機遇與資源約束博弈中的行動選擇,實際上反映了社會與國家間競爭關系的演變。環境NGO在參與環境治理中,如何利用行動策略改變他們與國家的關系,使之朝著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方向變化,進而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以及影響政府策略?在轉型背景下,源于西方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大分析視角是否具有本土化的解釋力?鑒于此,本文將對轉型背景下環境NGO參與環境治理的行動策略進行考察,以期探究在中國民間社會土壤中生長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解釋框架。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思路
(一)環境NGO與國家關系演變
中國環境NGO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從改革開放后的官辦環境NGO到90年代的半官辦NGO轉向,再到21世紀伴隨環境問題惡化以及中央強調“多元主體參與環境治理”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新興環境NGO。早期環境NGO具有官方性特征,更多作為政府的幫忙人與合作伙伴②洪大用:《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成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88頁。,從事比較溫和的環保宣傳行動。③童星、薛亞利:《社會轉型期有關NGO若干問題的探討》,《湖南社會科學》,2004(3)。晉軍對近20余年環境NGO從事環保實踐梳理發現,大多組織以“綠化”為使命,熱衷于從事“上山撿垃圾、植樹造林,動物保護”等初級的、低水平階段的、非專業性的環境教育與宣傳,沒有突破“重大利益沖突”以及“社會動員”的兩大“環保小世界”的邊界④晉軍:《兩種環保小世界:社會轉型期中的民間環保組織》,載郭于華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面向社會轉型的民族志(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22-45頁。,他們只是綠化,而不是對抗政府。⑤Ho,Peter.“Greening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and civilsocietyinChina”.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1(32):893-921.2001年環境NGO在與政府領導人對話反對京密引水渠硬化工程中受挫,隨后2004年云南大眾流域與綠家園在“怒江保衛戰”社會動員中失敗并付出沉重代價。為了生存,環境NGO不得不調整行動策略,重新回到傳統的環保宣傳教育的小世界,從而替代倡導公眾參與決策、積極影響政策的走向。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強調“多元主體參與環境治理”表明環境NGO逐漸成為獨立的公眾參與力量,為新興環境NGO實踐提供政治機遇。環境NGO從和風細雨的環境宣傳教育、科普活動轉向作為公眾或者弱勢群體利益的“監護人”,逐漸成為平衡政府和市場的重要力量。環境NGO行動軌跡與角色定位的變化反映了與政府競爭關系的演變,即從傳統政府主導型的環境保護逐漸走向多主體參與合作的環境治理時代。然而轉型背景下環境NGO發展與西方公民社會不同,在中國“家國一體”的歷史傳統中社會對國家有很大的依附性,中國環境NGO大多處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模糊地帶;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體制下,環境NGO與國家以及市場塑造的政治經濟結構密切關聯。于是我們有理由質疑,基于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視角是否有助于真正解釋中國新時期的環境NGO發展多種分化。
(二)環境NGO與國家關系的理論探討
通過梳理環境NGO的研究發現,主要從靜態社會結構與動態博弈關系兩大維度展開討論。一類是從靜態視角對環境NGO與國家互動所形成的行動邊界進行討論。改革開放以來,源于西方社會情景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①“civil society”的譯法,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多依據歐陸思想而譯為“市民社會”,近期研究者則較多譯為“公民社會”,本文主要使用后者提法。和“法團主義”視角成為分析中國環境NGO的主要概念框架。在轉型背景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遠比“公民社會”或是“法團主義”所提供的解釋更加復雜;同時中國經驗相對于二者產生的西方背景具有獨特性。有許多學者批判“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視角在解釋環境NGO實踐中存在難以超越二者建構的連續統局限性,于是有學者從國家與社會互動內在機制討論貢獻了精辟的概念框架,如“非正式網絡”②[美]華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地方性國家法團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③Jean C. 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分類控制”④康曉光、韓恒:《分類控制:當前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社會學研究》,2005(6)。與“與國家商榷”⑤Shieh, Shawn&Guosheng Deng.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The Impact of the 2008 SichuanEarthquake on Grass-Roots Associ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2011.等,但從思維模式看他們仍然落入了國家與社會連續統中,其難以突破背后預設的國家與社會的兩極關系。范明林指出NGO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包括四類:即“強控性”、“依附性”、“梯次性”和“策略性”,他們在法團主義特征逐漸減弱的同時公民社會特征逐漸增加。⑥范明林:《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互動關系》,《社會學研究》,2010(3)。環境NGO行動目標具有長期性、不確定性、強外部性等特征,其行動實踐在特定情境中并不必然具有單一屬性,而是同時具有公民性與法團性的雙重屬性。在本研究中為了探討環境NGO與國家互動形成的行動邊界,以NGO行動的雙重屬性為基礎,即結合“公民性”的“對抗”關系強弱特征(如圖1橫軸表示)以及“法團性”的“合作”關系強弱特征(如圖1縱軸表示)形成分析坐標,對環境NGO的行動邊界進行定位⑦本文借鑒范明林(2010)結合法團主義與公民社會兩大視角,將四種不同的NGO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總結為四大理想類型(據本研究需要有所修正),以此定位不同類型的NGO在象限中位置,有利于將不同環境NGO的行動邊界進行定位。(見圖1),從而有利于發現新常態下環境NGO行動突破現有結構局限的新特點。
如圖1所示,根據環境NGO的行動特征將其定位于國家與社會雙重維度構建的區域中,具有政府幫忙人角色的庇護型ENGO(A)與具有宣傳教育者角色的依附型ENGO(B)分布于“強合作、弱對抗”特征的區域;而具有信息咨詢者的層次型ENGO(C)與作為政策影響人和監督者的策略型ENGO(D)分布于“強對抗,弱合作”區域;第三象限是具有公民性與法團性“雙弱”特征的ENGO類型,大多存在于建國之前的民間社團(如學術協會,宗教和慈善組織等),這不是本文探討重點故在此將不展開。現有研究發現,大多數傳統ENGO的行動實踐均可以在公民性與法團性構成的序譜結構中找到相應位置。環境NGO的行動邊界是在社會與國家互動中形成的一種靜態權力結構分配狀態,基于當前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該視角在解釋行動邊界愈加模糊的環境NGO時存在不足。

圖1 “公民性-法團性”視角下環境NGO行動邊界分布注:圖中“+,-”表示強度,沿著箭頭方向強度逐漸增加。
隨著環境治理時代到來,環境NGO的行動策略凸顯公民性與法團性之間的斷裂,即具有“強法團但非合作,強公民但非抵抗”,直言之,從公民性維度看具有很強的公民社會屬性,但是并非對抗政府;從法團性維度看具有很強的法團屬性但并非與政府合作,表現出一種與傳統ENGO行動完全不同的混合型的行動特征,其具有不同區域特點但又不完全符合某一區域特征。在本研究中筆者將重點關注超越序譜坐標所能揭示的環境NGO行動新類型,從而對源于西方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視角分析提出挑戰。
另一類是從國家與社會的動態關系視角分析,認為國家與社會既非“國家中心的”,也不是轉型后“社會中心的”而是“國家鑲嵌在社會中”(state-in-society) ,二者關系是一個不斷沖突和妥協的動態過程(Migdal,1994)。該視角與靜態的權力結構分配的不同在于它們并沒有靜態地討論國家與社會強弱程度問題,而是動態地分析國家與社會之間競爭關系形態,環境NGO的行動必然分布于國家與社會連續統中的某一個位置。與西方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具有清晰界限不同,轉型期中國社會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環境保護具有政府主導型特征,國家與社會之間互動博弈的邊界既是環境NGO的行動界限,同時也為實踐行動提供較大的彈性空間。基于歷史特殊性以及現代社會轉型,中國社會“官民”結構中的“王權無邊”的制度安排發生了結構性變遷,國家控制能力下降容留了巨大的社會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使環境NGO與國家之間形成一種動態的權力分配演變。晉軍從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關系交織視角對西南水電開發中民間環保組織的成敗分析發現,當前中國環保民間組織存在“結構上的公民社會視角”以及“項目行動上的法團主義視角”特征。①晉軍:《兩種環保小世界:社會轉型期中的民間環保組織》,載郭于華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面向社會轉型的民族志(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22-45頁。也有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環境保護走向整合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視角的第三條道路,即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領導的公民社會”,“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②洪大用:《社會變遷與環境問題》,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第250-255頁。,“半官半民性”③王穎、折曉葉、孫炳耀:《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社團組織》,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第6頁。等特征。
無論是從靜態視角分析環境NGO與國家的權力結構分配,還是從動態視角探究國家與環境NGO競爭關系的演化研究表明,實際上并沒有突破國家與社會結構視角的討論。近年來中國環境NGO發展欣欣向榮,但實際上并不意味著形成了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并未成為一種真正獨立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以整合和代表社會的利益和聲音,從而凸顯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下的“強國家,弱社會”弊端。由此可見,轉型期環境NGO行動策略突破靜態權力結構分配中的區域定位;同時在動態的國家與社會力量博弈中,新興環境NGO傾向于尋求與政府以及市場等多元治理主體間的合作而非落入“國家與社會”二元爭論的陷進。
(三)分析思路
本文以重慶L環保中心①在本文中對所調查的社會組織以及調研所涉及的人物姓名都做了技術性處理,也都是完全遵循田野研究的既有規范進行的。發展歷程為軸線,著重考察環境NGO對待政府的策略,即是在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中L組織是如何利用行動策略嘗試改變其與國家的關系,使之朝著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方向變化,進而揭示源于西方傳統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大解釋框架的局限性,不斷建構社會轉型背景下適合本土化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解模式。同時期望環境治理從單純依靠政府的時代轉向推動政府主導、企業支持與環境NGO與公眾共同參與的“后政府動員式”的發展路徑。
三、研究方法:個案研究
本文的主體經驗材料主要來自2014年7月至今對重慶市L環保中心的參與式觀察與相關負責人的深度訪談。筆者前期主要通過媒體網絡對L環保中心、政策法規、政府文件報告等進行二手資料收集整理,與L中心建立關系后以志愿者身份參與組織各項活動以進行參與式觀察,同時對組織核心工作人員、重慶市環保局負責人、其他環保組織以及民間意見領袖進行深度訪談獲得一手資料。本研究屬于深度個案研究,其目的不在于試圖得出一個能推論到全國的結論,而是希望在治理背景下更好地理解環境NGO與政府互動的策略新趨勢以及對中國環境治理的意義。重慶市L環保中心最初由重慶某高校一名大學生XC發起,成立于2010年,前身是重慶青年環保協會,于2011 年 8月正式在重慶市民政局登記注冊,更名為重慶L志愿服務發展中心(簡稱“L環保中心”,以下簡稱L中心)。2014年初L中心將任務目標定位為致力于工業污染防治,通過運營環評公眾參與網,執行環境影響力調查、推進見習工程師計劃三個策略項目,以源頭控制和末端治理兩個路徑,達成削減工業污染的目標。②詳見L中心官網網址:http://www.gzcy.org。L中心自注冊以來積極參與地方與全國環境治理實踐并取得顯著成績,通過申請信息公開發現全國各大環評機構“掛靠”環評工程師現象嚴重并督促國家環保部成功處理“影子環評師”事件;在不到5年時間通過實地環境污染影響調查協助整改100多家企業水污處理問題等。L中心的行動實踐表明其逐漸突破傳統環境教育宣傳的內容邊界,本研究將其作為分析治理背景下中國環境NGO行動策略新趨勢特征的個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新時期環境NGO行動策略的建構
為什么一個普通的ENGO在短短5年內針對企業排污取得難以置信的成績?他們憑借什么力量以及采取哪些行動策略突破政府與企業的限制,使之朝著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方向變化,進而有效地實現組織目標并影響國家策略?從中國環境NGO近30年的發展歷程來看,但凡取得突出成就又能與政府長期共存的ENGO,通常歸結于兩大原因:一是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發揮著魅力型領袖作用動員大量的公眾力量;二是組織背后能夠追溯“上頭有人”的特殊資源。①陶傳進:《水環境保護中的NGO——理論與案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16頁。通過對重慶L環保中心的發展歷程以及行動實踐梳理發現,L中心在參與環境治理中的成功實踐不同于以上兩點,而是凸顯一系列與傳統ENGO不同的行動策略:即組織在夾縫中“做減法”成長;多策略聯動構建組織與政府、企業等多方主體常態化互動機制;在與政府的互動博弈過程中構建一種“非對抗但不合作”的共生邏輯;最后為了獲得基于生存的發展合法性對行動進行自我設限等。
(一)在夾縫中“做減法”成長
縱觀中國草根環境NGO的發展歷程表明,大體經歷了初期以資金為導向的野蠻生長,中期在不同力量博弈中進行調整完善;最后進入常態化發展期。與傳統環境NGO的生存邏輯不同,重慶L中心(前身為“重慶青年環保協會”)具有兩大特殊性。一是“名不副實”的機構名稱。一個以從事環保為主的社會組織的注冊名中卻不含任何與“環保”相關概念,難以讓人從名稱中聯想到組織的環保實踐。其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的限制競爭原則,其明確規定“在同一個行政區域內,不允許成立相同或相似的公益社會團體”。早在1995年,重慶市環保局下注冊成立了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基于同市不能再注冊相似的社團,所以L中心努力得到“跨界”業務主管單位重慶市文明辦起名,并于2011年8月登記后便有了今天看上去“比較疑惑”的名稱,但獲得夾縫生存的空間,為跨界生存提供契機。其二,中心任務目標定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做減法”歷程,L中心前身“重慶青年環保協會”(2010年成立)以“污染防治、環境教育、社區發展、節能減排、生態農業”為五大工作方向,試圖通過法律服務維護公眾環境權利,通過技術創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通過公眾參與促進公民社會發展;2011年8月正式注冊后的目標演變歷程可以從中心主任XC留存的三張名片得以充分體現:第一張:“環境保護、公眾倡導、社區服務、行業發展、生態農業”,這可謂包羅萬象;第二張:“環境保護、志愿者中心、公眾科學”;第三張:“環境保護和行業發展”,最終確定工業污染防治,主要運營環評公眾參與網,環境影響力調查與見習工程師計劃三個項目。2014年作為L中心發展的轉折點,與其說“環境教育”板塊內容從中心剝離是對組織發展的考量,還不如說是為中心適時調整發展戰略目標提供契機。從L中心任務目標發展演變表明,與草根組織早期以資金導向的生存邏輯相似,中心項目可謂圍繞“環保”無所不包,之后圍繞“環境保護”為核心“做減法”逐漸使目標任務更加明確、有針對性且具有可持續性。與官方與半官方環境NGO相比,民間環境組織最大的優勢在于,通過“做減法”的迂回策略逐漸明確組織發展目標,進而避免在“做加法”中喪失目標與獨立性。從L中心行動空間演變歷程表明,機構逐漸剝離“幫忙人”的環保宣傳教育者角色進而轉向工業污染監督者和環評政策的影響者、信息咨詢提供者角色,為民間環境NGO實踐突破對抗與合作的邊界奠定基礎。
(二)多策略聯動構建常態互動機制
L中心的核心目標之一是致力于工業污染控制的環境影響評價(以下簡稱“環評”)與監督,不可避免地要跟政府和企業等相關利益主體打交道。在中國轉型背景下,企業與政府形成特殊的“共生”結構,即企業成為政府的后方將環保部門推向行動的第一線形成應對ENGO監督的“防火層”②同上,第20頁。,企業與環保部門的共生合作使環保組織、志愿者及公眾的環保行動舉步維艱。正如資深公益人士H總結到,“政府發放的排污許可證實際上是企業排污的‘護身符'”(HLS20150720)。作為新興而力量弱小的環保組織L中心不可避免的遭遇“雙重”困境,一是企業的不理睬;二是環保部門態度和行動的消極。面對一系列困境,一個普通的ENGO如何進行企業排污監督?如何利用策略獲得環保部門關注、信任并建立常態化的互動機制?
“我們與環保局的關系并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但目前只要是我們中心監督舉報的事情,基本都能得到相應部門的及時回應和處理。”L中心負責人XC自信地說,但這樣良性的互動關系格局卻是來之不易。據了解,“最初市環保局把我們的監督和舉報看成是‘找麻煩',并不甩(即不予理睬)我們,于是我們只能利用訴諸新媒體等特殊策略使中心的行動成為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存在,通過互聯網發帖的策略性手段‘刺激'相關部門,在強大的網絡輿論壓力下政府開始妥協并轉變態度,同意與中心進行面對面溝通”(XC20141229)。于是L中心適時抓住機遇,積極向政府表達“讓你們知道時刻有人在關注,督促你們更好作為”,之后通過不斷調查發現新的污染企業并向環保部門匯報監督進展情況,督促政府及時回應進而提高行政效率。正如一位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在要求污染企業配置清潔生產設施時所說:“不只是環保局執法部門在盯著你們,是有人在盯著我們,看我們的工作程序效率如何?”可見中心監督力量已初具影響力。在多次的博弈溝通中,L中心最終在重慶市環保局上下“掛了號”,使之打交道的反應速度更快。為建立常態化的直接互動機制,市環保局特規定每月一天的“環保局長接待日”進行面對面的匯報、投訴和建議,從而組織不需要再倚重網絡媒體手段施壓。另一方面,L中心與企業互動溝通主要體現為對企業的獨立第三方監督。“我們不管企業內部發生了什么,為了避免風險也不直接對質企業,我們很明白我們能做什么”L中心負責人LB強調。由于L中心力量弱小難以與企業直接抗衡,更甚者若采取直接的企業污染抗爭行動可能遭遇生存的風險。L中心主要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跟蹤污染源,取樣檢測,向環保部門遞交檢測報告以及解決方案建議等行動積極支持政府督促企業排污整改。
L中心與政府間的互動關系經歷了“找麻煩、不理睬—網絡媒體輿論力量施壓對抗—面對面溝通—‘掛上號'后獲得合法性—常態化溝通與監督機制建立”的曲折發展歷程;同時與企業間的間接互動機制形成了共同依托政府作為“第一線”的行動實踐模式。從L中心與政府、企業構建的互動機制表明,通過多元化策略與一個系統構建起來的互動機制,在法定程序內解決問題,同時加上對抗和博弈的斗爭基礎,逐漸形成的正向影響在環保部門系統內部是可以傳承的,該模式區別于傳統官方或半官方“找關系”或與比較開明的領導建立合作關系,其不會因為某個領導調離而需要重新建立,是一種穩定、有效、確定、可傳承的合作基礎。
(三)非對抗但不合作的共生邏輯
傳統官方與半官方環境NGO的行動實踐表明,大多強調與政府“合作”以及難以突破“對抗”的行動界限,然而L中心作為獨立的第三方監督力量在與政府以及企業的互動博弈過程中凸顯對抗與合作相互斷裂的特征,在國家法團性和公民性兩大視角構建的行動區域中難以定位。基于中國政府主導型的環境保護體制以及傳統考核指標的單一化,環境保護在地方實踐中形成政府與企業的共生結構,地方保護主義成為破解環境保護的難題。在社會治理背景下,隨著新興的環境NGO的發展,能否置換企業與環保部門之間的共生關系,實現一種從功能上互補整合的環境保護體系?
“我們與環保局既不是合作,也不是對抗,而是互動共生關系。”L中心負責人XC強調中心與政府的關系是一種非對抗不合作的互動共生關系。他對“互動”(或溝通)的理解是,組織在與相關利益主體博弈中既有心平氣和的交流、談話,也包括情緒外露的吵架、拍桌子,還有采取網絡媒體輿論壓力的對抗性方式。為了深入理解L中心所特有的“非對抗不合作”行動策略,將以中心成功參與監督的“影子環評師”披露事件為例展開。
L中心在環保部門“掛上號”后即意味著獲得政府信任和行動的合法性地位,2011年下半年開始介入環境影響評價項目(簡稱“環評”),最初主要通過招募大量志愿者對全國各大環評公示網站手動搜索環評公示信息,審核環保部門審批的環評報告書,研究環評報告流程、公示信息渠道、環評公司資質、公眾參與辦法是否符合規定等問題。面對日積月累的大量碎片化信息,L中心借鑒“公眾環境中心”匯集數據建立“污染地圖”的經驗,于2013年5月創辦環評公眾參與網①截至2015年3月底,環評公眾參與網收錄超過41000 條環評項目信息,60 余家環保部門約1.5 萬名環評審查專家庫成員。并上線,被稱為“環評地圖”。中心又以《信息公開條例》為依據自2013年6月開始以掛號信的方式向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國家環保部發出環評專家庫的信息公開申請,歷時長達約半年的持續跟進,截至2013年11月30日全國32個單位分別通過不同方式將環境影響評價專家庫信息公開。然而L中心結合環評公示網站收集、整理環評信息以及各部門單位公開的專家名單,意外發現環評機構工程師“掛靠”②掛靠,這里實際上與“借用”系同一概念,即沒有資質的環評工程師借用有資質的環評工程師的名義從事環評影響評價相關工作。現象嚴重。經網絡搜索統計發現,129名環保系統公職人員將環評師的資質“租借”給環評機構以牟取利益,他們實為國家公職人員的“影子環評師”。為此,2014年年初L中心將違規行為舉報函遞交環保部,并在持續跟進下于2014年7月31日以及9月16日分別得到環保部回應,對62名“影子環評師”予以通報批評并注銷登記,并對31家環評機構進行整改。③參見環保部發文《關于對62名環評工程師“掛靠”環評機構問題處理的通報》環辦[2014]67號以及《關于31家環評機構“掛靠”環評工程師問題處理意見的通報》環辦[2014]79號,分別詳見網址:http://www.mep.gov.cn/gkml/hbb/bgt/201408/t20140806_287469.htm;http://www.mep.gov.cn/gkml/hbb/bgt/201409/t20140918_289247.htm。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大規模開始清除環評界“影子環評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環保部通報的62名掛靠工程師和31家環評機構中,有43名工程師和20家環評機構為L環保中心舉報。
通過L中心對“影子環評師”違規行為監督披露的成功實踐表明,民間環境NGO與政府在非對抗的互動關系中構建了一種真正有效的合作。環保部門不再對ENGO持有抵觸態度,中心始終為政府進行污染執法提供排污企業的一手資料和證據,將政府推向環境治理行動的“第一線”,實現了一種增量的民間環境監督。ENGO與環保部門實現的一種功能上的整合,將傳統政府與企業間的“共生關系”進行置換,社會組織成為環境治理的真正主體,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結構發生變化。然而L中心負責人更愿意將這種與政府間的關系稱為“互動共生”而非“合作”,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國“強法團,弱社會”背景下,經常把“合作”理解為妥協和投降,避免被作為環保部門的“力量腿腳”而偏離組織自身的目標。“非對抗不合作的關系”凸顯了新興環境NGO突破了對抗與合作雙向邊界的新趨勢。
(四)自我設限下的合法性生存與發展
“要生存,還是要發展”是環境NGO行動邏輯兩大基本原則,大多數傳統環境NGO以“要生存”為基本原則主動設定行動邊界從而一直熱衷于環保宣傳教育的溫和實踐。傳統環境NGO在嘗試突破“社會動員”與“利益沖突”邊界中遭遇失敗后進行自我調整回到行動邊界內活動以獲得相對安全,從而使其在“自我設限”的環保小世界中不斷再生產。①晉軍:《兩種環保小世界:社會轉型期中的民間環保組織》,載郭于華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面向社會轉型的民族志(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第22-45頁。新時期治理背景為多元主體平等參與環境治理提供契機,新興環境NGO以“要生存也要發展”為原則在謀求突破傳統限制的行動中凸顯新的趨勢。民間組織的發展具有合作性格,尤其是在組織發展初期為了生存傾向于與利益相關主體合作,如依附于政府與企業力量的支持。L中心主要致力于工業污染防治,工業企業自然成為重要利益相關主體之一,同時也是被監督的核心對象。基于L中心作為工業污染監督者角色與工業企業排污事實之間的特殊性,中心主動選擇與工業企業之間絕緣,該特征在L中心的資金來源中得以體現。從中心財務收支表發現(2014年上半年年報)資金貢獻主體及占總收入比率分別是:個人(0.05%)、企業(0%)、公益機構(76.06%)、政府(23.89%)。針對企業主體不占有組織資金來源的問題,中心負責人XC的說法是,“我們中心約定俗成不接受企業任何形式的捐贈,一是為了保證中心作為環境保護第三方監督審核機構的獨立性,二是確保在應對企業生產的不確定風險中進行企業污染調查與評價的公正和透明”。從民間環境NGO的行動實踐表明,雖然組織在發展初期基于“生存理性”原則呈現無所不包的任務目標,但致力于工業污染防治的L中心明確定位與企業的關系,從而在“生存與發展”的原則下進行“自我行動設限”以期獲得合法性。環境NGO“自我設限”的行動邊界從“生存”原則到“生存與發展”并重原則的演變與拓展表明,在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背景下新興環境NGO在生存原則下突破“合作性”邊界以及“對抗性”邊界構成的“環保小世界”的限制,同時為了獲得“發展”更大的空間與行動的合法性,在理性選擇下超越傳統行動空間對主體不同限制,從而為ENGO從生存型向發展型環境組織轉型奠定基礎。
五、理論反思與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一個權力和資源相對分化的轉型社會,為環境NGO的發展容留巨大的社會空間;十八大以來強調“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組織協調行動,推動生態文明”,為新興環境NGO突破傳統局限提供契機。新常態下環境NGO的行動策略凸顯獨特的時代特征對環境NGO自身發展以及中國環境治理模式創新具有重要理論意涵與現實意義。在理論方面,新興環境NGO策略行動為反思“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大視角的單一維度自主性的局限提供實踐依據;在實踐方面意味著能力不斷提升的社會組織真正成為環境治理主體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推進環境治理逐漸走向“后政府動員時代”。
(一)對“國家—社會”關系理論視角的反思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主導型的環境保護理念下環境NGO作為社會力量發展遲緩。十八大以來強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環境治理為環境NGO的發展創造政治機遇,通過重慶L中心的實證研究發現,新時期背景下環境NGO行動策略凸顯一系列新特點:即在“名不副實”的名稱中獲得夾縫中“做減法”成長;通過多策略聯動與政府、企業構建常態化互動機制;與政府間建立一種超越傳統限制的非對抗不合作的共生邏輯以及通過自我設限以獲得合法性生存與發展等。一方面從L組織行動實踐中體現的“公民性”維度發現“非對抗”的特殊性。治理大背景下為環境NGO參與合作治理創造契機與自由行動的空間,L中心因為“名不副實”的注冊卻隱含著組織獲得夾縫生存的機會;同時組織通過媒體等多策略聯動建構與政府間常態化溝通機制,中心主動選擇放棄傳統單兵前線作戰的策略,始終讓環保部門位于解決污染問題的第一線,中心作為政府背后具有獨立性的支持者而非對抗的力量,從而體現了“公民性中的非對抗”的典型特征。那問題來了,L中心在“公民性”中的凸顯的“非對抗”特征是否意味著其走向了“法團性”的一端?然而,另一方面從“法團性”維度卻發現“非合作”的獨特性:L中心通過劍走偏鋒從跨界業務領域尋找到“婆婆”后,獲得第三方獨立監督的合法性,通過申請信息公開成功監督并督促國家環保部門披露了“影子環評師”的違規行為,從而實現一種增量的民間環境監督。研究發現L中心負責人更愿意將與政府的關系構建為“非對抗不合作的共生邏輯”而不愿意定義為“合作”,主要是因為在“強法團弱社會”背景下通常將“合作”理解為妥協或投降而喪失了自身發展的獨立性,從而體現了一種超越法團主義視角的非合作特征。
從以上不同的行動策略表明,L中心超越了“公民性”與“法團性”兩大維度構建的行動邊界范圍,在中國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中運用源于西方的“法團主義”或“公民社會”兩大典型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存在難以逾越的特殊性困境。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體制發生巨大轉型,國家與社會關系遠比西方情景中建構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所能解釋的社會現實更加復雜,舶來的理論視角基于特定時空中歷史、文化與政治的獨特性使理論范式的適應性在信度和效度上受到質疑;同時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的制度安排預設了國家與社會兩極對立的連續統,然而如果這一連續統并非是現實中國家與社會關系存在的必然形態,無論是公民社會還是法團主義——這種在兩極對立連續統當中確立國家與社會關系位置與形態的做法缺乏解釋力。基于當前中國政府強調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契機,國家與社會關系逐漸演變為國家、社會、市場、公眾等多元主體之間復雜的關系維度。從L中心參與環境治理的行動策略發現,一方面揭示了“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大分析視角在轉型背景下不合時宜,同時突出L中心的行動策略超越公民性的對抗與法團性的合作等獨特性。由此表明環境NGO能力不斷提升并逐漸成為參與環境治理的主體,為新時期探索環境治理的新型發展路徑奠定基礎。
有學者認為,在轉型背景下,中國本土市民社會論者并沒有像西方論者那樣僅僅強調作為國家對立面和權力“監督者”的“市民社會”①鄧正來、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2008,第1-14頁。。“公民社會”是一個徹底的西方概念,即使中共十八大以來強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環境治理,為自身能力不斷成長的社會組織創造了參與治理的空間,但“公民社會”也僅僅是一個水土不服的假想概念,難以解釋轉型背景下中國新興環境NGO所凸顯的超越公民性與法團性的復合特征。在轉型背景下試圖通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后政府動員式”環境保護以尋求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建設路徑,而“公民社會”道路仍將任重道遠。
(二)中國環保抑或進入“后政府動員式”時代
在社會治理背景下,隨著環境NGO自身能力提升賦予了環境合作治理實踐的新意涵。研究表明,當前環境NGO的發展趨勢是,單純與破壞環境的企業以及政府對立的NGO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甚至走向消亡,由原來單兵前線作戰的斗爭轉變為與利益相關主體合作與斗爭并存的模式是環境NGO在當前以及未來長時段中最具有發展前景的方向。環境NGO在保留監督和制止破壞環境行為功能的同時,還積極幫助企業和政府對接環保技術,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由此可見,中國環境治理從單純依靠政府的時代逐漸轉向推動政府主導、企業支持與環境NGO與公眾共同參與的“后政府動員式”的發展路徑。
“后政府運動式”概念是洪大用教授在對比亞洲環境運動的不同路徑后針對中國環境運動發展的特征提出的,但關于“后政府運動式”的內涵沒有作進一步闡釋。①洪大用:《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成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96頁。在新常態下,筆者試圖通過新興ENGO行動策略所凸顯的特點對“后政府動員式”概念進行嘗試性解讀,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后”的理解,借鑒“后總體社會”中“后”的含義,從時間階段上是指改革開放以后;進而具體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權力和資源相對分化的轉型社會,也是中國隨著環境NGO發展標志著“社會”領域出現的時期;二是“政府”的理解,主要是指在改革開放后“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職能轉型,逐漸從國家領域分離出來的有限的、局部的和具有一定依附性的社會空間,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創造生存和運作的契機;三是“動員式”,在中國特殊體制背景下由政府主導的社會公益性行動具有典型的“動員式”特征,這里重點強調轉型背景下對多主體共同參與環境治理的資源動員。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靠市場,環境靠政府”口號下形成的“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具有典型的“政府動員式”特征;但隨著環境形勢日益嚴峻、公眾環境意識的提升、環境規制加強、民間組織成長成熟,中國環境治理的主體日益多元化,十八大明確強調“依靠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參與的環境治理”,表明推動中國環境保護的主體逐漸拓展為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組織與公眾等多元主體。由于環境保護具有目標不確定性、純公共物品性、外部性、邊界模糊性等特征,而環境NGO成為政府和市場之外以組織化資源參與環境治理的必然選擇。基于當前大力推進社會治理的政策機遇期,新興環境NGO在不斷突破傳統“環保小世界”的行動實踐中能力得以提升,從而逐漸成為環境治理的真正主體,有利于推動中國環境保護“后政府動員式”時代的到來。
如上所述,當今不斷拓展政策環境和開放的市場為環境NGO的發展提供了生存與行動空間并激發了社會中豐富的資源與機會,但并不意味著環境NGO的前景一片光明和繁榮。相反,在轉型背景下面對復雜的社會問題與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發展中的環境NGO在參與環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復雜性,互聯網背景下環境NGO行動實踐如何突破“社會動員”的環保小世界;環境NGO與政府、企業、媒體以及公眾等主體互動的原則、限度和方式等,這些問題本文并沒有給出答案,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責任編輯:童志鋒、馬國棟)
Ac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L Organization in Chongqing
ZHONG Xing-ju
Abstract:By conducting a survey on the L environmental NGO of Chongqing, and give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transition society, this study found several limitations of using the ‘corporatism' and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the actions of environmental NGO. For example, it is diffcult to explain the special action strategiesbook=96,ebook=98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of practice from dynamic perspective, including growing up in the cracks by the way of ‘subtraction', building a normalization mechanism by multi strategies interaction, the coexist logical of nonconfrontation and non-cooperation and to get legitimacy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y restricting themselves. The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that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oriented by macro policy changes,market system reforms, and enhanced capacities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in China can alter from ‘government-ruled' model to ‘post governmentmobilized' model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the leader and enterprises, whereas the environmental NGOs and the publics are all the stakeholder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NGO; post government-mobilized
作者簡介:鐘興菊,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社會學、社會政策。(重慶,400044)
基金項目: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博士項目“基層主體參與環境政策執行過程的社會學研究”(2014BS041),以及中央高校重慶大學專項項目“社會力量參與環境治理的社會過程研究”(2015CDJXY)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