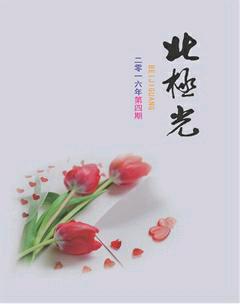刑法的客觀解釋立場
石佳宇
摘 要:刑法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內涵的闡述[1]。對于刑法條文該如何解釋,目前大陸刑法學界主要有主觀解釋說和客觀解釋說兩種觀點,而究竟該采用哪一種解釋立場的問題,已經成為了刑法學界的焦點問題和核心問題。然而,筆者認為,學界的爭論普遍沒有從整體的角度,具體歷史的分析問題,并且忽略了刑法解釋的一大主體——即法官在該問題中的作用。因此,筆者擬從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利用會話含義理論,站在法官審判具體案件時所處的立場,分析刑法解釋的立場應當并且只應當是客觀解釋的原因。
關鍵詞:刑法;客觀解釋
一、導論
認知心理學告訴我們,人是信息主動的探求者,并不是消極等待環境刺激才能產生反應的被動個體[2]。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也告訴我們,人的認識具有主觀能動性。人的這種主動性決定了人在認識事物,理解事物,解釋事物的過程中必然會經歷一個主動的認知過程,并且這個過程是一個“普世”的過程。在筆者看來,這個過程的要點就在于“認識”的過程。所謂“認識”的過程,在筆者看來就是一個“認識”陌生客體的過程,確切地說是一個“對話”或“會話”的過程。在面對一個新事物時,我們首先要通過該事物傳達出來的一定信息與該事物進行初步的“會話”這種信息的表達一定是遵循了一定規則,否則這種“會話”是不能進行的。這便是“會話含義”理論的基本點。而對于刑法的解釋,正是這種“認識”過程的反復再現,也是對于“會話含義”理論的反復應用。
法官作為刑法條文的主要閱讀者和解釋者,在理解和解釋條文的過程中必然也要經歷“認識”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會話含義理論”也不斷發揮著作用,這種作用決定著刑法的客觀解釋立場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
二、“認識”的過程——“會話含義理論”對刑法解釋立場的啟示
(一)“會話含義理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會話含義”理論最早是由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在1967年于哈佛大學以“邏輯與會話”為題作演講時提出的。他認為:人們在會話這一交際過程中必然遵循合作原則。在此基礎上,格賴斯提出了四條準則,認為遵循了這四條準則就是遵守合作原則。他們分別是[3];①量的準則:即所提供的信息量。②質的準則:所說的話力求真實。③相關準則:即所說的話是相關的④方式準則:即清楚明白地說出要說的話。
格賴斯的會話含義理論在語用哲學領域造成了很大的反響,但也有一些不足。后來很多學者致力于修改這一理論,并涌現出許多新的成果。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1984年列文森提出的“三原則理論”。
三原則論的具體內容是[4];第一,數量原則。包括說話人準則:即調動自己已有的知識,盡量不說信息量不足的話,除非被提供足量的信息。聽話人推理:即把說話人的陳述看成是建立在他既有知識體系上的最強陳述。第二,信息量原則。包括說話人準則:說的盡可能少,即只提供當下交際語境所必需的最少量信息,不冗述,不贅述。聽話人推理:通過尋找最具體解釋的方法對說話人傳達的信息進行擴展直到認定說話人的意圖為止。第三,方式原則。包括說話人準則:表達力圖簡潔,不采用偏詞怪詞,不用冗長結構。聽話人推理:如果說話人運用了不簡潔的表達方式,則聽話人要盡力理解并避免不必要的歧義。
(二)“會話含義”理論與司法的互動
然而,司法者對刑法的解釋是否是一種交際過程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法學界,早在幾百年前,著名法理學家奧斯丁就指出法律是主權者向司法者下達的命令[5],“命令”的比喻意味著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進行的特殊的對話。我國法學學者也有人認為司法活動是解釋者,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實的對話。事實上,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就已經將司法人員欲設為潛在的讀者,通過法律文本將法律理念與抽象的法律規則傳達給司法者,并期望他們在閱讀中能夠理解并找出解決個案的方法。而司法者在遇到個案難題時,也會不斷“追問”法條文本,尋找問題的答案,通過理解文本得出初步的答案后,再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和客觀情勢對答案的合理性進行審視,如果認為答案不適當,他就會向文本提出新的問題,并再次從文本中提取信息,經過多次反復直到得到滿意答案,這個過程即告停止[6]。可以看出,這樣的過程與傳統交際的過程十分相似。因此,司法者提問,理解和解釋法律的活動就是讀者與文本“會話”的過程。
正因為如此,這整個過程就會遵循列文森“三原則”理論。首先,在刑法解釋這一交際過程中,立法者,確切地說是法律條文扮演著“說話者”的角色,那么它理應遵循三原則中三個說話人準則。第一,就數量原則來說,立法者不會向司法者提供比其想提供,應該提供的信息更少的的信息,換句話說,通過文本表現出來的立法者的法律思維和價值,已經向司法者提供了在其能力范圍內最大的信息量。第二,就信息量原則來講,刑法文本遵循“惜字如金”的原則,凡是根據生活經驗和常規能補充,闡發,延展的信息,刑法文本都予以省略。如我國刑法第104條武裝叛亂暴亂罪中的一個罪狀——‘組織就省略了“組織多人實施”因為根據常規關系,個別人是無法發動武裝暴亂,叛亂的。最后,就方式原則來講,刑法條文并不會無端采用冗長,晦澀,有標記的表達方式,簡潔明了是刑法條文的特點。其次,作為刑法解釋的主體,交際過程中的“聽話者”,法官對法律的適用也符合三原則的要求。第一,司法者——作為整個交際過程的聽話者和法律條文的主要解釋者——他必須相信立法者已經將他所要表達的法律思想不余遺力的表達出來,即相信現有的法律文本是整個時空的立法者最大智慧的最強陳述。誠然,任何事物都有缺陷,刑法條文也不例外。但作為司法者的職業價值使然,相信法律,盡力執行法律,甚至信仰法律是司法者的職責。而作為法律的內在價值和本質要求,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言:法律不是被裁判的對象,而是被研究、被遵循、被闡釋、甚至是被信仰的對象[7]。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要求司法者對法律抱有一種積極的確信。而這種確信就是數量原則中“聽話者推理”原則的體現。第二,(下轉第頁)(上接第頁)關于信息量原則,正如上文所說,刑法條文雖然盡可能簡潔的表達一個規范,但司法者作為能動的主體,在與條文進行“交際會話”時必然會為了讓條文回答自己的問題而對條文本身的意思作自己的擴展解釋,從而在法條限定的范圍內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如果不經過這個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僅拘泥于法條原文,司法者將很難解決個案中的爭議焦點,發揮其作用。最后,關于方式原則,既然立法者和法律條文作為“說話者”不會無端使用冗長,復雜和有標記的表達方式,而如果用了這種表達方式,那么立法者就是在試圖表達其他的意思,而作為聽話者的司法人員,在適用這些法律時就該特別注意這些表達式的意思。表現在我國刑法中,就是刑法條文的司法解釋對許多詞語諸如“幼女”“國家工作人員”等都作了詳細的解釋。可見,司法者在解釋刑法條文時遵循了方式原則。
如上文分析,司法者在適用法律,解釋法律的過程中,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運運用了列文森三原則理論作為獲取信息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客觀解釋的方法才在獲取信息的“認識”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
(三)“認知理論”與刑法的客觀解釋
首先從說話者——即立法者和刑法條文的角度來講,立法者在編寫遵循數量原則,信息量原則,方式原則的法律文本時,其實已經不自覺地將客觀解釋預設為司法者將來獲取信息解釋法律,適用條文的基礎。因為在此時,立法者將司法者預設為文本的直接讀者,其根本和首要的目的是讓司法者解決個案問題,做到“有法可依”而不是讓法學家拿來研究或是讓學生學習。而涉及到具體問題,就不能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實際來適用法律,而這正是客觀解釋立場的要求,而主觀解釋要求的探求立法者原意,并不是個案審判中法官的工作,審判中的法官只有一個任務,就是解決爭議維護法律的尊嚴。
其次從聽話人——即法官的角度,客觀解釋是在這個“會話”過程中獲得有利于案件解決的信息的唯一途徑。第一,雖然法官信仰法律,無條件服從法律,但在“認識”的過程中法官也不是消極被動的。這種認同應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相信法條的確切性和預見性,即刑法文本沒有說的,司法者必須保持沉默,不能隨意擴大和縮小解釋。其二是相信法律的規定必然不會違反基本正義的要求,因此對于那些未被法律規定的正當行為,應當確認為其無罪,如正當防衛和自主行為[8]。這種信息的獲取是文本中體現不出來的,探求立法者原意也于事無補,因為立法者可能并未注意到這一點。因此,法官在獲取這一部分信息時必須結合社會實際及當下個案的狀況,做出客觀的評判,只有這樣,法官才能全面掌握案情動態。第二,正如上文所說,刑法條文的簡潔必然會使司法者在“認識”的過程中盡量擴大信息量的攝入。因為要完整地獲取信息,僅理解言語形式的“字面意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根據當時的語境推導出言語的言外之意。司法者在獲得刑法文本提供的簡潔信息后,必然會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從文本中解讀出直接意義之外的間接意義,字面意義之外的隱含意義,形式意義之外的實質意義,語義意義之外的語用意義。并以此在“認”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的信息量已達到其目的。這個“擴展”的過程真正需要的就是客觀解釋的方法,需要法官視野開闊,不僅從法條原文,更從社會實際甚至從道德與法律價值出發,高瞻遠矚的考慮個案中的問題。
四、結語
誠如上文所述,列文森三原則下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合作交際,解決刑法個案”的過程中,只有秉持客觀解釋的立場,才能完成刑法“保護法益,保障人權,解決個案”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陳興良:《教義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參見梁建寧:《當代認知心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3](美)格賴斯:《邏輯與會話》載《句法和語義學:言語行為》第三卷上.
[4]徐盛恒:《會話含義理論的新發展》,《現代外語》1993年第二期第30--35頁.
[5]奧斯丁:《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商務印書館.
[6]轉引自王政勛:《刑法的解釋立場是客觀立場——基于會話含義理論的分析》,《法律科學》2012年第三期第61頁.
[7]陳興良:《刑法知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8]轉引自王政勛:《刑法的客觀解釋立場》,《法律科學》2012年第3期第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