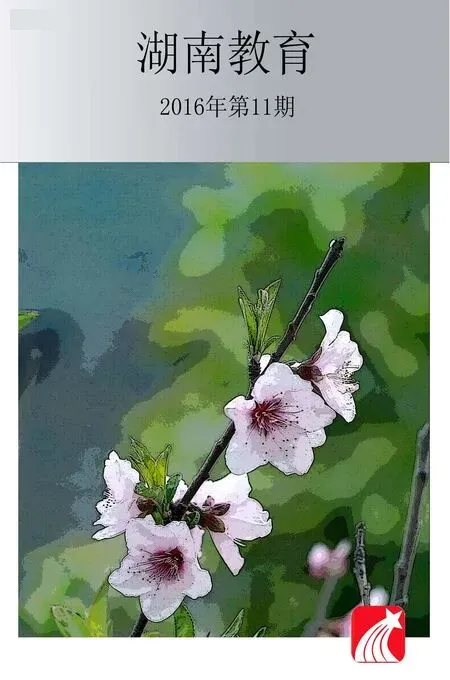山水游記二篇
于乾式
?
山水游記二篇
于乾式

張家界的雨
天子山披著淺灰色的罩衣,面帶冷冷的笑,一直笑到褲腳。這陰冷的笑比放肆大笑好,因而不熱,頭上頗有涼氣撫慰,感覺視覺寬敞。盡管人流如織,增加了熱度,卻還是感覺舒服。
金鞭溪卻一味曖昧,利用樹林中的涼風(fēng)推動(dòng),把一切的一切霧籠起來。金鞭隱入霧中;小猴子隱入霧中;溪隱入霧中,只聽水響;林也隱入霧中,不見風(fēng)騷。青峰疊嶂,若近若遠(yuǎn)。這就是善待。
情到深處,墜下淚來;霧到深處,落起雨來。
那雨,從霧里滲出來,擠出來,擁出來。先是細(xì)絲絲,如絲如縷如紗幔,使人想起長(zhǎng)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禪衣。似能看到肉皮,又看不清肉皮。極輕極輕,你感覺不到它的壓力,它卻漫天布著。你撐開雨傘,它卻跑到你的口袋里來了。
細(xì)絲越來越粗,成串成串掛起了珠簾,睜不大眼,看不盡簾。還有散珠子蕩來蕩去,歡蹦亂跳。金鞭溪快活地叫起來,發(fā)財(cái)嘎。它想把雨珠都擁進(jìn)懷里帶走,怎么帶得完呢?林子里珠光閃爍,寶氣四溢,像要成親了。猴子們張嘴接珠,像要成仙飛去。
七上八下的游客,披的雨衣成了水晶衣,打的傘成了玻璃傘,還有的什么也沒帶,滿臉滿頭濕漉漉的,不知是雨是鼻涕是眼淚水,嘻嘻哈哈,拍照留影,在水中踏踏踏。
到商店躲躲雨吧?
不躲!這雨是極好的空氣凈化器。山林中負(fù)離子多。深呼吸一次,勝過城里一百次啊!
一對(duì)老夫妻,手牽著手。來了一個(gè)獨(dú)身女子,著天藍(lán)色的連衣裙,足蹬黑色長(zhǎng)筒皮靴,雨傘下的一雙金絲眼鏡,瞟過來,瞟過去,閃著調(diào)皮的睫毛。莫非尋找難得的邂逅?
雨覺得機(jī)會(huì)來了,大點(diǎn)大點(diǎn)地敲打起來,黃豆大,沒有豌豆大。密密匝匝,像古代紡織機(jī)出紗,布起了天羅地網(wǎng),終于,將一個(gè)瀟灑男子絆倒了。時(shí)不我待!那女子立即跑過去牽起那帥哥,笑成了花臉。
你往哪兒跑啊,落湯雞們。水四面八方地流,奏開了交響樂。只聽到樹上沙沙沙,巖石上叭叭叭,金鞭溪嚓嚓嚓,還有“吳冠中”在哈哈哈。
躲不掉,就享受吧。張家界的山已幻化成海市蜃樓。我們就過一會(huì)兒神仙日子吧,哪怕一天也好。
桂林的山
“五岳歸來不看山”,說是說,建議還是看下桂林。
朋友是畫水墨畫的,去過桂林,酒宴間,要他畫個(gè)桂林山水看看。他抿一口酒,大喊一聲“好”,當(dāng)場(chǎng)潑墨,端起一碗墨水便往紙面上潑去!哇噻,紙面馬上一塌糊涂。他從容地濃墨重彩幾筆,嫩山露出來了,秀水流出來了,甚而似乎有水珠子彈出來。
有意思。
我決定實(shí)地欣賞一下,是在去年11月23日。那天天色陰郁,時(shí)有絲絲毛毛雨。如此情況,山勢(shì)就不鮮艷,不明朗;空氣里水分子多,就霧氣彌漫。整個(gè)的人大有醉翁之意,朦朦朧朧,踉踉蹌蹌,稀里糊涂闖進(jìn)朋友的水墨畫中。
桂林的山與五岳不同,與張家界亦不同,雖都是石質(zhì),妙就妙在桂林的山是女性的,是水托起來的,一生都和漓江這娘兒依偎在一起,說話也軟綿綿的,怎么能不女性化呢?她的潔癖也聞名遐邇,不是一年洗一次澡,而是時(shí)時(shí)洗浴,楊貴妃也做不到啊。所以全身上下晶瑩剔透,如處子一般,毛茸茸的,蔥嫩嫩的,那么豐潤(rùn),那么美麗,那么年輕,那么單純。

我想舟楫?dāng)n岸和她們拉拉手,艄公笑曰,只可遠(yuǎn)觀,不可褻玩焉。那山有的扭動(dòng)腰肢,似在開鏡試新衣;有的踮起腳尖,似在顧盼心儀的寶貝;有的寬衣解帶,似要貪涼一下;有的舉起了棒槌,似要敲打無情游客。忽然,山的深處,霧的隱處,似有彩帶飄閃,咦喲——永不消失的民歌手劉三姐的清音隱隱約約傳來。咦喲——由于劉三姐的歌在腦中老是唱,便也覺得劉三姐老是跟著我身后轉(zhuǎn),趕也趕不走,幸福死了!
水里面的山更有情趣。山麓接著水面,山尖卻插入水宮。一個(gè)漁翁搖櫓而來,舟上站立一排鷺鷥。他一揮竹篙,鷺鷥們紛紛下水去尋找去年丟失的相思。余下他獨(dú)自思忖,要和三姐對(duì)歌一番。奇怪的是,千呼萬喚,怎么還不出來呢?
桂林的山不僅撩撥人的柔情,還開導(dǎo)人的智性。好端端的平地,好端端的水面,兀自凸起一山,不倚不靠,不挨挨擦擦,也不上下一般粗,而是如羅漢,如觀音,穩(wěn)穩(wěn)當(dāng)當(dāng),正靜靜地斟酌人類的幾大命題:色即空,空即色;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學(xué)而不思則罔;自強(qiáng)不息與厚德載物;飲水思源,崇尚感恩。
在水中看山是青色,在霧中看山是灰色,在日中看山是乳色。綠色常有,但未形成大氣候。桂林,應(yīng)多栽點(diǎn)桂樹啊。既不能違反天人合一,要順應(yīng)環(huán)境;又必須自主改善。自主才有個(gè)性,自主才有人格,自主才有創(chuàng)意。那就是說,物和人是在同中取不同,世界才能記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