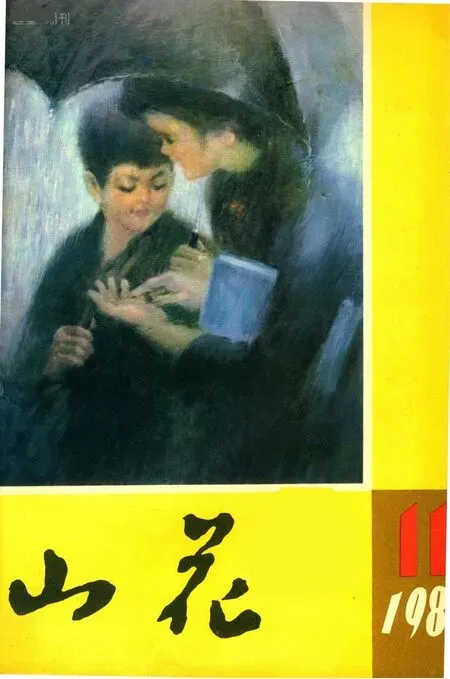尋常冷暖,百姓尊嚴
這里我想談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市井小說。這是當時比較松散的一個類型,一般涉及汪曾祺、陸文夫、劉心武等寫城市下層平民的一類小說,但比如王安憶早期寫弄堂和小雜院的作品,似也可以歸入。我想從題材來講,“下層平民”是要強調的,這使它區別于都市小說:如果說都市故事發生在咖啡館酒吧,主人公是麗人紳士,那么市井故事則在弄堂街市,寫的也是普通勞動者。但我下面想討論的不僅僅是代表性或反映現實的問題,這里涉及到如何寫普通勞動者和他們的生活,也就是“審美形式”的問題。實際上現實主義雖在知識論上聲稱要反映現實,它在美學上卻總是在賦予現實以某種審美形式,比如19世紀現實主義就賦予了新興資產階級生活以英雄史詩的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八十年代初市井小說才引起我的注意,這些市井小說賦予了市井生活怎樣的美學形式呢?
一
就市井小說的總體美學風格,汪曾祺在1988年出版的《市井小說選》的序言里有一個精當的說明:
“市井小說”沒有史詩,所寫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說”里沒有“英雄”,寫的都是極平凡的人。“市井小民”嘛,都是“蕓蕓眾生”(《<市井小說選>序》)。
這里不僅涉及內容,更是提出了“反史詩”的瑣碎的市井美學形式,這很關鍵。亞里士多德提出史詩之所以和散碎的歷史事件不同,是因為它的意義被統一在了英雄行動(敘事)之中。受亞里士多德影響的盧卡奇后來在《小說理論》里把小說看作在散文世界里重寫史詩的美學努力:現代生活是瑣碎的,但小說仍在美學層面上追求總體性意義。盧卡奇對19世紀現實主義的洞察無疑是深刻的,但他對史詩和英雄的強調也帶來問題的另一面,即非英雄的瑣碎生活是否就喪失了美學資格?這在亞利克斯·沃洛克(AlexWoloch)看來是敘事學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這位論者在《一個和多個》一書里提出了次要角色的“異化”現象:19世紀小說在塑造資產階級英雄個體的同時,也在敘事內部“壓扁”了勞工等邊緣角色,這些角色的內在性和生活世界在敘事組織里被剔除,他們沒有性格,少言寡語,不過是英雄完成行動的工具性要素。比如在普魯斯特筆下,一個洗衣的女仆就是洗衣的人,一個花匠就是鋪花徑的人,關于他們的描述都被放在句子末端,這在句法層面上就否定了下等人獲取自己視點的可能(見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在完全不同的新時期語境里,汪曾祺提出了類似的下等人視點問題,這涉及到在美學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否也有角色異化的問題。其實早在五十年代初趙樹理就提出過類似問題。他當時編輯《說說唱唱》,提出“用人民大眾的眼光來寫各種人的生活和新的變化”。這里“人民大眾的眼光”不是左翼精英知識分子的眼光,也不是革命群眾升華了的眼光,而是在評書、曲詞這些民間文藝里提煉出來的市井普通人的眼光——趙樹理當然考慮到反封建、“提高”等問題,但他爭論的是民間文藝所表達的下層市井的“較低的”視點,尋常的市井故事,平民樸素的倫理生活有沒有在美學上發展成人民文藝的可能?新政策下的《說說唱唱》很受讀者歡迎,但這種對主流的挑戰遭到左翼精英主義和官方話語的聯合狙擊,很快就失敗了(見張均:《趙樹理與<說說唱唱>雜志的始終》)。汪曾祺在五十年代初做編輯時是趙樹理的助手,在《說說唱唱》經歷了雜志被批判、調整、解散的整個過程,他雖對這場爭論沒做評論,但晚年對趙有溫馨的回憶。實際上在五六年他就寫過一篇文章批評看不起大眾文化、不理解民間情感的錯誤傾向(汪曾祺:《魯迅對于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還提出民間文藝是勞動者文藝,是“剛健、清新”的文藝。甚至在文革強調英雄升華的“三突出”原則下,在汪曾祺參與創作的阿慶嫂身上,是否依然保留著尋常的市井眼光(如“人一走,茶就涼”)呢?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新時期文藝政策放松,汪曾祺避開抽象的工農兵去寫下層的工匠挑夫,在上面這個脈絡里看是回到趙樹理的平民立場。不過在新時期反英雄史詩,汪曾祺直接針對的是當時改革、傷痕、知青文學里的(悲劇)英雄主義,這一點汪在《賣蚯蚓的人》一文里說得很明確。汪曾祺宣稱他在城市貧民——賣蚯蚓的人——身上看到了審美意義,同時嘲諷那些自詡“走在時代前面的人,呼嘯著前進的,身上帶電的人”,在后者看來,下層貧民只是社會無意義的填充物。如此刺耳的精英主義言論不可能出現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這和八十年代新啟蒙話語有關;在敘事層面這時下層的次要角色的異化在文學里也頻頻出現了,比如《班主任》里的宋寶琦,《爬滿青藤的小屋》里的王木通等。在這樣一個話語環境里,市井文學整體上替小民視角辯護,在美學上嚴肅回答了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問題:普通人瑣碎生活如何獲得審美意義?這是一個大問題,下面只簡單提提陸文夫等的反諷敘事和汪曾祺等的風俗描寫。
二
陸文夫在1956年寫《小巷深處》,寫改造后的妓女在新生活里的矛盾,已透露出他向下層探求的努力。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工廠農村,這種向下的經歷反過來在創作上給他帶來了幫助。他在新時期作為右派分子寫作,情感上卻更認同市井,這就使他在處理知識分子和下層貧民視角上有了“反諷”的張力。
這里的反諷我用的是亨利·詹姆斯的意思。詹姆斯發現,在寫作中很難避免將次要人物扁平化,因為一旦次要人物的內在視點膨脹,就會和主導視點沖突。我們可試著假設如劉心武按照蘇童的方式在《班主任》里發展宋寶琦這個市井少年的視點,那么啟蒙知識分子張老師就會顯得可笑,小說也就成了反諷。但詹姆斯的保守性阻止了他去進一步闡發視角沖突可能帶出的不同階層間的文化與生活世界的沖突,而這個沖突卻在陸文夫的《小販世家》《美食家》等作品里獲得了復雜的表達,作者有意讓本該被壓扁的市井小民視點膨脹起來,從而腐蝕、瓦解了“我”的啟蒙視點。
在《小販世家》里,“我”和小販朱源達曾是好友,但自從“我”成為革命干部后就成了朱的啟蒙者,決心要改造“朱”和他的生活。這一種面向他者世界的征服性敘事本該寫成經典的“成長”故事,比如在《綠化樹》或《北方的河》中的敘事,但在這個作品里“我”雖在政治經濟上都比朱優越,具有抽象話語能力,在敘事上也控制著視點,卻始終是一個孱弱的行動者:“我”被朱陰暗潮濕的生活世界所震懾,后者侵入并顛覆了“我”的敘事控制,啟蒙也因之失敗。相比于“我”的抽象理性能力,朱的優勢在于與“物”的親近,一方面是他販賣的餛飩、鮮魚活蝦、菱角等物的世界帶來的色彩氣味光澤,這些描寫性場面總是無聲無息地滲入到“我”的抽象理念之中,顯示出“物質”對“精神”的激烈反抗,而這一美學路徑開啟了后來新時期文學中的世俗化趨向。第二方面的力量則來自對朱的市井生存的局促性的認識,他深陷在生計窘迫之中,他的辛勞和狡詐因此是迫切具體、不容否定的。承認市井局促意味著對革命的道德理想主義的放松,陸實際上是將倫理評判放低到粗糙的庸常物質層面上,他的市井絕不理想,很多時候很冷峻(比如《井》《還債》),但他對底層人在實際生存中的掙扎有了更多體諒同情——在更廣闊的寓意上談,市井貧民的泥濘就成了革命理想或啟蒙理性的解毒劑,這些抽象所不能到達的生活弄臟了美麗的宏圖設計,瑣碎的描寫因而構成了宏大敘事的反諷性力量。
但朱的生活世界的力量還來自第三個方面:朱源達的生活雖泥濘,但這個人物身上有剛健向上的力量,他是通過勞動獲得生活意義和個體尊嚴的,所以他的敘事視點才能與“我”的視點發生經典的馬克思-黑格爾的主奴辯證的顛倒——勞動獲得的實踐理性對抽象理性的顛倒。這在王安憶的《流逝》里被概括為“自食其力”,在這個作品里視點沖突發生在少奶奶瑞麗和文革時自食其力的勞動婦女瑞麗之間;而在《小院瑣事》、《庸常之輩》里,王更積極地開拓了“庸常之輩”的生活理想,透露出面向新時期、正面建設市井美學的鮮亮色彩,而這在汪曾祺八十年代初的小說里則表現得最為充分。
三
蔡翔在討論社會主義文藝時談到過“勞動烏托邦”,提出中國革命在顛覆“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意識、奠定勞動者尊嚴政治上的重大意義(《<地板>:政治辯論和法令的“情理”化》)。林凌則在八十年代初小說中發現了這些遺產,在他看來汪曾祺的抒情小說是書寫普通勞動者的史詩(《“抒情”作為“史詩”的完成》)。這個看法若放在新時期頭幾年市井寫作的整體風格中來看,是不突兀的,這里關鍵是要看是勞動還是財富成為敘事意義的起點:老舍的祥子愛拉車,但拉車是為了買車,勞動為了積累財富,小說敘事是通過個人追求財富(的失敗)組織起來的,是經典的19世紀現實主義套路;但在汪曾祺筆下,勞動所交換的是具體的生計,同時勞動自身就可以帶來了尊嚴和生活意義,這個圖景在美學上有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的支持。
七八十年代之交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被熱烈討論。“本質力量對象化”這個原則源自席勒和浪漫派的生產美學,黑格爾從中引出主體外化的問題,馬克思則把外化落實到勞動中,但這些思考都來自工匠的非異化勞動這個美學模型(哈貝馬斯認為這是馬克思美學理論的根本困境,見哈貝馬斯著《現代性的哲學話語》)。資本主義異化勞動導致了勞動審美意義的消失和剝削的誕生,馬克思的本意是要“揚棄”異化、在社會主義集體勞動中恢復人的類本性的;但這時期的美學卻普遍傾向于退回到非異化個體勞動,產生了大量關于集市、小生產者的文字,并成為當時個人主義話語的一部分。不過這個個人理想是和勞動理想結合在一起的,比如朱源達在“餛飩挑子”上“下餛飩”的勞動場面,這場景在汪曾祺的《晚飯花·三姐妹出嫁》也出現了。汪曾祺寫工匠、挑夫、小買賣人的勞動,《受戒》里把“當和尚”也寫成手藝人的職業;而《大淖記事》中則有大量風俗性描寫,從雞鴨炕房到小生意人,再到打錫器的錫匠、大淖東頭的挑夫——寫這些人和風俗實質上是在寫具體的勞動和游戲場面,人化自然,勞動者“清新、剛健”的生活和生產世界。汪曾祺的作品最主要的敘事張力總是在勞動者自足的生活世界和外界破壞性的社會政治力量之間展開的,外在力量很容易暴力顛覆微小的市井生存,這是汪曾祺筆下的冷色,但故事的視點往往是從勞動者理想的生活世界出發的,這已經由敘事展開之前散碎的風俗描寫奠定了,于是故事最終總能顯出和諧、歡快的美學風格。
由此汪曾祺的風俗世界透露出更平等更和諧的社會理想,這也是汪的人道主義的基石,而這在當時的市井寫作中是不特殊的,這一時期市井小說里出現了不少對平等而寬容的勞動者的市民社會的憧憬,這在今天看來有些讓人驚訝。比如劉心武在《大塔》里就給出了一幅胡同口迎親的風俗畫:新郎大塔是胡同里熱心腸的搬運工,出了事故后成了獨臂,大塔結婚時讓胡同里他照顧過、也照顧過他的老街坊來“迎一迎”,于是就聚集起了處長、經理、主治大夫、小學校長和其他迎親群眾:大塔的新媳婦是個很丑的羅鍋,但這個姑娘“鎮定地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某種重大許諾的應驗”,人群起初很驚詫,但很快鼓起掌來,新人也在鞭炮聲里鼓掌,于是這個場景充滿歡快、和諧的氣氛。這幅“迎親圖”在美學風格上很接近黑格爾所闡釋的荷蘭風俗畫,新郎、新娘殘廢的軀干是自然意義上的丑,但勞動者的品行、夫妻倆的自信自尊、胡同眾人的平等溫和都給“自然”灌注了人類美的生氣。當然《大塔》里也寫市井殘酷,比如經濟窘迫社會歧視等,這是風俗畫的底色,但劉心武壓著暗色寫亮色,這就給平凡個體和瑣碎生活帶來了理想性,和汪曾祺很接近了,這都和當時勞動者美學所奠定的小民尊嚴有關。這樣的作品當然具有意識形態的空想性,然而也是審美上的烏托邦,隨著后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我們在之后的小說里很難再看到這樣的尋常冷暖與百姓尊嚴了。
作者簡介:
謝俊,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紐約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批評理論、當代中國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