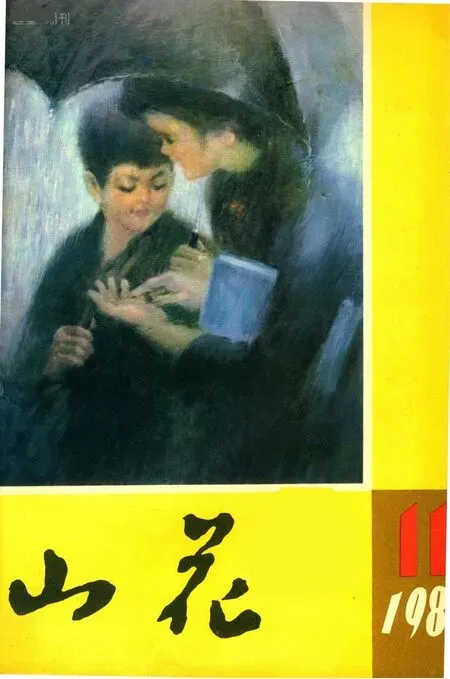格非:面對先驅的寫作
張莉
“重構或歸返中國敘事之路”這個題目讓我想到了2001年。那一年,格非老師剛剛從華東師大調到清華大學,那是秋天,他為研究生開設他的第一門課。我們都很好奇,這位新銳的先鋒作家會給我們講什么。——沒有討論博爾赫斯,沒有討論馬爾克斯,也沒有討論米蘭·昆德拉,那個學期我們討論的是中國小說傳統,或者說是中國小說傳統的財富。中國戲曲如何在一桌一椅的簡單背景下表現那么激蕩人心的故事?魯迅刻畫人物是如何做到如此簡筆而又如此傳神的?15年過去,很多具體討論已經變得模糊,但是,那些問題卻一直潛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我懵懂地意識到,那可能是他正在進行的一些思考,而這個思考深具先鋒性。
2004年,當我讀到《人面桃花》第一句:“父親從樓上下來了”時,非常激動。我意識到它與我三年前的課堂討論形成了暗在的呼應。今天看來,《人面桃花》的寫作是一個開啟,是另一個起點,由此,格非開始返歸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卻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傳統。父親留給秀米財富,但這個財富是需要破解才可以成為財富的,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它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可能就分文不值。當然,這部小說中讀者也難以忘記張季元這一人物,革命者的另一種形象,很可能更接近真實的一種形象。作為革命中人,如何理解革命,如何畫下我們最早對于烏托邦的想象,《人面桃花》是一個緣起。
2009年,讀《山河入夢》時,我想到的是格非對歷史的認知和書寫是如此地別有路徑。那位共和國的縣長,秀米的兒子譚功達,他的情感際遇和他的抱負一樣荒誕,具有某種隱喻性。但是,坦率說,當時最吸引我的是2011年出版的《春盡江南》。《春盡江南》氣質優雅淳正,在細節與事件中追求一種具象的真實,但同時,小說也罕有地具有對當代社會的整體性認知。在閱讀中,你會強烈意識到,在這個虛構的世界里,作家創造和構建了一個別樣的現實,一個脫胎于當下但又比當下更觸目驚心的現實。在當代中國,如何書寫現實是困難的,這幾乎是每一個作家的困境。格非的意義在于,他以獨有的路徑尋找到了談論現實和精神疑難的方式。
從2004年到2011年,七年的時間里,格非以“江南三部曲”完成了一個整體的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思考。關于革命,關于烏托邦,關于歷史,關于現實,更關于世道與人心。2015年8月,在茅盾文學獎評審期間,我又用集中的方式對這部作品進行了重讀。如果說以前的閱讀是從《人面桃花》順流而下,那么,那一時期,我試圖從《春盡江南》逆流而上。我對三部曲有了更為深切的整體認識,我發現,每一部都有今人與古書的對話,或者說都與歷史對話。
尤其對《春盡江南》的譚端午印象深刻。面對時代,他仿佛是個袖手旁觀者。但是,那些對過往的念念不忘,那些他閱讀的詩章和古書都表明,他在思考,也在抵抗。小說中他閱讀歐陽修的《新五代史》的行為尤其令人難忘。敘述人說,那是一本衰世之作,可是,借陳寅恪說法,歐陽修幾乎是用一本書的力量,使時代的風尚重返淳正。
那么,讀書人端午的感受如何?“端午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兩個地方讓他時常感到觸目驚心。書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憂卒’三個字一筆帶過。雖然只是三個字,卻不免讓人對那個亂世中的蕓蕓眾生的命運,生出無窮的遐想。再有,每當作者要言那個時代發點議論,總是‘嗚呼’二字開始。‘嗚呼’一出,什么都說完了。或者,他什么話都還沒說,先要醞釀一下情緒,為那個時代長嘆一聲。嗚呼!”嗚呼!這是當時讀者的嘆息,恐怕也能傳達今日讀者讀史的感慨。
這邊是古書,是我們走過的歷史;另一邊是此刻,是正在經歷的現實。在我看來,這是《江南三部曲》隱在而迷人的結構。而現實寫作中,格非讀《金瓶梅》,他出版了《雪隱鷺鷥》,關于《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這是我們大家都看到的。我想,他也在讀《史記》,在茅盾文學獎的獲獎感言中,他梳理了茅盾、老舍、巴金、李劼人等人奠定的現代長篇敘事文學的傳統;也梳理了由《水滸傳》和《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說的傳統;進而他追溯了被我們幾乎快要忘記的但又深深影響我們寫作的史傳文學傳統,在那里,《春秋》和《史記》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從而,他辨認出古人寫作的抱負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風俗。”由此,他回到今天,“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文學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矯正力量。文學寫作不僅僅關乎娛樂和趣味,也關乎良知,關乎是非,關乎世道人心。”
一面是寫下優秀文字的前人和他們構建的傳統,一面是對傳統進行重新理解的當代寫作者。把格非十多年,或者更長時間里有關作家寫作的思考并置在一起,我們將會意識到,中國敘事傳統之于格非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給養,是一種勇氣和力量。這也標志著,作為作家,格非深刻意識到了“個人”與“傳統”的關系,他以寫作思考“當代”與“傳統”的關系,思考屬于作家的“歷史意識”。當然,這里所說的作家的“歷史意識”并不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么簡單和淺表。
這里的“歷史意識”更接近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所說:“歷史的意識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結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性的。同時也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我想說的是,這些話評價格非的三十年創作之路非常恰切,他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在時間長河里的地位時,他由此意識到自己與當代的重要關系,我以為,這也是這位作家之所以優秀的前提。
“因為當一個人寫詩時,他最直接的讀者并非他的同輩,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驅。是那些給了他語言的人,是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 布羅茨基在《致賀拉斯書》中說。寫作者的另一個使命是常常被今天的我們所忽略,即,寫作者要面對那些給了他語言的人,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那么,我們如何面對傳統寫作就是如何為我們的先驅寫作。作為寫作者,我們能否在先驅的基礎上前進一小步?今天,我們常常討論中國文學的主體性,我認為主體性也應該體現在這里,即作為后來的寫作者,我們如何在傳統的鏈條里成為我們自己。
在我看來,《江南三部曲》是承襲了中國敘事優秀傳統的寫作,是作家自覺面對先驅的寫作。“假如我們研究一個詩人,撇開了偏見,我們卻常常會看出: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我以為,格非和《江南三部曲》中最好的部分是他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中國敘事傳統中最不朽的那部分。由此,他不僅僅使自己成為中國文學傳統寫作中的一員,也使自己的作品成為了優秀傳統小說鏈條中堅固的一環。格非和他的寫作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寫作者在今天的寫作意義,也有力地證明了寫作者在我們時代的意義所在。
今天,我們為什么要討論“重構與歸返中國敘事之路”?當然因為中國敘事之路是我們的珍稀財富,但是,我想,這個題目也在提醒我們,每個寫作者不僅僅是在面對同輩與后人而寫,也是在面對我們的先驅而寫。作為作家,得認識到我們是在面對先驅而寫,也得思考我們該如何面對先驅而寫。當然,這樣的寫作和思考都極具難度,每前進一小步都困難重重。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包括格非在內的中國寫作者們,都是在那個“永久與暫時”的時間長河之中,是在行進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