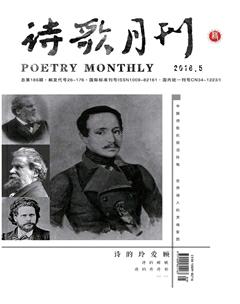化歸于北土的金桔
辛茜
昌耀離開我們15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即使內地也遇到了多年未見的風寒。到了三月,風已不那么刺骨,青海高原的冬天就要過去了,可是,昌耀,你在哪兒呢?那邊的日子過得怎么樣,和這邊一樣有煩惱有委屈有歡喜嗎?
窗外陽光正好,透過帷幔落下一地金子似的斑紋。
捧起《昌耀的詩》,極鐘愛的一本詩集,扉頁上有他2000年2月17日于病榻前為我留下的簽名。那一刻令我難忘,如同昨日,他的手指微微顫抖,蒼白如紙。
昌耀的詩是讀不夠的,每一次,都有不一樣的感覺,有不一樣的熱浪止不住地撲人心懷。想起他論及詩歌創作時,癡迷、孤寂的面容,想起他離開家鄉時經歷過的、他此生最為不忍的一幕——與母親的“話別”,心里便會泛起酸痛。
那是昌耀瞞著父母入伍,赴遼東邊防的前幾日,母親終于打聽到他住在一處臨街店鋪的小閣樓,母親由人領著從一只小木梯爬上樓時他已不好逃脫,于是耍賴皮似地躺在床鋪裝睡。母親已有兩個多月沒有見到兒子了,坐在他身邊喚他的名字,然而他卻愣是緊閉起眼睛裝著“醒不來”。母親執一把蒲扇為兒子扇風,說道:“這孩子,看熱出滿頭大汗。”母親坐了一會,心疼兒子受窘的那副模樣就下樓去了。戰友們告訴他:“沒事了,快睜開眼,你媽走了。”當他奔到窗口尋找母親,母親已走到街上,只來得及見到她的背影,穿一件緄邊短袖灰布衫、打一把傘、孤獨走去的背影……
那一年,昌耀13歲,他意識不到,這就是與母親的訣別,他只想著如何逃脫母親、母親的牽掛。第二年,母親去世了,噩耗傳來時,昌耀嚎啕大哭,旁若無人,而與母親的所謂“話別”也成了他一輩子的隱痛。
昌耀開始寫詩,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事。那時,他還是一個少年,一個離開家鄉湖南桃源,跟隨英雄部隊向前線挺進的抗美援朝戰士。1953年,剛滿17歲的昌耀在元山負傷,從硝煙彌漫的朝鮮回到祖國。1955年6月,由河北省榮軍中學高中畢業,報名參加大西北開發,來到群山縱橫、莽莽蒼蒼的青海高原。
沒有了母親的昌耀,以為沒有了牽絆,一心向往開拓西部疆土,把自己看作過繼給北國的孩子,打算將青春獻給西部蒼涼的大地,在一闋《南曲》中,他稱自己是“一株化歸于北土的金桔”。
這略顯感傷又單純的理想,濃郁地表現在他早期的詩歌創作中,包括描繪朝鮮人民軍女戰士于風雪中奔赴前線的詩作、在青海貴德體驗生活時為勘探隊員寫下的《車輪》《林中試笛》,這些詩雖顯稚拙,僅得之于間接經驗與青年的熱情,卻已顯出不同尋常的質樸、峭拔。然而命運無常,昌耀的生活受到時代風云的極大沖擊,在經受風雨磨礪、重重苦難后,這位富有理想主義、浪漫情懷的受難者,一生只能以詩歌創作表達情感、求得精神的自由了。
歷經三十年的苦難滄桑,進入1990年代后,他的詩變得更加深沉厚重了,但仍不失其滾燙的理想情懷。比如1991年2月4日,立春之日寫下的《暖冬》:
暖冬的泥土在崖巔保留著圣火的意念。
涸澤為萎陷的秋水刻下退卻的螺紋。
推土機佩一把鏟刀向著進發的原野大肆聲張。
像孤獨的旗幟調轉身子而又突突遠馳。
長久地沉默只有三五座橋涵龜縮河渠。
傾聽歲月這般逝去總是洶洶不止。
暖冬的崖巔保留著圣火的意念,意念是大地的火焰,是昌耀心底里無法泯滅的生存的欲望,也讓他的詩發出了纖夫用力時低沉的胸音,冬天的陽光,則是一張皮膚,雖歷經風雨酷寒仍富鏗鏘的色塊。是蔻丹。是挑戰。是濃稠的焦油。
那年景多么年輕多么年輕真是多么地年輕。
他獨自奔向雪野奔向雪野奔向情人的雪野。
他胸中火燎胸中火燎而迎向積雪撲倒有如猝死。
他閉目凝神閉目凝神等待心緒漸趨寧靜。
仿佛只在冰床安息他才得以從容品味蓬勃之生機。
強烈的感情推進,一再重復的語式,令詩人亢奮起來、年輕起來,覺得自己從未衰老,從未有過衰老的痕跡,覺得自己會永遠停留在那個時代,為那個年月的激情與火焰吶喊。這究竟是昌耀為理想追逐出路的掙扎,為痛惜命運無常發出的幽嘆,還是因為母親的背影,留下的遺恨。
1990年代之前,昌耀的詩已引起詩壇矚目。但他不像有些人說得那樣冷漠偏執,也不像有些人說得那樣狂熱激昂。他內心透明、簡潔,從不拒絕平凡,他所處的環境與情感經驗獨立自我,他的詩融入了時代和生活,又具備了堅韌、力度和空間感,有節奏、有彈性,還有沉默,只是將外表的怯懦與內心的高傲、生存的艱辛與精神的富華凝成了一種高古簡約奇崛的正大氣派,將自己對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一人一景、家國之愛化人宗教之境,最終在經歷了西部荒野、人情冷暖的拷打之后,挾艽野之風、青海之云、阿尼瑪卿之雪,如一股颶風向中國詩壇撲來,遮天蔽日。
隨著他的橫空出世,西部詩風也成為一種絕響傳遍四野。
大路彎頭,退卻的大廈退去已愈加迅疾。
聽到滴答的時鐘從那里發出不斷的警報。
天空有崩卷的彈簧。很好,時間在暴動。
我們早想著逃離了。但我們不會衰老得更快。
這是寫于1992年10月10日的《花朵受難》,昌耀對于自然、事物、人類情愫的感覺異常敏銳,在抒情達意、展開視野,擴大人生領域的建構上,提高著心靈的水準,培養著寬厚仁慈的氣度,與生活緊密,與生命同在。讓詩的寬度,以及對人生了解的深度,產生了無限可能的意義,這種可能的意義使昌耀的詩無比輝煌,永遠輝煌。
俯身從飛馳而過的車輪底下搶救起一枝紅花朵。
時間對抗中一枝受難的紅花朵。
花朵是一種意象,這意象是詩人自己。
修篁啊,你知道大麗花是怎樣如同驚弓之鳥
墜落在車道的么?似我無處安身。
你知道受難的大麗花是醉了還是醒著?
似我無處安身。
一枝車輪底下的紅花朵,讓敏感的詩人動了情,想到自己,想到命運。隨地崩潰枯萎的瞬間,即是花朵承受苦難的過程,也是讓天性活潑、本質憂郁的詩人以詩的沉郁、蒼勁、高質、精微征服詩壇的原因。
沒有一輛救護車停下,沒有誰聽見大麗花呼叫。
但我感覺花朵正變得黑紫……是醉了還是醒著?
我心里說:如果沒醉就該是醒著。
昌耀是執拗的。他追求藝術的深度表達與完善,不受任何藝術觀念的約束,更不愿放縱自己;他的詩作個性鮮明,卻又出自生活本身,瓦罐、燈塔、蘋果花、西關大橋、姑娘的蘭花指都是他詩中的主體。一切努力之后,他對自己說:前方灶頭,有我的黃銅茶炊。
昌耀是真實的,從里往外散發著硬骨頭的味道,與世俗格格不入,不善虛情假意。雖蒙受痛苦卻依舊善良、慈悲,用心貼近大地,用不同于常人的姿態感應生活、承受生活、想象生活。命運摧毀了他、造就了他、成就了他,讓他超越自我,以詩的方式活著,純粹、驕傲、自我、無媚態與粉飾。
這是他的圣桑《天鵝》:
哀莫大兮。哀莫大于失遏相托之愛侶。
留取夢眼你拒絕看透人生而點燃膏火復制幻美。
感慨之余,他的詩仍無感傷今日凄涼、悵惘來日離合的悲苦,詩境生動、意象完整,不論傷悲、情愛,還是親情,早已超越個人經驗,走向了精神祭壇,如意念在火中冶煉,在波濤中洗滌,最終變得雕刻般冷靜明晰。
偉大的詩可能產生的意義,是詩人難以預料的。昌耀生前不曾想到,他的詩會在未來的日子里,成為熱愛詩歌的人們反復詠嘆、隨時生長著的生命。昌耀走時正值創作力成熟、充沛的時候,但病魔是這樣的無情,來不及讓他感覺真實的幸福、吮吸玫瑰的芳香。
少年時與母親失之交臂的訣別,注定了昌耀一生都與愛擦肩而過。他一生都在尋找愛:母愛、情愛、性愛,家國之愛,但命運無情,他終其一生,未尋找到真實的愛。他的愛只活在詩里,活在大荒之中。
他最后的愿望,是讓自己這株遠離故土的金桔重返家鄉,與長眠在那里的母親相會……
寫了一輩子的詩,他最想說的,也許就是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