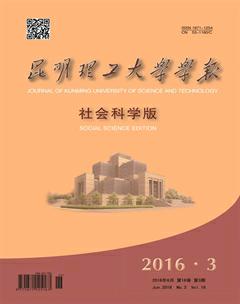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的多中心分析
丁澍++劉芬++羅志敏++繆柏其



摘 要:圖書館及其使用狀態是維系高校教學質量的三大支柱之一,對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特別是自學能力、創新能力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分析不同類型、不同地域、不同層次高校圖書館的使用頻率及其影響因素,中國現場統計研究會教育統計與管理專業會通過其組織的多中心研究,對圖書館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調研。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確定影響因素并對其影響程度進行量化。研究結果表明,各高校存在共同影響因素,其中制定學習計劃、學習能力的影響最重要,同時也存在各自特有的因素,如政治面貌、每月開支等。對于這些因素,學校應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干預。
關鍵詞:教學質量;圖書館;使用頻率;累積Logistic模型
中圖分類號:G250. 7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1254(2016)03-0088-08
A Multi-Center Analysis on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Learning Stat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requency of Library Use at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DING Shu1,LIU Fen1,LUO Zhimin2,MIAO Baiqi3
(1.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3.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Anhui, China)
Abstract:The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specially the ability of self-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use of library of some different kinds of universities,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Branch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Statistics organized a multi-center survey on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learning state in late 2010. Quantitative methods are applied to discuss the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common factors among all the universities, and course plan and academic abil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Meanwhile, there are some uniqu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status, monthly expenses, etc. Finally, universities can take certain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libraries.
Keywords:quality of teaching; libraries; frequency of use; cumulative logistic model
一、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多中心研究的緣起
本科教學質量一直是教育部門的關注重點,目前課堂仍是我國本科教育的最主要實施場所,而圖書館及其使用狀態作為維系高校教學質量的三大支柱之一,肩負教育和信息服務兩大基本職能,是重要的教輔機構,被稱為教室外的“第二課堂”。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者都非常重視圖書館及其使用狀態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例如,Lane認為,要重視圖書館對大學生教育結果的影響[1];Hiscock提出,圖書館需要通過研究圖書館利用與學生教育結果間的正相關關系以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2]。Powell提出,高校圖書館應展示自身對學業成果的影響[3]。至于國內學者,蓋世田和霍燦如提出,高校圖書館必須加強學生相關圖書閱讀研究,使學生認識到閱讀和自身成績間的關系,由此來宣傳、推薦圖書閱讀[4]。鄒聲威和俞培果發現,由圖書館服務的總體來看,圖書館館藏的借閱頻次與學生相應的學習成績呈明顯同向變化關系[5]。吳英梅和何璨發現,圖書館利用情況和學業科研情況之間呈現正向相關[6]。喬慧君和周筠珺認為,學生利用圖書資源學習的狀態是決定其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學生的圖書借閱率與學習成績的掛科率呈反相關[7]。因此,圖書館的使用對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特別是自學能力、創新能力發揮著重要作用,要了解、評價本科學習,需對課堂學習和圖書館的使用情況進行分析。
為此,中國現場統計研究會教育統計與管理專業會自2010年發起并組織了關于“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問卷調查”的多中心研究,第一階段涉及2所985高校、3所211高校、2所普通高校;第二階段涉及湖北省6所不同高校;第三階段涉及高職學校。彭美云通過前期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圖書館的頻率不足40%,并進一步影響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等方面的評價[8]。
針對前期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基于“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問卷調查”的多中心調研結果,應用多種數理統計方法。例如,屬性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累積Logsitic回歸分析,對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進行分析,以期評價影響教學質量的可能因素,以便后續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自覺使用圖書館的意識,使其充分利用資源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二、數據和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問卷調查” 結果。本次調研旨在對影響高校教學質量的大學生課堂學習狀態進行全面客觀的調查分析。調查問卷由各高校相關專家反復商討、全程共同參與設計,得出問卷初稿;隨后專家組經過數次預試驗,以評價問卷的有效性及科學性,針對其中暴露的問題進行反復修改并最終形成現有問卷。問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對該部分與態度、意見相關的項目進行信度分析,α系數達到0. 718,內部一致性較高;第二部分包含被調查者圖書館使用情況、成績水平、學習目標、出勤、課堂聽課情況、作業完成情況、師生交流、學風建設等與教學質量相關的多方面信息,同樣進行信度分析后α系數達到0. 736,也較為可靠。通過使用該問卷,可全面了解高校教學、學生課堂學習、圖書館使用等相關的各方面情況,獲得大量、翔實的研究資料,并保證研究結果的全面性、準確性和針對性。
雖然目前眾多學者認為圖書館應強調工作、評價的標準化,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評價本科教學和學習,對于圖書館的功能主要是突出其“第二課堂”的作用,不涉及規模、資源等方面的評價,同時研究的起點也是基于前期研究發現的現象。因此,研究選擇圖書館使用頻率作為因變量。
前期調查共分為3階段。鑒于第一階段調查共涉及培養目標、類型、層次、生源及地域不同的7所高校,包含2所985層次高校(分別簡稱985A校及985B校)、3所211層次高校(分別簡稱211A校、211B校及211C校)、2所普通高校(分別簡稱普通A校、普遍B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學校選擇多著眼于某特定省份或特定類型高校,故本研究采用代表性較好的第一階段調查數據。
對于7所高校的抽樣調查,本研究采用多階段隨機整群抽樣,即在各學院中隨機抽取1個系,然后在各年級中隨機抽取1個班級作為調查對象。此外,在問卷填寫、回收、錄入、數據庫建立的全過程中,均設有執行、監督、核對環節,以降低系統誤差。
本階段研究最終回收可供分析的有效問卷為9022份,有效問卷率達74%。由于采用多階段整群抽樣且樣本量較大,基于這些樣本的統計推斷,能較好地達到本研究的目的。
(二)統計方法
為深入了解學生圖書館使用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影響程度,有必要選擇合適的數理統計方法對其進行定量研究。鑒于所采用的問卷對學生課堂學習狀態的諸多方面進行調查,需對圖書館使用頻率的相關變量進行初步篩選,因此本研究對數據首先進行屬性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為進一步篩選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影響因素,并對其影響程度進行量化,本研究對初篩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最后,以估計出的回歸模型為基礎,對不同特征學生的圖書館使用頻率進行預測。
三、影響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因素分析
為了解學生課堂學習狀態的基本現狀,對本次多中心調查的結果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不同高校學生各方面的表現兼具大學生群體共性及各高校學生的個性。該結論提示,在對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進行影響因素分析時,有必要進行分層分析,即先將所有高校學生作為整體進行分析,接著對各個高校學生分別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再比較和總結。
本研究將問卷中反映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第2部分第32題(“你會經常去圖書館看書、查參考資料或上網查詢嗎?A會;B偶爾去;C從未去過”),記為“N2-32”(下同),并作為因變量。
(一)影響所有高校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因素分析
根據變量是否有序,可選擇恰當的統計量(γ或者τ)來描述兩個變量間的相關程度,并據此進行影響因素的初步篩選。如果γ或者τ的絕對值較大,則這兩個變量的相關程度較高。該自變量可能是影響程度較高的自變量之一,可納入回歸方程中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表1列出圖書館使用頻率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系數(限于篇幅,僅列出γ絕對值大于等于0. 4的變量及τ最大的2個變量)。
結果顯示:將所有高校學生作為分析對象時,“開學時是否會制定學習計劃”與圖書館使用頻率相關程度最高,有制定學習計劃習慣的學生去圖書館看書、查資料的頻率更高。“學習能力強”“覺得學習有意思”“勤奮”的學生使用圖書館也更頻繁。此外,“目前所學專業與個人需求符合程度不同”的學生,圖書館使用情況存在著差異;“面對課堂提問持有不同態度”的學生圖書館使用情況也存在著差異。
如前所述,由于因變量圖書館使用頻率的狀態大于2,需要利用累積Logsi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但需要先進行自變量的初步篩選。篩選時,將γ大于0. 2、小于-0. 1的自變量(有序變量)及τ最大的3個自變量(無序變量)作為備選的自變量。回歸分析時的變量選擇方法為逐步回歸法,以期得到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回歸分析發現:當綜合考慮眾多因素對于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影響時,共有14個變量同時產生影響。這些變量按以下順序依次進入模型:N2-30(制定學習計劃) 、N2-20(覺得學習有意思)、N2-31(學習能力)、N2-37(每天平均花在學習上的課余時間)、N2-10(對多媒體教學資源庫的使用情況)、N2-29(1)(是否常常課前預習)、N2-3(勤奮程度)、N2-35(專業是否符合個人需求)、N2-2(上大學的目標)、N2-43(對大學的課堂授課方式適應程度)、N2-19(是否和同學課后討論)、N2-12(聽不懂向老師請教)、N2-17(聽課時的感覺是否輕松)、N2-9(對多媒體教學方式的適應程度)。回歸結果進一步驗證“制定學習計劃”對于圖書館使用頻率具有最重要的影響;“學習能力”“是否覺得學習有意思”“勤奮刻苦程度”“專業是否符合個人需求”等,同樣具有重要影響;而綜合考慮多個因素時,“對課堂提問的態度”不再具有重要意義,該因素產生的影響被其他因素涵蓋或者替代。進一步總結后發現,這些影響因素大致包括7個方面:學習習慣[N2-30、N2-29(1)]、學習興趣(N2-20、N2-35)、學習目標(N2-2)、學習能力(N2-31)、學習投入(N2-3、N2-37)、課程適應情況(N2-43、N2-17)、多媒體教學(N2-9、N2-10)及學習交流(N2-12、N2-19)。
回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提示,頻繁使用圖書館的學生往往具備如下特征:具有良好的學習習慣,能夠在開學時制定學習計劃并且做到課前預習;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將大學學習的目標定位為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學習能力較強,學習努力,能夠適應大學的課堂授課及多媒體教學方式,聽課輕松并能使用多媒體資源;樂于和老師同學交流。
為量化使用頻率的變化,可假設2名學生分別具有不同的特征,根據回歸分析得出的模型結果(見下式)可以估算出這2名學生使用圖書館頻率的百分比(詳見表2)。
學生1:學習過程中頻繁使用現有的各類多媒體教學資源庫;在課堂上遇到聽不懂的問題會經常向老師請教;聽課時感覺良好;經常與同學在課余時間討論、交流學習情況;上大學學習的目標是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覺得學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經常課前預習;學習十分勤奮刻苦;會在開學時制定學習計劃;自己的學習能力很強;認為目前所學專業基本符合個人需求;每天平均花在學習上的課余時間為4小時以上;對大學的課堂授課方式基本適應;非常適應多媒體教學方式。
學生2:學習過程中基本不用現有的各類多媒體教學資源庫;在課堂上遇到聽不懂的問題從不向老師請教;聽課時感覺有點吃力;從不與同學在課余時間討論、交流學習情況;上大學學習的目標是為拿文憑;對學習沒有感覺;從不課前預習;學習不用心也未下功夫;從未在開學時制定學習計劃;自己的學習能力很差;不知道目前所學專業是否符合個人需求;每天平均花在學習上的課余時間為1小時以內;對大學的課堂授課方式還不太適應;不太適應多媒體教學方式。
表2的結果顯示:2名不同特征的學生去圖書館的頻率差距明顯。第1名學生經常去圖書館的可能性達到87%以上,而第2名學生偶爾去或者從未去過的可能性高達98%。
上文中自變量的初步篩選首先剔除相關程度較低的無關變量,但備選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可能使得某些變量的影響被放大,而某些可能存在影響的自變量被已進入模型的自變量替代,未能進入模型。為此,可將首先進入方程的自變量剔除后,再次進行回歸分析。重復多次時,每次首先進入方程的自變量都是當前備選自變量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將N2-30去掉后,以下自變量在各次回歸中率先進入模型:N2-20 、N2-3 、N2-31、 N2-37 、N2-29(1)、N2-46、N2-10、N2-19。除N2-46外,其他自變量均在第1次回歸分析中已被納入。同樣對N2-46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發現N2-46與N2-3相關系數達到0. 5532,與N2-37、N2-31的相關系數達到0. 4以上,較高程度的相關性可能是N2-46在初次回歸時未能納入方程的原因。
(二)影響各個高校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因素分析及比較
為進一步揭示出各個高校間的差異和個性,在對高校整體進行分析后,對各個高校分別進行分析,分析方法與前類似。
如表3至表5所示,7所高校各自的回歸分析結果以學校層次分類,其中表3為985高校,表4為211高校,表5為一般高校,表中“序號”(i)表示該變量在第i次回歸中率先進入模型,因此該序號與變量影響的重要程度有關。如表中所示,影響各高校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因素相對分散,沒有任何一個共同因素影響所有7所高校。其中,N2-30(制定學習計劃)、N2-31(學習能力)是影響6所高校的公共因素。“制定學習計劃”在985B校、211B校、211C校、普通A校4所高校中是最為重要的單一影響因素;而“學習能力”是普通B校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是985A校重要程度第二位的影響因素;N2-3(勤奮程度)、N2-29(1)(是否常常課前預習)是影響5所高校的公共因素。“勤奮程度”是影響985A校學生最重要的因素;對于985B校、211C校而言,其影響的相對重要程度排序為第3;而對于211B校、普通A校而言,其相對重要程度僅為第6、第7。N2-12(聽不懂向老師請教)、N2-20(覺得學習有意思)、N2-37(每天平均花在學習上的課余時間)是影響4所高校的公共因素。“聽不懂向老師請教”對4所高校影響的相對重要程度均在第6或者第7,而“覺得學習有意思”“學習時間”對于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影響更為重要,“覺得學習有意思”的排序為第2或者第4,“學習時間”的排序為第2、第3或者第5。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學習習慣、投入程度、學習能力、學習興趣、與老師交流討論是影響7所高校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公共因素,但各方面因素的相對重要程度在各高校間有所區別。
而就兩所985高校而言,N2-3(勤奮程度)、N2-46(對自己學習狀態的綜合評價)、N2-12(聽不懂向老師請教)是其公共因素,但這些公共因素對于985A校學生的影響相對重要。就三所211高校而言,N2-30(制定學習計劃)、N2-31(學習能力)是僅有的2個公共因素,這些公共因素對于211C校產生的影響最為重要,其次為211B校,對211A校產生影響的相對重要程度僅為第4、第7。而對兩所一般高校而言,影響因素較為一致,表現為共有5個公共因素:N2-30(制定學習計劃)、N2-20(覺得學習有意思)、N2-31(學習能力)、N2-29(1)(是否常常課前預習)和N2-12(聽不懂向老師請教)。這些公共因素在兩校的相對重要程度,雖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排在前7,且在2所高校的相對排序相差不超過2。
總結各校的公共因素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結論,但一些非公共因素的存在提示各校存在著固有的差異,同樣不容忽視。對各校影響因素的總結歸類發現:211A校、211B校、985A校、985B校4所高校都有一些其他高校所沒有的影響因素,其中211A校特有的影響因素最多,共有4項。例如,“政治面貌”是影響211A校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的最重要因素,而“政治面貌”的這種重要影響和211A校的生源特點有關。211A校生源中有大量的華僑、華人及外籍學生,因此,存在多種政治面貌,而其他高校大致為黨員及團員兩種,華僑等“其他政治面貌”的學生圖書館使用頻率可能存在不同特點。此外,“考試成績不好時的態度”對于211A校學生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對985A校學生進行回歸分析時,第1次建立的回歸模型中也納入“考試成績不好時的態度”,但隨后的多次回歸中,該因素沒有作為相對而言最重要的因素率先進入模型;而在211A校的分析中,該變量的相對排序也僅為第8。可以認為,對于985A校和211A校而言,“考試成績不好時的態度”會對圖書館使用頻率產生影響,但就單個因素而言,其相對重要程度排序在第8或者更后。除了“政治面貌”及“考試成績不好時的態度”外,“聽課時的感覺是否輕松”“花多長的時間去準備期末考試”也是211A校特有的影響因素。結合211A校其他的一些影響因素可知,對于211A校學生來說,學習任務的完成情況,對于學生去圖書館的頻率影響較大。對于211B校學生而言,“專業是否符合個人需求”“對課堂提問的態度”是其特有的影響因素;對于985B校學生而言,“學習成績”是其特有的影響因素;而對于985A校學生而言,“是否常常課后復習”是其特有的影響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985A校分析過程中,N1-14(在校每月開支)在第1次回歸時曾納入模型,即綜合考慮所有因素時,“每月的在校開支”也是影響其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因素之一。但這種影響不是單調的,并不是開支越大或開支越小,去圖書館越頻繁。每月開支400-800元的學生,頻繁去圖書館的可能性較大,而每月開支400元以下或800元以上的學生頻繁去圖書館的可能性較小。每月開支過多的學生往往課余生活比較豐富,不能專注學習;開支過低者,生活條件艱苦,則課余時間往往需通過勤工儉學來補貼,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占據去圖書館的時間。對于前者,相關部門應及時提醒學生合理分配時間;而對于那些生活確實存在困難的學生,學校應充分發揮其在貧困生資助體系中的主導作用,幫助學生從各種渠道獲得資助,減輕生活壓力,順利完成學業。
四、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在對7所高校學生的圖書館使用頻率進行整體分析及分別分析后,相關結果顯示圖書館使用頻率的影響因素相對分散。總體來看,學習習慣、學習投入、學習興趣、學習目標、學習能力、學習交流、多媒體教學及課程適應情況等方面的因素會影響學生使用圖書館的頻率。
具備良好學習習慣(善于制定學習計劃,進行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勤奮刻苦,認為專業符合自己需求且覺得學習有意思,學習目標明確,學習能力較強,學習過程中習慣進行交流,適應大學授課方式,且善于使用各種多媒體資源。具備以上特征的學生,使用圖書館的頻率更高。其中,制定學習計劃和學習能力的影響最為普遍。
但具體到不同學校,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都會發生變化,共性中體現出個性。除上述較普遍因素外,某些高校具有一些特有的影響因素,如政治面貌、每月開支等。
(二)啟示
針對上述結論,需要學校對相關影響因素進行針對性地引導、干預,提高圖書館使用頻率,但最終目的還是提高教學質量、增進學習效果、緊扣創新、全面提高。同時給我們一些啟示:
1.轉換角色。當今正處于信息爆炸時代的大背景下,圖書館不能僅限于傳統的學習場所及傳統/經典資料的提供者,更要順應時代的發展,成為學生接觸先進理念、創新思維的橋梁及途徑,為學生提供最新的資源、文獻;結合當今學科的交叉特點,為學生創新提供靈感;讓學生做到有所學、有所思、有所得,釋放學生的天性,鼓勵學生走進課堂,更要走出課堂,進入圖書館學會自主學習,學會主動獲取信息、全面提高自主學習能力、鍛煉創新思維、全面增強自身素質。
2.轉換思路。圖書館轉換角色,首先需要學校管理者轉換思路。在緊抓課堂教學的同時,發展圖書館。但凡一流的高校必有與之相對應的一流圖書館。課堂教學和圖書館是本科教育的兩個互補且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發展圖書館、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是進一步促進課堂學習、教學相長的重要舉措。
3.加大投入。發展圖書館不能只停留在口頭,需要學校加大投入。首先加強傳統建設,優化圖書館環境,定期更新、充實圖書館館藏資源,剔除陳舊、落后資源,充實、增加經典資源,緊跟學科發展充實新資源;其次,根據時代特點、學校定位以及學科特點,擴充數據庫資源、增加多媒體學習場所、擴大多媒體適用范圍、完善多媒體資源,推廣新興教學方式,吸引和鼓勵學生利用網絡及多媒體資源自主學習和提高,寓教于樂、因材施教,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吸引更多的學生愿意走入圖書館;最后,引進科學化管理流程,對圖書管理、流通等傳統運行模式及環節加以優化,對多媒體、數據庫等新興模式更要規范化管理,專人維護,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科學管理圖書館,提高圖書館運轉效率。
4.因勢利導。針對已發現的特點,如學習習慣、學習投入、學習興趣、學習目標等一些內化的因素,會促使學生自覺提高圖書館的使用頻率,學校應加強管理,善于引導,因勢利導,從學生入學初始,就提醒并幫助學生樹立明確的學習目標,明確本科階段與中學階段學習特點的區別,養成既符合本科學習特點又適合自身情況的學習習慣,讓學生了解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及如何提高自主學習能力,把素質教育及創新教育的理念貫徹始終,使學生具備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的內在需求和熱情。對于那些不適應高校學習、多媒體教學,學習習慣不佳的學生,則應予更多的關注和輔導,加強其信息素質的培養。
5.主動求變。關注不同學校、學科特點,尊重不同類型的學生,全面了解大學生信息渠道多樣的特點,注重傾聽大學生的需求。一方面加強圖書館的利用教育,另一方面根據時代發展特點、學生的不同訴求,主動求變,不斷深化圖書館的服務內容、拓展圖書館的服務形式,以便更好地順應時代,更好地服務學生、服務教學。
參考文獻:
[1]G LANE. Assessing the undergraduatesus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1966,27(4):277-282.
[2]JE HISCOCK. Does library usage affect academic performance?[J].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d,1986,17(4):207-214.
[3]RR POWELL. Impact assess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 consideration of issu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1992,14(3):245-257.
[4]蓋世田,霍燦如. 高校圖書館應該加強對學生讀書的調查研究——從我校七七屆畢業生四年讀書分析談起[J]. 黑龍江圖書館,1982(S2):176-177.
[5]鄒聲威,俞培果. 高校圖書館為教學服務效果的研究[J]. 圖書館建設,1996(5):44-45.
[6]吳英梅,何璨. 高校圖書館對學生學業科研影響的實證研究——以北京師范大學為例[J]. 圖書情報工作,2014(20):73-77.
[7] 喬慧君,周筠珺. 高校圖書館借閱率與學生學習狀態關系研究[J]. 大學圖書館學報,2015(1):55-60.
[8]彭美云. 大學本科課堂教學中的幾個共性問題——基于13所高校問卷調查的統計與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2):162-166.
[9]LA GOODMAN,WH Kruskal.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for Cross Classificatio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54,49(268):732-764.
[10]ALAN AGRESTI.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M]. New York:John Wiley&Sons,1990:32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