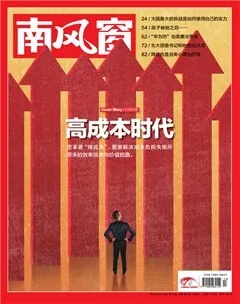敵人,競爭對手還是朋友
李哲夫
假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不是反法西斯力量一方,而是希特勒德國和惡貫滿盈的日本,他們還會給被武力占領的國家以主權地位嗎?起碼這是很可懷疑的。
人類社會已經有幾百萬年的歷史了,不能不謂之久遠。然而人類世界的秩序卻仍然未能走出“叢林”狀態,按照趙汀陽先生的說法,是“有世界而無天下”,因而,還不能擺脫亂世。由此,令人聯想到亞歷山大·溫特所提出的國際無政府結構下的三種文化形態及其所表征的三種國家間的互動方式。
溫特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就這個“有世界而無天下”即無政府結構的世界,從文化層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這樣三個截然不同而又相互遞進的文化類型,“屬于哪種結構取決于什么樣的角色—敵人,競爭對手,還是朋友—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以下所有引用溫特的引文均出自《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
敵人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則為霍布斯結構,競爭對手占主導地位則是洛克結構,而朋友占主導地位就是康德結構。這里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是角色結構,由于角色結構不同,國家間的互動方式也不同:“敵人的姿態是相互威脅,他們在相互使用暴力方面沒有任何限制;對手的姿態是相互競爭,他們可以使用暴力實現自我利益,但是不會相互殺戮;朋友的姿態是相互結盟,他們之間不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并協力抗擊對他們的安全構成的威脅。”
最早出現的無政府結構是霍布斯結構,這是典型的“叢林”狀態,它的行為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政治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自我,消滅敵人,生存完全依賴于自我的軍事權力,安全是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這一結構中,安全困境十分嚴峻,政治行為體隨時都處于生死存亡的緊張狀態。因而,兵連禍接是其顯著特征,行為體將常年處于戰爭和準備戰爭狀態。據統計,世界在公元前1000年時有60萬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及到近代只剩下了幾百個。我國春秋初年也有大小諸侯國幾百個,到了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個強國了。
第二個出現的無政府結構是洛克結構。溫特認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建立以來,“霍布斯自然狀態中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邏輯已經被洛克無政府社會的生存和允許生存邏輯所替代。”這是由于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兩者最重要的區別是對于主權的態度,霍布斯狀態不承認國家主權,而洛克文化的基底在國家主權,而且這種主權還被國際法予以確立,因此競爭的基礎是法治,雖然還是一種弱法治。在這一結構之下,戰爭既被接受也受到制約,戰爭雖然仍會奪取大量人員的生命,但卻不奪取國家的生命。所以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主權國家有的盡管十分弱小,也鮮有遭到滅亡的。
第三個出現的無政府結構是康德結構。溫特認為,這是一個在西方新興起的政治文化,它的基礎是友誼的角色結構,在這一角色結構中,國家之間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的方式解決爭端;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的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洛克文化要防止的是國家的毀滅,而康德文化甚至連國家間的相互進攻都不允許。發展這種結構,有可能使國際社會逾越無政府狀態,走向一個“后無政府體系”的世界。
溫特的三種無政府結構說,把社會學引入了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把文化作為形成一種國際結構和改變一種國際結構的深層動因,它突破了現實主義歷史循環論的發展觀,也能說明一些歷史和現實的國際關系現象。但似也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不足。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起來之后,20世紀上半葉就接連爆發了兩次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認為洛克式的競爭體系是此時世界的主體結構,是不是有些勉強?如果用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理論來解釋后發資本主義強國和原有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為爭奪霸權,爭奪資源、市場和投資地而進行的不可調和的斗爭,是不是更為合適?還可以進一步設想,假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不是反法西斯力量一方,而是希特勒德國和惡貫滿盈的日本,他們還會給被武力占領的國家以主權地位嗎?起碼這是很可懷疑的。
如果仍用溫特的三結構說來加以解釋,那么應該認為,在同一歷史階段,很可能是三種結構或者至少是前兩種結構并存,只不過有一種居于主導地位罷了,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地位應該還會發生轉化。否則就難以理解會發生如此喪心病狂、造成幾千萬人死傷的殘酷戰爭了。
“莫道下嶺便無難,賺得路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過一山攔。”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秉持這種觀念前行要比太過樂觀會更堅定,更扎實,更不會意志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