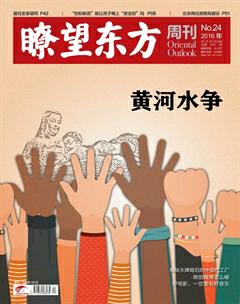走出電視臺
劉佳璇

隨著制播分離的演進,制作主體多元化,引領內容領域持續繁榮的,將不只是大型衛視平臺、跨產業的大公司,而是專攻細分領域的中小型公司
“離開體制創業累嗎?當然累。”
電視制作人易驊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手里的咖啡已經喝了大半。這是她當天上午的第二個媒體訪問,她說:“留在電視臺工作,我之后20年的生活都會很舒服,但那是個被劇透的結局。”
到2014年,易驊已經在電視臺工作了21年。這一年,易驊自深圳衛視離職,創辦日月星光傳媒,徹底告別體制內生活。
易驊先是作為湖南衛視大型活動中心副主任,擔任過《快樂大本營》《超級女聲》和湖南衛視各種大型晚會制作團隊的負責人;后來空降深圳衛視擔任節目總監,又打造出《年代秀》等節目。
易驊的出走不是個案。2013至今,在制播分離等一系列改革舉措的推動下,包括東方衛視原副總監蘇曉、湖南衛視原制作人謝滌葵等在內的體制內精英,紛紛走向市場,創辦自己的內容制作公司。
同樣從湖南電視臺離職的正楊映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始人楊力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出走后的電視人要經歷創業適應期里的“九死一生”:“第一步是要面臨市場考驗和自我調整,那很殘酷,走過不去就沉寂了。”
“制播分離的情況下,行業內人選擇辭職創業,大家覺得遍地都是機會。”易驊對本刊記者說,“但最后你會發現,做好內容才是唯一的機會。”
改革中的個人命運,也是觀察改革效果的窗口。
瓶頸與選擇
易驊時常想起自己住在長沙金鷹小區的日子。作為宿舍區,那是湖南廣電系統精英人才的聚居地。
然而,在湖南衛視奠定了江湖地位之后,金鷹小區舒服安穩的日子令她有些不安。她說,自己不知道如何尋找下一個目標。
電視精英的跳槽和逃離體制,往往是為尋找事業的突破口和更大的創作空間。否則,作為內容生產者,有人擔心自己的競爭力下降,最終被市場淘汰。
“做大型節目時,臺下領導為你把關,最好的資源協助你,在大平臺的依托下,你不知道自己能力是真還是假。”易驊回憶。
易驊對于自己的第一次驗證,仍是在體制內。2014年,應深圳廣電集團時任總裁王茂亮的邀請,她前往深圳。那之后,她的下屬們也紛紛前往,一起重新打拼一個天地。
2016年2月從浙江衛視離職的制片人岑俊義,選擇了獨自創業。作為《奔跑吧!兄弟》原總導演,在他創業之初就得到了資本方億元規模的戰略投資。
楊力對《瞭望東方周刊》坦言,很多走出電視臺的制作人,是“裸奔”出走,背后沒有資本方、手上也沒有項目,他們或面臨升職與薪資的天花板,或在業務上有更大野心,于是選擇了離開。
1999年到2003年,中國的電視行業曾迎來第一次制播分離浪潮。彼時通過電視劇制播分離的初步實現,出現了最早的民營電視劇制作公司。
2009年后,以中央電視臺、上海電視臺、湖南電視臺等為代表,傳統電視臺開始新一輪制播分離試驗。這為制作公司的興起敞開了大門。
由此,全行業人員流動開始頻繁。聚焦至個體,每個電視人的離職都有各自原因。但從大背景來看,這與制播分離密切相關。
所謂“制播分離”,誕生于英國,原意是指電視播出機構將部分節目委托給獨立制片人或獨立制片公司來制作。
內容制作與播出渠道,是電視臺的兩大傳統業務。將內容制作剝離而出,其目的是在觀眾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用競爭來鼓勵精品內容的產出。
同時,行業市場化趨勢下,傳統體制對人才吸引力減弱。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10年,職位也不會發生改變,要求高、薪資低和發揮空間小,使體制內的電視精英開始重新審視職業的未來。
說到底,制播分離,給內容生產者提供了新的空間。
“人才流動已經在業界成為常態,只有流動才有活力。”浙江衛視總監王俊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手藝與效益
曾就職于多家電視臺,米未傳媒創始人兼CEO馬東馬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能做的,就是按牌理出牌,把輸贏交給命運。”
創業電視人手中的底牌,就是在廣電系統中工作多年所磨練的內容制作的手藝。
岑俊義此前就對媒體表示,自己幾乎擔當過節目制作的所有崗位,這為創業帶來的好處就是他對內容的把握更扎實。
楊力概括電視臺工作經驗為團隊帶來的優勢:“第一,你對所有的工種都有涉獵。第二,團隊對整個流程非常清楚。第三,對收視率和觀眾的心理架構較為了解。”
不過,體制外市場上的牌理,他們要重新學習。市場化背景之下,面臨著機遇、風險與誘惑,如何完成身份轉換與心態調整,對每個出走的電視人來說都是挑戰。
以往在電視臺工作時,大平臺的資源與資金成為內容制作者背后的加持。背靠大樹,他們可以專心鉆研創作。“單做節目的人其實很笨,不懂經營,也不懂商業,腦袋里只有做節目。”楊力對本刊記者說。
楊力帶領團隊第一次擔當節目承制方時,她和甲方討論得“一塌糊涂”。楊力糾結著節目質量,但甲方目的非常明確——成本必須控制。
易驊坦言,自己常為內容不計成本,她和純粹的生意人在目標和專長上都不一樣:“我對好內容的敏感度足夠,跟客戶的溝通足夠,經常會做出生意人不會做的選擇和判斷。我的規則是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把內容做最好,而不是利潤最大化。”
較快適應新身份的電視人很可能面對資本的追逐。楊力表示,這種誘惑會影響出走后電視人的心態,導致迷失方向,她將那種狀態概括為“飄”:“適應是第一關,保持初心是第二關。”
有些創業者為了快速沖擊業績,將手中的一些項目委托給外包制作團隊,甚至徹底解散了自己的內容制作隊伍,只關心商業經營。
2015年,制作過《沖上云霄》的正楊映像已經開始在市場上確立自己的位置。資本方找到楊力,為公司估值,并表達了投資意愿。
“(制作公司)很容易跟著資本方思路走,但他們不會管你創作,這本身無可厚非,資本方都會要求利益最大化。”楊力對本刊記者說,“內容制作者不能忘了自己是手藝人,手上的活兒生了,你就不值錢了。我們一開始都會迷惑,吃過一點虧就會明白自己真正的價值何在,回到本質去。”
試錯的勇氣
2016年4月,易驊團隊制作的戶外競技明星真人秀《非凡搭檔》在江蘇衛視開播。她一直在歐洲錄制現場和發燙的機房之間奔波。
對電視制作人來說,收視率就是最基本的考核,爆款節目都有高收視。在易驊看來,節目成為爆款,內容質量占40%因素,天時地利人和占60%。競爭時段、競爭對手和社會熱點都會影響那60%,內容制作團隊的任務就是將內容做到極致,為那60%創造更多條件。
當初,易驊在深圳衛視做的第一檔節目并未取得很好效果,領導說“下一次再來”。“在創業公司不一樣,有時候就會覺得沒有下一次。”
激烈競爭中,為了向投資方和平臺提交一張合格的收視成績單,內容制作公司難免失去了試錯的勇氣,而請明星、做娛樂效果往往能為收視保底——這也是同質化的明星真人秀泛濫的原因。
楊力對本刊記者說:“這就如同出了一款好看的衣服,馬上就有模仿的同款,拼命地減價格,本來值200元的衣服,同款一出值99元,肯定是越來越難做。”
雖然如今國內真人秀如火如荼,但無論是《奔跑吧!兄弟》還是易驊此前制作的《極速前進》,都是引進國外現有電視節目版權的模式,并向外方支付版權費用。易驊認為,觀眾終究會倦怠,內容制作公司必須有做原創內容的勇氣。
在戛納電視節上,國內的內容制作公司和衛視平臺往往都會進行引進版權的選擇。像易驊日月星光傳媒這樣的新公司,通常并不具備爭奪版權的優勢,因為版權方會希望提前知曉播出平臺,否則,制作公司就要提供更高的價格。
這也逼迫易驊們在原創內容上做出更多努力。
易驊希望未來的環境和創作者都能夠容忍一定的失敗率,“抱著試著玩一下的狀態,思想解放開來,或許會更容易出好的內容”。
跨界整合的考驗
據業內人士透露,目前活躍的電視內容制作公司中,90%以上都是從體制內出來的精英創業而成,或由從電視臺離職的高管擔任CEO。
例如,湖南衛視節目中心原副主任楊暉辭職后創立唯眾傳媒,東方衛視原總監田明加盟了星空華文傳媒,江蘇衛視原副總監龔立波創建了大道行知文化傳媒。
這些電視精英往往會從大平臺資源整合和管理經驗中汲取養分。蘇曉離開東方衛視和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SMG)后,成立了檸萌影業,也帶出在SMG有過高管經歷的周元擔任公司執行副總裁。
周元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擁有大平臺管理經驗可以讓團隊更有格局意識,包括對行業縱深的理解和資源整合能力,優秀內容都是在優秀管理與整合的基礎上誕生的。”
隨著制播分離的演進,制作主體多元化,引領內容領域持續繁榮的,將不只是大型衛視平臺、跨產業的大公司,而是專攻細分領域的中小型公司。
大型集團與中小型公司之間會構成彼此競爭合作的關系,這樣的生態鏈中,依靠資源整合能力,國內外不同領域的團隊進行聯合作戰將是常態。
背后的原因在于,無論是對制作方還是贊助商,依靠內容進行廣告推廣的商業模式,都顯得過于單一。
對制作公司來說,整合資源打造內容衍生子產品,營造更多元的盈利渠道是更好的選擇。2015年《沖上云霄》播出后,節目贊助商推出了節目同款的一日飛行體驗項目。楊力透露說,這款旅游產品的線下收益甚至超過了線上收益。
在播出渠道上,多元化也已成趨勢。高互動的網絡視頻平臺與直播秀場興起,互聯網成為制作公司新的進軍方向。
易驊表示,高互動是網絡直播吸引制作公司的創新點,不過她也認為:“在傳統媒體里做太久,有時會有一些固定思維和套路,會陷入經驗主義的危險。”

《極速前進》引進了國外現有電視節目版權模式,并向外方支付版權費用
楊力認為,“一日三千里”的行業變化,要求內容生產者除了考慮節目的內容、環節和主題之外,也要迅速了解網絡視頻制作流程、適應新技術的嫁接方式。同時,互聯網元素與熱點也要融入進來。
更根本的問題是,電視節目注重大眾文化的輸出,網絡則是多元文化的秀場。內容生產者要從電視思維中轉變過來,找準受眾群體,對觀眾需求進行精確的洞察、快速的反應。
周元對本刊記者說,無論觀眾是在手機屏幕前,還是電視屏幕前,最終都在要求高質內容。“這是一個草原賽馬的狀態,各種團隊和資金在逐鹿。同時,也會是一個制作業心態再平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