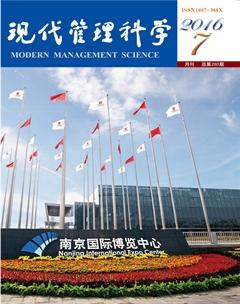我國產品責任制度法律問題研究
王道發
摘要:《侵權責任法》對我國多年產品責任制度的發展成果,做了繼承性的系統吸收。與《產品質量法》存在交叉關系,一起構筑了我國完整的產品責任法律制度。但是,作為《民法典》重要組成部分的侵權責任法,對產品責任制度的規定,還有許多需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例如,沒有細化精神損害賠償在產品責任中的適用規則,對懲罰性賠償規定也是一筆帶過,模糊的規定會引起適用的混亂。而且,對損害范圍界定的爭議會引起整個產品責任體系的混亂,這需要加深對產品責任制度的研究。因此,對現有產品責任制度的立法規定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產品責任;損害;精神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
一、 產品責任的一般概述
《侵權責任法》系統規定了產品責任制度,并以“產品責任”作為專章名稱。從廣義上來看,產品責任不僅包括民法上的侵權責任,而且也包括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但是,民法上的產品責任主要就是指產品上的侵權責任,而侵權責任法范圍內的產品責任只能是指產品缺陷引起的侵權責任。因此狹義的產品責任就是指,因流通中的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應當承擔的侵權責任。產品責任形式主要是以損害賠償為主,也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險等。
1. 產品缺陷。《侵權責任法》對產品缺陷沒有做出詳細的解釋,而筆者認為產品缺陷的概念和內容應當依據《產品質量法》上的規定做出判斷。1993年的《產品質量法》是產品責任領域的基本法律。雖然更早之前的《民法通則》也涉及到產品責任,但是由于過于原則性,在適用上不具有操作的實用性。產品責任在《產品質量法》中才得到了全面的體現。盡管已經頒布了《侵權責任法》,也不能由此認為《侵權責任法》可以完全替代《產品質量法》。即使是未來的《民法典》,也不會承擔這樣的功能。理由就是:(1)產品責任制度本身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特征,不僅僅包括責任方面的內容,還包括其他規范內容;(2)產品領域安全的實現,不僅僅依賴于侵權責任法的救濟,也需要其他法律部門的保障;(3)產品自身快速更新必然會引起產品責任制度的更新和發展,而這些在立法上是不可能及時全面做出反應的,立法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且,《侵權責任法》第5條的規定,科學地說明了《侵權責任法》不能代替《產品質量法》。
缺陷應當是指產品存在的危及他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這是缺陷最本質的內容,至于不符合標準而認定缺陷的,則是屬于表面的基本判斷,是一種推定。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相反事實,這樣的標準可以被推翻。
2. 損害。關于產品責任中的損害,學界存在很大的爭議。有學者認為,損害應當包括缺陷產品本身,其理由就是有利于保護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減少訴訟成本等。還有學者認為,不應當包括缺陷產品本身。其理由是將缺陷產品本身的損失納入到產品責任的損害中會破壞債法內部體系的和諧。在實踐中,完全可以分別依據《侵權責任法》和《合同法》提起訴訟,全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產品責任的損害不應當包括缺陷產品本身。缺陷產品雖然屬于用戶的財產權,產品受損本身就是財產權益的損失。但是,其不應當納入《侵權責任法》中的產品侵權責任的調整范圍。理由有二:(1)侵權責任法的定位是填補損害的救濟法,但是其救濟的損害必須是由于侵權行為或者侵權事實引起的損害,而缺陷產品本身是引起產品侵權責任的損害后果的一個原因事實,不應當經作為原因事實的財產本身作為《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否則有違侵權責任構成基礎的邏輯關系。(2)《侵權責任法》與《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如果將缺陷產品本身納入到侵權責任法的調整范圍,不但破壞債法體系和諧,而且給侵權責任法和合同法本身帶來沖擊。
二、 產品責任的法律構造
《侵權責任法》第41條和43條確立了我國產品責任是無過錯責任。只要產品缺陷致使他人損害的就要承擔侵權責任,不需要考慮產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也不能通過證明自己主觀沒有過錯而不承擔侵權責任。在產品責任的法律構造上,可以分為外部責任承擔和內部責任分擔。通過產品責任產生的基礎和內部分擔的合理構造,平衡了救濟被侵權人合法權益和保障行為人行為自由的利益關系。
1. 產品責任是一種無過錯責任。產品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也直接關系到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但是產品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由于自身存在缺陷也會容易給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帶來侵害。在實際生活中,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很少會以產品為中介,故意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但是,產品本身在制造、設計和流通中,基于生產技術水平的限制,難免會存在缺陷,從而對人們生活的一種不合理危險。為了更好地保護保護產品用戶或者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減少他們的風險,平衡雙方主體的利益關系。在立法上規定產品責任是一種無過錯責任(嚴格責任)是科學的。當損害發生時,用戶只要證明損害是由于產品的缺陷引起的,就你可以直接向產品的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銷售者請求賠償,甚至無需證明產品自身是否存在缺陷的事實。
2. 產品責任的外部分擔。當產品缺陷致使的損害發生時,被侵權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或銷售者請求承擔侵權責任,但不能向其他主體請求承擔侵權責任。在責任主體上,產品責任的外部主體只能是被侵權人和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之間。《侵權責任法》第42條規定,當銷售者不能指明生產者或供貨者的,銷售者仍要承擔侵權責任。質言之,當被侵權人在損害后果發生后無法找到生產者,而銷售者又無法指明時,銷售者還是責任的直接承擔者。
侵權責任法中的供貨者是不同于銷售者的主體,他既不是生產者,而不是銷售者。與實際產品用戶沒有直接產品買賣合同關系,也不是產品制造者和設計者,在產品的流通中是一個中間環節。如果是由供貨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而造成他人損害的,被侵權人也只能向產品的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請求賠償。這里的供貨者可以作為“第三人”進行解釋,不影響產品責任的外部關系。
3. 產品責任的內部分擔。當被侵權人的請求得到滿足后,在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第三人之間可能會就會引起最終的責任分擔問題。無過錯責任是責任產生基礎上不考慮主體是否存在過錯,并不意味相關主體實際上不存在過錯。產品消費者或者第三人會由于自身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這里的過錯是對產品缺陷的產生和存在主觀上有故意或者過失。這決定了他們對損害后果的發生也是存在過錯。在最終責任的分擔上,會依據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過錯的大小,分別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產品缺陷如果是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如果缺陷是由銷售者造成的,生產者賠償后同樣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同樣適用于產品生產者或銷售者向有過錯的第三人追償的情形。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按份責任,以各自過錯確定責任大小,超出應擔份額的,有權就超出部分向其他內部責任主體追償。
三、 產品責任之懲罰性賠償
《侵權責任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而且只在產品責任專章予以規定,沒有在侵權責任法做全面的一般性規定。較之于美國產品責任制度堅持的則是懲罰性賠償原則,賠償金額并不以受害者的損失為限。我國侵權責任法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采取謹慎的立法態度。理由有二:(1)在合同法已經建立相關懲罰性賠償性制度的情形下,侵權責任法作為保護民事主體固有利益的民事單行法不可能排除之;(2)侵權責任法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補損害,因此對于其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是由嚴格限制的。目前存在爭議比較大的,還是賠償數額的計算標準上。侵權責任法對此沒有作出明確規定,相關的司法解釋也沒有出臺。產品責任中的懲罰性賠償計算標準應當由立法機關以立法形式作出規定。
1. 應以人身損害造成的損失的2倍為上限。一個侵權行為引起的損害可以是純粹的財產損失,也可以是人身損害以及精神損害。但是,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是針對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情形,因此只能以人身損害作為計算的基礎。這里的"健康嚴重損害"是指身體健康權,不包括精神健康權,只能做限縮性的解釋。因為精神利益或者健康受到損害一般由精神損害賠償承擔救濟功能,以達到相應的撫慰功能,也具有相當的懲戒作用。《侵權責任法》的懲罰性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產品責任中的人身損害賠償包括由于人身損害而發生的直接財產損失。例如醫療救治費用、喪葬費等。如果發生死亡,還會發生被撫養人撫養費的喪失以及相應的死亡賠償金。如果健康權受到損害引起殘疾,也會引起被撫養人撫養費的喪失損失以及相應的殘疾賠償金計算。因此,這里的損失可以統稱為人身損害引起的損失,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應當以這些損失為基礎,不超過人身損害引起的損失的2倍。
2. 具體計算應當綜合酌情考量。懲罰性賠償除了有一個明確的計算標準計算出具體數額作為賠償上限外,還需要綜合考量侵權人的主觀惡性、被侵權人的損害程度等因素計算出最后的數額。這些考量因素可以由司法解釋規定,因為這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每個具體案件的性質和情況都是不一樣。如果具體規定應考量的因素,不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正確發揮。有學者認為,應當考慮侵權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等主觀狀態。筆者認為,這不應當是考量因素,因為《侵權責任法》已經在適用條件上限定為“明知”的惡意是產品責任懲罰性賠償的前提。
有學者主張,引起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數額是具體確定懲罰性賠償金額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而筆者認為,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數額不應當作為確定具體賠償金額的考慮因素。質言之,這些不應當影響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計算。因為這是完全依據不同法律部門引起的性質不同的“罰金”。一個最終歸被侵權人,一個歸國家所有,不應當混淆。
四、 產品責任之精神損害賠償
《侵權責任法》第22條專門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之前都是見之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在產品責任中,精神損害賠償也有很大的適用空間。立法已經明確只有損害人身權益時,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不包括損害相關財產權益,即使其涉及到相應精神利益,也不包括在內。而且,只有達到嚴重精神損害是,才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不是一般的精神損害。
1. 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產品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包括被侵權人以及死者的近親屬。當被侵權人由于產品缺陷遭受人身損害,相應也會帶來嚴重的精神痛苦。由于人身損害引起的精神痛苦,有些是即時顯現,有些只有經過一段時間后才能表現出來,但是帶來的精神損害絲毫不輕于立刻顯現的精神痛苦。所以,只要被侵權人證明其遭受的嚴重精神損害是由于產品缺陷最終引起的,就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當人身損害致使被侵權人死亡,被侵權人的近親屬可以獨立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因為被侵權人的死亡讓給其近親屬帶來嚴重精神打擊,因此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里的近親屬僅指父母、子女而不包括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2. 嚴重精神損害的判斷。精神損害不像財產損害那樣可以有量化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法官不能隨意發揮自由裁量權判斷是否達到嚴重程度,否則立法規定此制度的目的就會落空。精神損害嚴重的判斷應當結合兩方面的標準。一個就是要有法醫學明確的鑒定結果,運用醫學技術或者心理學對受害人的精神作出判斷是完全可以行的。另一個必須結合案件事實情節的判斷。最直觀的判斷標準是嚴重的精神損害前提應該是嚴重的人身損害,即人身損害達到嚴重程度,就可以判斷造成嚴重精神損害。
3. 賠償數額的計算。精神損害賠償是損害賠償的一種方式,其主要功能在于填補損害(可以稱為撫慰)。其賠償數額的計算應當由立法做出明確規定。關于精神損害的賠償,應當規定一個統一值予以概括。理由有二:(1)精神損害的填補是撫慰,不可能量化計算。只能由立法者結合具體國情作出統一規定、統一適用。(2)人格利益和精神利益是平等的,只要認定為嚴重的精神損害,構成精神損害賠償,則統一適用賠償數額,不需要再比較嚴重程度輕重再做分級計算。
五、 醫療產品責任與產品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59條規定了醫療產品責任,雖然規定在醫療損害責任專章中,但屬于產品責任的特殊形態。醫療損害責任是一種過錯責任,而醫療產品責任和產品責任一樣都是無過錯責任。醫療產品責任因為與醫療機構或醫生的醫療服務不存在直接聯系,而是與醫療產品有直接的關系。醫療產品是由專業的制造機構和銷售機構進入到醫院,所以醫療機構不承擔過錯責任。但是為了全面而充分地救濟被侵權人。《侵權責任法》也把醫療機構納入到了直接責任主體范圍之內,即被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醫療機構對其損害進行賠償。
1. 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是特殊產品。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是屬于特殊產品,與人們的生命健康有著最直接的聯系,直接作用于人的身體健康,一旦產品存在缺陷會給患者直接的生命健康損害。而且,作為產品在一般情形下,只有與醫生的醫療服務行為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使用。因此,醫療產品與醫療機構有著密切關系,患者不可能直接單獨使用這些產品。在實踐中,由于產品存在缺陷發生醫療損害時,患者往往很難直接尋找到生產者要求賠償,為了便于訴訟和救濟患者,在醫療產品由于缺陷發生損害時,醫療機構往往作為直接的責任主體被主張損害賠償。醫療機構在承擔賠償責任后,再向生產者主張最終的賠償。因為醫療機構與產品的生產者存在一種頻繁交易的穩定關系。因此較之于患者,醫療機構更容易對其主張賠償責任。這就把損害賠償的責任最終轉移到了醫療產品生產者身上。
2. 不合格血液不屬于產品,但是也能產生醫療損害責任。輸入血液在現代醫學救濟過程中是一種極其常見的手段,但是輸入血液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不合格的血液也會給患者帶來直接的身體健康損害。血液本身不是人為制造,而是人們之間互相輸入輸出。所以,它不是一種產品,也不能稱為醫療產品。基于它自身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也會產生類似產品缺陷一樣的危險,因此把它作為一種類似產品責任的形態來規定也是合理的。在不合格血液產生損害時,被侵權人可以血液提供機構或者醫療機構請求賠償。在醫療機構先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血液提供機構追償。
參考文獻:
[1] 張新寶,任鴻雁.我國產品責任制度:守成與創新[J].北方法學,2012,6(3):5-19.
[2] 王利明.論產品責任中的損害概念[J].法學,2011, 26(2):45-54.
[3] 杜江涌.我國產品責任制度的反思與重塑[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4,16(9):58-62.
[4] 肖松.中國產品責任制度述評——以美國知識為參照[J].企業導報,2010,17(9):187-188.
[5] 朱凱.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侵權法中的基礎及其適用[J].中國法學,2003,8(3):84-91.
[6] 周新軍.中美產品責任歸責原則比較研究[J].現代法學,2004,(2):175-180.
[7] 劉哲.缺陷產品召回制度與產品責任制度關系探究[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33-36.
[8] 楊立新.論產品代言連帶責任及法律適用規則——以《食品安全法》第55條為中心[J].政治與法律,2009,(10):72-80.
[9] 王利明.關于完善我國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若干問題[J].法學家,2008,(2):69-76.
[10] 劉仕龍.中美產品責任歸責原則比較研究[J].法制與經濟(下半月),2007,(12):93-94.
[11] 黃琴英,姚淙.完善我國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思考[J].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104-106.
[12] 潘悅.進一步完善我國缺陷產品召回制度[J].商業時代,2007,(9):22-23.
[13] 鄭毓楓.完善我國缺陷產品召回法律制度研究[J]. 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2):77-78.
[14] 王世好.論我國缺陷產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完善[J].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3):100-102.
[15] 項賢國,陳慧娟.美國缺陷產品召回法律制度及其啟示探究[J].法制與社會,2007,(12):34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