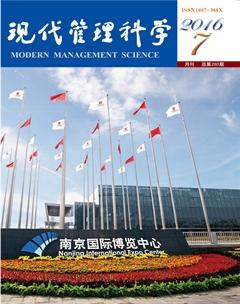產能過剩測量方法比較與綜述
賈潤崧
摘要:文章比較了測量產能過剩的直接法和間接法,直接法將產能產出定義為有效產出或最大產出,前者主要通過成本函數或者利潤函數方法求得,后者主要通過企業調查法、數據包絡分析(DEA)和峰值法求得。間接法通過對現有統計數據構建反映產能利用率的指標體系來考察和判斷產能利用情況,并對產能過剩進行監測預警。
關鍵詞:產能過剩;產能利用率;直接法;間接法
一、 引言
對產能過剩程度的判斷是產能過剩相關問題的研究核心,目前無論是官方統計機構還是學術界對產能過剩的定量核算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統一一致意見。早在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國發〔2006〕11 號),就提出“有關部門要完善統計、監測制度,做好對產能過剩行業運行動態的跟蹤分析,盡快建立產能過剩衡量指標和數據采集系統,并有計劃、分步驟地建立定期向社會披露相關信息的制度,引導市場投資預期”。隨后的政策文件又多次強調要加強對產能過剩的監測與預警,但從現實來看,這些文件的政策意見并未落到實處,迄今我國仍然未建立起權威系統的產能利用率數據發布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每季度公布的“5 000 戶工業企業設備能力利用水平指數”,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個連續整體度量工業產能利用情況的官方指標。盡管如此,人民銀行監測的這5 000戶企業主要由國有大、中型或者規模較大的其它類型企業構成,能否反映全部工業行業的整體情況仍有待證實。近幾年國內學者愈發重視對產能過剩的定量核算研究,采用的方法可分為直接法和間接法,前者選取國際通行的產能利用率指標來衡量產能過剩程度,后者選取一些與產能利用率相關的替代指標來間接反映產能利用情況。本文將通過梳理這兩類研究文獻,對產能過剩測量方法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二、 產能過剩測量方法比較
1. 直接測量法。
(1)企業調查法。對產能利用率的直接測量還可以分為企業調查法和經濟分析法,調查法是在一定時期內選取樣本行業企業,通過對企業生產運營人員發放調查問卷得到企業產能利用情況。國外很早就開始從企業層面對產能及其利用率展開系統跟蹤調查,比較知名的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和美國國防部(DOD)共同資助的企業產能利用率調查(Survey of Plant Capacity Utilization),另外還有OECD組織的商業趨勢調查(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等。在企業調查中,通常由企業管理人員直接報告產能利用率,調查采用的產能概念一般為“可持續的最大產出”(Sustainable Maximum Output)。具體而言,是企業按照實際工作日程,除去機器、工廠由于安裝、保養、修理、待料等正常停工期,在機器設備運轉所需投入充分可得條件下能保持的最大產出(Corrado & Mattey,1997)。由于產能管理是企業運營管理的重要環節,產能規劃能夠為企業長期競爭戰略提供有效支撐,所以可以預計,企業生產管理人員是企業產能及產能利用率的最佳評判人。但是企業調查方法也面臨一些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抽樣錯誤,這是調查數據難以回避的問題。其次,企業調查完全取決于被調查人員對“產能”概念的理解,這種主觀上的理解很可能隨時間和不同企業而不同。例如,在經濟周期上行期,需求高漲,企業管理人員會認為此時的加班加點就是可持續正常生產條件;當經濟陷入衰退,總需求減少,企業開工率普遍下降,此時正常生產條件的標準就會有所不同。這種差別導致企業或產業間產能利用率的比較變得非常不可靠。第三,國內企業常有夸大其產能和產能過剩狀況的激勵,這樣能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政策扶持(鐘春平和潘黎,2014)。第四,調查方法不能排除生產過程中的非效率,所以以最大產出作為產能產出的測量方法會有向下的偏誤。盡管如此,我們相信企業調查得到的結果反映出一線生產管理人員對產能利用的判斷,極具說服力。國外很多學者在測算產能利用率數據時,都會將所得結果與企業調查數據進行對比,作為結果判斷的參考(Berndt & Morrison,1981;Nelson,1989)。
(2)經濟分析法。對產能利用率的經濟分析法源于經濟學家對產能利用率工程學定義的批評。按照工程學的定義,一個年產100萬噸的煉鋼爐,其產能就是一年生產100萬噸鋼鐵,產能利用率就是實際產出與該產能的比值。對產能的這種工程學定義不僅在經濟上意義不大,而且不準確,因為它沒有考慮機器檢修等正常停工造成的產能閑置,還假設產能完全取決于這家鋼爐,其它生產投入和價格因素都被忽視了。這種定義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最大產出,除了戰爭等特殊情況,在現實生產中絕少能實現。需注意,產能利用反映的不僅僅是資本存量的利用情況,它還綜合反映了所有投入要素的利用情況(Klein,1960)。為了將其它要素投入納入產能定義,Klein(1960)研究了生產函數框架下產能的界定,指出產能產出即是短期生產函數上的某個點。也就是說,產能不僅是資本存量的函數,它還取決于其它所有生產要素。Klein(1960)的這一思想后來演變為產能核算領域非常流行的趨勢過峰值法(Trend-through-peaks)(Klein & Summers,1966)。此方法首先根據產出的歷史數據識別出所謂的“峰值”,并假定在峰值處的產能利用率為100%,然后用直線擬合峰值就得到產能產出的趨勢圖。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簡單、易于操作,但它的缺陷也很明顯,比如它假設所有峰值的產能利用強度都一樣,若經濟出現大幅波動,會使結果越來越不準確;而且它還假設產能產出沿著線性的路徑移動,忽視了產能利用的周期性特點。盡管如此,借助生產函數框架定義產能的思想得到后來很多學者的應用與拓展。
為了應用生產函數方法定義產能產出,需要設定經驗生產函數的形式,例如Harris和Taylor(1985)利用Cobb-Douglas和CES生產函數計算了英國四個產業的產能利用率變化情況。隨著近些年數據包絡技術(DEA)和隨機前沿分析技術(SFA)的興起,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非參數生產前沿面分析方法用于生產函數框架下的產能計算。其中影響最大是Fare等(1989)對Johansen(1968)產能定義的形式化處理,為眾多學者所借鑒(James Kirkley et al.,2002;Karagiannis,2013;董敏杰等,2015)。Johansen(1968)給出的產能定義是——假設可變要素的供應不受限制,在現有廠房和設備條件下,企業單位時間內能生產的最大產出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不需要研究者事先設定生產函數形式,而是從實際觀測到的投入產出數據構建出行業的最佳實踐前沿(Best Practice Frontier),再將各企業的實際產出與前沿面產出進行對比得到產能利用率。除此之外,該方法還可以把技術效率從產能利用率中分離出來,得到無偏的產能利用率。
雖然生產函數框架將其它投入要素納入對產能的考察,但是并未將價格因素明確考慮進來,有鑒于此,一些經濟學家嘗試建立更具經濟含義的產能定義。Cassel(1937)最早從成本函數角度研究了企業產能的界定,并將產能定義為企業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AC)的最低點,但是Klein(1960)指出,由于LAC可能并非是常見的U形狀(比如是L型),導致LAC沒有最低點,那樣就無法識別產能產出,所以他建議把產能定義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AC)與短期平均成本曲線(SAC)的切點。Berndt和Morrison(1981)進一步把產能產出定義為SAC曲線的最低點,并指出,如果長期規模報酬不變,這種定義的產能與Klein(1960)所定義的產能是重合的。由于具有清晰的經濟意義,利用成本函數定義產能也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支持和應用(Berndt & Hesse,1986;Nelson,1989;Garofalo & Malhotra,1997;韓國高等,2011)。但是不同學者在實際測算時并未采取統一的成本函數形式,例如,Berndt和Hesse(1986)和Nelson(1989)使用的都是超越對數成本函數,這種函數形式得不到產能產出的閉合解,所以,某種形式的數值解就不可避免;而Garofalo和Malhotra(1997)采用的廣義二次型函數則能求得產能產出的解析解。
成本函數方法根植于廠商選擇理論,它根據對企業的行為假設計算出產能產出。盡管成本函數方法有明確的經濟含義,但應用到中國現實中存在以下幾個待解決的問題。第一,正如前面指出的,成本函數形式選取的任意性會影響到測算結果的穩定性。其次,應用成本函數法測算產能需要大量準確的要素價格信息,而當前中國土地、原材料、能源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一系列要素價格并不能充分反映各類資源的真實價格,再加上各級政府在經濟增長目標驅動下,普遍施行財政補貼、稅收減免、信貸支持等產業政策,這些都會嚴重干擾準確獲取企業投入價格信息,限制了成本函數方法的應用。第三,轉型階段國企多重任務目標的現實使得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假設可能并不完全準確。第四,目前利用成本函數方法測算產能都是從行業層面建立成本函數計量方程,隱含假設同一行業內部的企業具有相同的成本結構,忽略了企業異質性特征。
DEA法與成本函數法實際對應著看待產能產出兩種不同的視角:前者把產能產出視作最大產出,后者把產能產出視作有效產出(Fare et al.,2000)。按照前一種思路,由于資源是稀缺的,對產能的利用越大越好;根據后一種思路,當產能利用提高后,企業其它投入成本也會隨之提高,因為要安排更多的工人輪班,對機器進行更多的維護等等,如此就限制了產能利用的進一步擴大。由于產能利用率屬于短期經濟變量,所以由這兩類方法得到的結果并不完全一致,通常也不具有可比性。由成本函數法得到的產能利用率以數值1為分界線,小于1即表明存在某種程度的產能過剩,大于1則表示產能超負荷利用;由DEA法得到的產能利用率不會大于1,需根據某個正常的產能利用率標準來判斷是否存在產能過剩,一般而言,這一標準會因行業技術特征、區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差異而不同。
2. 間接測量法。除了上述直接測量方法,很多國內學者選取與產能利用率密切相關的替代指標,通過建立刻畫產能過剩的指標體系來對產能過剩進行判斷。韓國高和王立國(2012)以鋼鐵業為例,從固定資產投資、產需與庫存、行業效益、勞動和生產成本5個方面選擇了11個指標來構建產能過剩的監測預警系統,并用熵值法確定每個指標在預警系統中的權重,最后得到綜合的產能利用率情況。江源(2006)利用報告期內某行業主要產品實物產量與相應的生產能力之比來衡量行業產能利用率,并分析對比了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和汽車五個行業1995年~2005年的產能利用率。但是以實物計算的產能利用率僅能反映某一細分行業或者較為粗略地代表全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無法得出全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例如對于鋼鐵行業,僅能以粗鋼產能利用率來反映其產能利用率。周勁和付保宗(2011)從經濟效應、社會效應和環境效應3方面選取7個指標(工業品出廠價格、成本費用利潤率、資金利稅率、企業虧損面、閑置資產、失業人數、銀行呆壞賬、三廢排放)構建了產能過剩的評價體系。劉曄、葛維琦(2010)建立了一個由5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組成的產能利用率評價體系,并用它對煤炭產業的產能利用進行了評估。黃永和等(2007)研究了汽車產能利用率的衡量指標,他們用庫存、價格、利潤率(利潤總額/產品銷售收入)、應收賬款比重(應收賬款/產品銷售收入)、虧損總額、虧損面(虧損企業數/企業總數)和產銷率來綜合反映汽車產能利用情況。
除了建立指標體系,部分學者還發展了一些測算產能利用率的非常規方法,比如Shaikh和Moudud(2004)假設產能產出與資本存量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然后建立資本存量與產能的協整方程,根據資本存量數據來推算產能產出。程俊杰(2015)利用該協整測算了我國30個省市2001-2012年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協整方法對資本存量數據的準確測度要求很高,眾所周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次,這種方法側重宏觀產能分析,難以獲得關于微觀企業產能利用率分布特征的啟示。Dergiades和Tsoulfidis(2007)通過建立投資、利潤和信貸的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方程來估算產能利用率,他們的方法同樣是從宏觀角度分析產能利用,缺乏行業和企業層面的分析。
三、 結論與建議
國外發達國家很早就開始了對產能過剩的定量測算工作,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為我們提供指導和幫助。本文通過梳理對比產能過剩不同測量方法,發現不同方法對產能的定義有明顯差異,其中最大產出和有效產出是兩種最常用的定義。除此之外,不同學者還發展出建立指標體系、協整、VAR等方法來對產能利用率進行測算。鑒于產能過剩問題的復雜性,單一評價方法可能難以對產能過剩情況進行準確度量,只有通過多角度,多方法的比較,才有可能形成對產能過剩的準確判斷。除此之外,國家統計部門應著力提高企業產能利用率數據的調查能力,并能定期及時地向外界公布這些信息,減少企業的盲目投資,也利于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產能利用率的影響因素、變化趨勢和行業分布情況。
參考文獻:
[1] Carol Corrado and Joe Mattey,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151-167.
[2] 鐘春平,潘黎.“產能過剩”的誤區——產能利用率及產能過剩的進展、爭議及現實判斷[J].經濟學動態,2014, (3):35-47.
[3] Ernst R.Berndt and Catherine J. Morrison, Capacity Utilization Measures: Underlying Economic Theory an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48-52.
[4] Randy A.Nels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9,(37):273-286.
[5] L.R.Klein,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apacity, Econometrica,1960,(28):272-286.
[6] Lawrence R. Klein and Robert Summers, The Wharton Index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Economics Research Unit),1996.
[7] Richard Harris and Jim Taylor, The Measurement of Capacity Utilization,Applied Economics, 1985,17(5):849-866.
[8] Rolf Fare, Shawna Grosskopf and Edward C. Kokkelenberg, Measuring Plant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9,30(3):655-666.
[9] James Kirkley, Catherine J. Morrison Paul, Dale Squires,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Common-pool Resource Industrie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2,22(1-2):71-97.
[10] Roxani Karagiannis, A System-of-Equations Two-Stage DEA Approach for Explain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2013,227(1):25-43.
[11] 董敏杰,梁泳梅,張其仔.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行業比較、地區差距及影響因素[J].經濟研究,2015,(1):84-98.
[12] 韓國高,高鐵梅,王立國,齊鷹飛,王曉姝.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測度、波動及成因研究[J].經濟研究,2011,(12):18-31.
[13] 韓國高,王立國.我國鋼鐵業產能利用與安全監測:2000-2010年[J].改革,2012,(8):31-41.
[14] 江源.鋼鐵等行業產能利用評價[J].統計研究,2006,(12):13-19.
[15] 周勁,付保宗.產能過剩的內涵、評價體系及在我國工業領域的表現特征[J].經濟學動態,2011,(10): 58-64.
[16] 劉曄,葛維琦.產能過剩評估指標體系及預警制度研究[J].經濟問題,2010,(11):38-40.
[17] 黃永和,劉斌,吳松泉,胡衛國.我國應制訂汽車產能利用衡量標準[J].汽車工業研究,2007,(11):2-8.
[18] 程俊杰.轉型時期中國產能過剩測度及成因的地區差異[J].經濟學家,2015,(3):7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