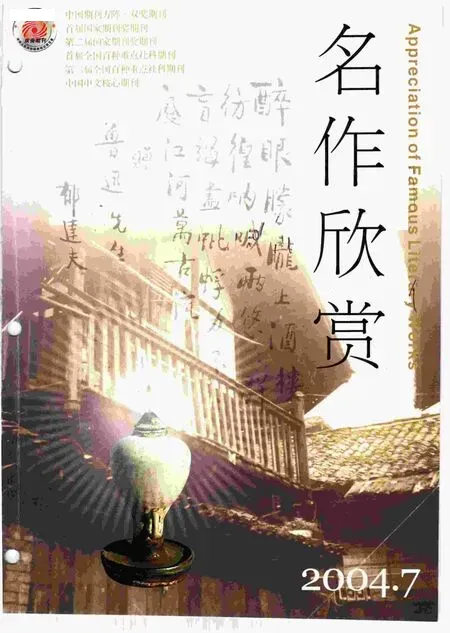經典·時文·魯迅——關于高中語文選文方向的一點思考
山西 李學文
?
經典·時文·魯迅——關于高中語文選文方向的一點思考
山西李學文
摘 要:傳統經典組成了人類的精神史,對于高中語文課本,我們不是要“去經典”,而是要更力求讀懂經典,并著力于剔除課文中 的“非經典”。而對于魯迅作品,我們也不是要“去魯迅”,而是要著力讀懂魯迅,吸收魯迅作品中的“正能量”。
關鍵詞:高中語文 經典 魯迅
關于經典選文
現行高中語文教材沒有機械刻板地按照文體進行選擇,也沒有一味地迎合浮躁社會的閱讀習慣,選擇那些所謂受“歡迎”的作品,而是根據語文“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結合,選擇那些典范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章,還關注到了文章結構的典范性、思想內容的積極性等方面,我認為這種選文的理念是正確的。“任何一種母語的語文教材都是以自己母語中的經典作品和一定比例的其他語種的經典翻譯作品構成,因為傳統經典代表了我們無法逾越的歷史和必須接受的傳統。經典是經過幾代人的淘洗篩選得來的,面對傳統經典的閱讀,其閱讀與鑒賞的對象不管從時間、空間,抑或是從文化、心理、審美上與我們都相距甚遠,但我們依然必須了解它,因為它是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歷史。傳統經典組成了人類的精神史,它是我們認識自身無法繞過的文化遺產。”(汪政:《語文教材的經典性與當代性》)這也是語文教材歷來重視經典的重要原因。但為什么經典選文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認為還是要從教師自身找原因。
比如經典散文《荷塘月色》一直是語文教材的常客。但是我多次參加各類教學賽講的評課,當選到此文時,很許的教師不去認真研究編者選文的意圖,不去思考作者寫作的意圖,不去理解課改語文教學中對這些經典作品的教學要求,更不去顧及文本的特點、語言的特點,也不去研究所選單元選文的共同點和差異性,而是照本宣科,按照解讀寫景狀物類散文的機械步驟,使得學生對《荷塘月色》創造的幽暗、優美、靜謐的氛圍和意境的理解,大打折扣,學生聽得昏昏欲睡,教師自然也就講得寡淡無味了。如果能夠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把《荷塘月色》和《故都的秋》進行比較,情形就會大為不同。郁達夫對于色彩的欣賞,和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表現出來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同樣是在北方的文化大都市,朱自清對于色彩的欣賞顯然要重于鮮艷——雖然《荷塘月色》中表現的還是“淡淡的”;而郁達夫恰恰相反,他是排斥鮮艷的。牽牛花的藍色白色最佳,紫黑次之,淡紅色最下;落寞的“破屋”“衰草”等,追求的是一種淡雅;因為淡雅,“其中蘊含著一種趣味,一種超越日常世俗的,日常的趣味”(錢理群語)。由此不難看出朱自清是帶著才子文人那樸素的雅趣來欣賞這殘敗之美的。這樣在兩文的內在有序性上下工夫,引導學生如何欣賞生命的衰敗,如何超越世俗的實用的價值觀念去感悟藝術表現的正價值也就得到了解答。
再就《荷塘月色》中思考:當我們讀完《荷塘月色》這篇文章,我們閉上眼睛就很容易想象出荷塘的美景,那么作者為什么要花這么多筆墨寫荷塘的景色呢?難道僅僅是為了躲避煩惱么?教者引導學生把時代背景的材料進行收集、整理、加工就不難發現:這個荷塘其實是作者內心向往的另一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彌漫著寧靜、典雅、生機、情趣和自由,讓人們內心深刻感到平和與安寧,更重要的是在這個世界里,作者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當思維完全由個人情緒支配時,個體的自由便達到了最大的空間,這是作者最想得到而最難得到的東西。所以,作者花這么多筆墨來向我們展示這個荷塘,其實是為了向我們展示他的內心世界。他在這種氣氛中感受到了快樂和喜悅,我們則在他的歡樂中進行了心靈上的溝通。
再比如,我們可以帶領學生從《故都的秋》中感受郁達夫式的悲秋與中國文人傳統悲秋情緒的聯系與區別。中國的文人從宋玉開始就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到杜甫的《秋興》“聽猿實下三聲淚”,到馬致遠《天凈沙》“斷腸人在天涯”等,都是把秋當作一種人生悲苦來抒寫的,使人沉浸在悲秋之中,在讀者看來,使人以愁為美,卻并不是痛苦的。
其實,這個審美過程貫穿于文本解讀的始終,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每個過程中都有所體現,只是其側重點不同罷了。教師在與學生、與教材、與生活“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教師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必須在對文本進行充分的挖掘、涵泳基礎上,努力探究文本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脈絡,去體會文本的人文精神、作者的審美追求。語文教師的任務就在于此。“越是偉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傾向,往往越是隱蔽,有時就潛藏在似乎平淡并不見得精彩的字句中。一般讀者常常視而不見,解讀的功夫就在這些地方,所謂細微處見精神”(孫紹振語)。
試想一想,這樣的學習,學生一定是處在一種亢奮的開放性學習之中,他們帶著問題去收集資料,帶著問題去學習,該有多大的收獲啊。即使是教師的講也是一種升華,教師也會與學生一道在文本的學習中升華。
這樣的經典,就賦予了時代學習的特征,經典所包含的信息、所傳達的經驗具有普適性了。所以,對經典的閱讀、對經典的選擇,既是對作品自身信息的接受,更是在了解和熟悉人類經典的標準,學習和驗證這些標準的過程,也是語文教材不能繞過的話題。
當然我們不否認今天的《讀者》《意林》等雜志,有許多文章可讀性極強,但是,從文體看,選入語文教材是否合適?是否可以帶給學生學習一種典范的“例子”?就頗值得推敲了。我們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去遷就學生的閱讀心理。我曾在我所教的學生中做過一個閱讀調查,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學生熱衷于閱讀網絡小說,因為網絡小說簡單,容易懂,不需要思考,閱讀的途經也方便快捷。但是,這些作品對學生的聽說讀寫語文能力的提升,對學生的審美提高,對學生的閱讀鑒賞能力的提高,對學生人格塑造的作用,確實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令人為之擔憂。
再如,高中語文必修五第四單元的選文,《中國建筑的特征》《作為生物的社會》《宇宙的未來》從文體的角度來看屬于自然科學小論文,這里所說的“小論文”是科學普及意義上的文章,但這些文章出自自然科學大師之手,觀點信實,論證嚴謹,文筆生動,兼有情趣和理趣,也體現了科普作家敏銳的思維和獨特的語言風格,可讀性也很強。這樣的選文,雖屬“經典”,同樣是緊貼時代特征的選文。知識經濟的時代,有知識的勞動者將取代傳統的產業工人,未來社會的掃盲,不是文字的掃盲,而是文化的掃盲,是科學掃盲。一個人沒有良好的科學文化素養,就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動者。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在1989年就推出了一個“2061計劃”,即《為全體美國人的科學:達到科學、數學和技術脫盲的2061報告書》,其目的也在于強化對公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教育。從現階段語文學習方面而言,要加強學習內容的文化內涵,在閱讀和寫作上有質的飛越,而閱讀、學習這類文章,可以增長知識,開闊視野,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推理能力和思辨能力。教學中也需要教師先認真閱讀這類文章,這時字詞的認讀已經退為其次,而內容的因素就需要加強。這種語文能力形成的開放性,決定了語文學習具有“百川歸海”的特點。試想,如果語文學習不重視對科學文化的吸納,我們可能讀不懂每天報紙上涉及的大量科學內容,也看不懂電視上很多宣傳科學文化的專題片(如《探索發現》《人與自然》及discovery系列),這就大大影響了與他人的溝通。由此可知語文教材中這些文章的選入是多么必要和重要了。但是僅僅憑這幾篇文章的入選,解決這些問題顯然也是不夠的,它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拓展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語文讀寫能力更趨綜合。如果我們的編者把這些文章去掉,換些時尚通俗的“時文”,課本的神圣性和厚重感將會大打折扣。再者,如果教師能在引導學生學習這些文章時適當加入些遷移材料,學生也照樣會喜歡,也照樣會學得津津有味。我曾在教《中國建筑的特征》時,除了對中國建筑的解讀,還選擇梁思成中國建筑的手繪圖呈示給學生,學生在充滿敬意地感嘆的同時,也被建筑學家嚴謹的科學態度所折服,這樣也把枯燥的中國建筑的學習,更加生動地做了闡釋。
關于魯迅作品
高中語文教材所選擇的魯迅作品,只有(必修一《記念劉和珍君》、必修三《祝福》、必修四《拿來主義》三篇。最近幾年,無論是教材編寫者還是語文界,都對魯迅作品一直爭論不休,似乎大有去之而后快的必要。香港《南華早報》曾有報道稱,多年來,學生和教師一直在抱怨年輕人很難理解魯迅的作品,并稱魯迅大約寫在一個世紀以前的那些對中國文化的見解正在與時代脫節。對于“去魯迅化”,新浪網曾做過一個調查,在新浪新聞與微博展開的調查中,絕大多數受訪者都對大幅度去掉魯迅作品這樣的變動感到不滿。他們說,魯迅的作品都是經典作品,代表著中國人民的精神。錢理群教授也說:“對中國一代又一代改革者和知識分子來說,魯迅對國家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文學領域,他的作品鼓勵人們對社會進行反省。即便現在閱讀魯迅的作品,你還能受到強烈的啟發。”對于高中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我認為不是多而是不夠。是我們今天的教師對魯迅及其作品理解不夠,既不愿“神化”,又不愿“妖魔化”,更不愿意對魯迅作品對國民靈魂的啟迪做深入的思考,就采用最簡單的辦法,先否定,然后去之,讓它從中學語文教材中永遠消失,來滿足全社會的娛樂化、快餐化。
其實,我多么希望我們的語文工作者能夠靜下心來,仔細地讀讀魯迅的作品。魯迅的作品文筆犀利,思想深邃,需要我們語文教育者帶著學生去解讀,去創造性地解讀。問題不在于孩子們能不能讀懂,關鍵是我們語文教育者怎樣讓他們都懂,并在讀懂的過程中思辨,體會魯迅語言的個性化特點。《南方日報》的這段話是不是值得我們思考?它說:“讀魯迅,不必從娃娃抓起。問題倒不在孩子們讀不讀魯迅,教科書里還是保留了相當多的魯迅文章,況且,真正愛魯迅的學生,自然會通過各種途徑去認識魯迅。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成人世界對魯迅的回避乃至過濾,某一段時間,避談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潮流。讓中學生去讀魯迅,但成人世界里真正秉承魯迅精神的又有幾個?如果沒有成人社會的示范教育,在教科書里放再多魯迅文章又有多大作用呢?”毫不客氣地說,就社會批判的價值而言,迄今為止,沒有哪個人的作品能超越魯迅作用。所以說,魯迅并沒有過時,也永遠不會過時。讓中學生接觸一點魯迅的批判精神沒什么不好。吶喊“魯迅作品的全面退出,是教材編寫者和語文教育者的怯懦和無品,也寓示著當代社會的思想混亂仍需漫長的沉淀才能成新的價值”。(《新京報·魯迅不可以退出語文教材》)這不禁讓我想起了郁達夫說過的話:“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
比如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語言在魯迅那里,變成了會變形的筆,自如地驅遣著中國漢語:口語、文言、排比、重復、長句、短句、陳述、反復……很難想象,沒有學習過“30天寫好高考作文”的魯迅,能在一篇文章中變化那么多語言技巧。可見只有情感濃烈到逼迫血管的地步,才能有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一氣呵成。而這種汪洋恣肆的語言風格,正是魯迅表里如一的體現,是對當時社會模式、文化模式、思維模式、語言模式的挑戰,是對那個還身在奴隸時代的自己的叛逆,是對那些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底層民眾的同情。
再如《祝福》,從小說的場景安排,到中國傳統浙東風俗畫,再到刻畫人物的精當,無不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把祥林嫂這個中國傳統勞動婦女的形象刻畫得如此生動。她生命悲劇的如此令人動容,使她足可以和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中塑造的任何一個形象媲美。我們看看臨死時的祥林嫂:
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著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頭發過早全白寫出她的遭遇之慘、衰老之快;“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 “間或一輪”,正表示她陷入極度的悲哀,內心的痛苦已無法表露,精神已完全麻木;她眼珠的偶爾轉動,反襯出她精神的衰頹、生命力的枯竭。這樣的描寫,真可謂鬼斧神工,句式的變化自然靈動。在苦難深重的中國勞動婦女形象中,不難找到祥林嫂這樣的婦女,但她身上“有價值”的東西,不只是勤勞、質樸,她也不可能承擔揭露封建社會黑暗和罪惡的任務,魯迅先生在這時已經開始側重考慮如何探路前進的問題了。祥林嫂的死,這一不尋常的死以及死前對舊世界統治的“疑惑”,正是警示和教示一切活著的人,能夠沿著這一“疑惑”繼續“求索”下去。
如果能這樣思考魯迅作品的價值的話,我們就不至于整日糾纏在“他”“她”、“那”“哪”不分,“預備”寫成“豫備”,“支吾”寫成“支梧”這些枝節之中了。
其實對教材的理解和運用各自的看法不同,但是,只有積極去思考、努力去改進才能有助于語文教學的進步,也才能有助于學生語文知識、語文能力的提升。“破舊”不等于全盤否定,“立新”也不等于重新做一個版本的語文教材。如果寄希望于一本萬利,寄希望于一勞永逸,也是不切實際的。語文不同于其他科學,更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版本、選文、體例,在穩定中適當改善。我們也沒有必要迎合現今社會對語文的苛求,做語文人該做的事就足夠了;我們更不需要把語文教材變成一種看起來熱鬧,但是內容淺薄、文體不能具有典范的娛樂性讀本,那豈不是大大的悲哀?或許我們需要做的是用“經典的標準”,謹慎地選擇作品中的優秀者,根據教材使用實際情況,去更換其中不具“經典性”的作品。
作 者: 李學文,山西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學高級語文教師,太原市語文學科帶頭人,太原市第五批教學名師。
編 輯:張勇耀 mzxszyy@126.com
課文新讀 特邀主持:李華平
《背影》是中學語文課本中的經典篇目,因而圍繞這篇課文的解讀也角度各異,因這篇課文的教學解讀所引發的爭議也層出不窮。本期我們刊發三篇對這篇課文的解讀文章。這三篇解讀文章可以說是站在了另外一個維度,為課文更多層次的解讀提供了別樣視角,希望能對中學語文教師的教學有所啟發。也期待本欄目能引起更多關注,激發出更多對經典篇目全新角度的有意義的解讀。——編者
《背影》一文三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