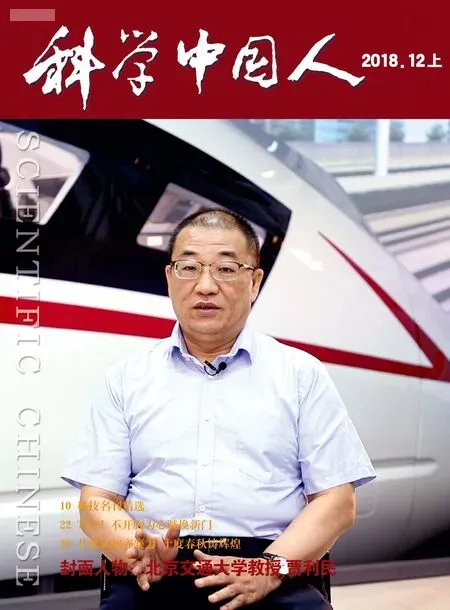尖吻蝮蛇出血毒素的生物信息學研究進展
孫江山,沈林,沈源重慶市醫(yī)藥衛(wèi)生學校;重慶市武隆縣白馬中學校
尖吻蝮蛇出血毒素的生物信息學研究進展
孫江山1,沈林2,沈源1
1重慶市醫(yī)藥衛(wèi)生學校;2重慶市武隆縣白馬中學校
尖吻蝮蛇是我國十大劇毒蛇之一,其毒液主要作用于血液系統(tǒng)引起出血、腫脹與局部組織壞死。當前,生物信息學高速發(fā)展,使全世界的生物學研究數(shù)據(jù)和成果得到共享。本文主要從尖吻蝮蛇蛇毒中的出血毒素的生物信息學上進行分析論述。
尖吻蝮蛇;出血毒素;生物信息學
1.尖吻蝮蛇簡介
蛇類屬脊索動物門,脊索動物亞門,爬行綱,有鱗亞綱,蛇目。目前,世界現(xiàn)存蛇類有二千七百多種,而我國有二百二十余種,其中有毒蛇五十余種,隸屬四科[1]:即海蛇科,眼鏡蛇科,游蛇科,蝰科。蝰科可分為兩個亞科,沒有頰窩的屬蝰亞科,有頰窩的屬蝮亞科。其中蝮亞科可分為兩個屬,即烙鐵頭屬和蝮屬。尖吻蝮蛇又稱五步蛇、祁蛇和百步蛇,屬于蝰科,蝮屬,是一種劇毒蛇,主要產(chǎn)于我國長江流域、華南及越南北部[2]。
2.生物信息學簡介
生物信息學是以存放有大量生物信息的數(shù)據(jù)庫為基礎(chǔ),使用計算和統(tǒng)計的方法,對各種生物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和處理的生命科學研究方法[18]。生物信息并不僅限于基因組信息,生物信息學也并不等同于基因組信息學。我們普遍認為生物信息學是把基因組DNA序列信息分析作為源頭,破譯隱藏在DNA序列中的遺傳語言,找到代表蛋白質(zhì)和DNA基因的編碼區(qū),特別是闡明非編碼區(qū)的實質(zhì),從而認識生物有機體代謝、發(fā)育、分化和進化的規(guī)律;同時在發(fā)現(xiàn)了新基因信息之后進行蛋白質(zhì)空間結(jié)構(gòu)的模擬和預測,然后依據(jù)特定蛋白質(zhì)的功能進行必要的藥物設(shè)計。因此,現(xiàn)代生物信息學主要包括3個重要內(nèi)容,它們分別是基因組信息學、蛋白質(zhì)的結(jié)構(gòu)模擬以及藥物設(shè)計[19]。基因組信息學是指從基因組水平研究遺傳的學科。到目前為止,已經(jīng)測出了上百種生物體的完整基因組序列。如何分析這些從實驗過程中獲得的大量原始數(shù)據(jù),并從中獲得與生物結(jié)構(gòu)、功能相關(guān)的有用信息是當前困擾理論生物學家的一個棘手問題[20]。解決這些問題又可以帶來新技術(shù)的進步,推動生命科學的發(fā)展。
3.尖吻蝮蛇毒出血毒素的研究進展
出血毒素是一類主要存在于蝮亞科、蝰亞科蛇類的毒蛋白,是主要的血循環(huán)毒素,能引起動物的水腫、出血和組織壞死。眼鏡蛇中僅眼鏡王蛇毒含有出血毒素。響尾蛇和蝰蛇毒以能引起較強的局部效應著稱,這種局部效應包括水腫、出血和組織壞死,它們無一不與一種的出血毒素有關(guān),由于局部病理變化快,往往沒有以抗血清治療就發(fā)生,因此難以治療。出血毒素往往使蛇傷病人的肢體壞死,有時不得不截肢,它是蛇傷治療中的一大難題。出血毒素引起出血作用的強弱與不同蛇毒及劑量大小而有關(guān)系,出血作用弱的出血毒素只能引起傷口或注射部位皮內(nèi)或皮下少量出血;較重者則可引起傷口或注射部位附近組織或肌肉大面積出血;嚴重者不但傷口或注射部位出血。而且可引起內(nèi)臟器官(如肝、肺和腸等)廣泛出血。當動物身中響尾蛇和蝰蛇毒時,出血毒素的出血作用是導致動物死亡的主要原因。
1978年,Bjarnason[3]從西部菱斑響尾蛇蛇毒中分離得到了出血毒素a、b、c、d、e,其分子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大約在24000左右;另一類主要為68000左右,出血活性比較強。后來,Xu,等(1981)[4]從皖南尖吻蝮蛇中分離出了三種出血毒素,分別是AaH-I,AaH-II,AaH-III。還有Mori(1984)[6]、Omori-Satoh(1979)[7]、Mandel?baum(1975)[8]、Sugihara(1983)[9]、Kishida(1985)[10]、Sancheez(1987)[11]、Ovida(1978)[12]、Huang(1984)[13]以及Kureeki(1985)[14]也分別提取得到了出血毒素。甚至Nikai(1995)[5]從Crotalus atrox中得到了五種出血毒素a、b、c、d、e和f。龔為民等[15,16]以Adamalysin II晶體為模型,研究了皖南尖吻蝮蛇出血毒素AaHI的初步晶體結(jié)構(gòu),結(jié)果表明,AaH I由201個氨基酸殘基組成。Gong,等[17]還解析了皖南尖吻蝮蛇毒的晶體結(jié)構(gòu)。AaH I是一個只有一個催化結(jié)構(gòu)域的含鋅金屬蛋白酶。
蛇毒中的多種毒素蛋白在闡明病理過程中的作用也越來越被重視。在治療各種各樣的神經(jīng)、肌肉、免疫、血液循環(huán)、腫瘤、代謝機能失調(diào)等疾病方面也提供了新的希望。有人甚至將某些難治之癥的治療寄希望于蛇毒毒素的研究。而我國的蛇類資源豐富,對蛇毒的研究、開發(fā)和利用,并最終造福于人類,這使我們面臨許多新的課題,有待于我們?nèi)ミM一步研究。
[1]覃公平主編.《中國毒蛇學》[M].廣西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1998.
[2]美華等.《五步蛇》[M].科學出版社,1983,155-156.
[3]Bjarnason,J.B.,et a1.,Biochemistry,1978(17),3395-3404.
[4]Xu,X.,et al,Yoxincon,198l(19),633-644.
[5]Nikai,Kato,C.,et a1.,Bio1.Pharm.Bulletin,1995,18(4),631-633.
[6]Mori,N.,et a1.,Toxicon,1984,22,451-461.
[7]Oshima,G,et a1.,J.Biochem.(Tokyo),1968,64,215.
[8]Mandelbaum,F.R.,et al,Toxicon,1975,13,109-110.
[9]Sugihara,H.,Moriura,M.,Nikai,T.,Toxicon,1983,21,247-256.
[10]Kishida,M.,Nikai,T.,Mori,N.,et a1.,Toxicon,1985,23,637-645.
[11]Sanchez,E.F.,Magalhaes,A.,Diniz,C.R.,Toxicon,1987,25.
[12]Ovadia,M.,Toxicon,1987,25,621-630.
[13]Huang,T-F.,Chang,J-H.,Ouyang,C.H.,Toxicon,1984,22,4.
[14]Kurecki,T.,Kress,L.F.,Toxicon,1985,23,657-668.
[15]龔為民,滕脈坤等.科學通報.1996,41(17),1611-1614.
[16]Gong Weimin,Teng Maikun,eta1.,Chin.Sci.Bull.1997,42(2), 333-337.
[17]Gong,W.,Zhu,X.,et a1.,J.Mol.Biol.,1998,283,657-668.
[18]陳潤生.生物信息學[M].生物物理學報,1999,15(1):5.
[19]北京生物技術(shù)和新醫(yī)藥產(chǎn)業(yè)促進中心,世紀之交的新科學:生物信息學[J].生物技術(shù)通報,1999,(8):49
[20]楊福愉.展望21世紀的分子生物學[J].生物物理學報, 1999,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