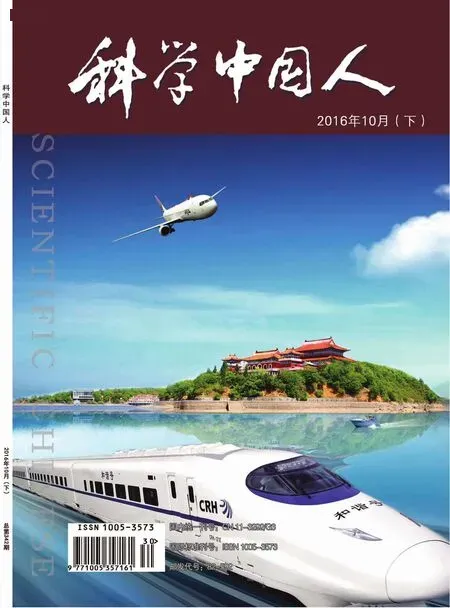學校直接德育課程問題研究及其出路
李成霞
遵義職業技術學院
學校直接德育課程問題研究及其出路
李成霞
遵義職業技術學院
直接學科德育課程是學校專門設置的為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而以學科課程形式呈現在學校課表的課程。在學校整個德育體系中起著主導性作用,是學校德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環節,本文著重探討了直接學科德育課程的傳統困境、形態變革中的問題,從而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和策略,以認清直接學科德育課程的未來發展方向。
直接學科德育課程;傳統困境;問題;出路
本文所說的直接學科德育課程是指以直接的,而不是間接的學科課程。即把課程當成一門學科或者所有學科的總和形式呈現的德育課程,是學校為進行德育而專門設立的,體現在課表上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開設的課程。以區別于那些雖然不是直接為提升學生思想道德素質而設立,但對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形成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課程。現代學校制度建立以來,學科化的直接道德教育課程逐漸形成,但其發展卻并非一帆風順。各種歷史或現實的理論爭論隨之紛紛出現,因而對直接德育課程變革的呼聲在各個歷史階段都表現得強烈,我國正在提倡的“生活德育”的課程改革亦屬于此列。
一、直接德育課程的傳統困境
隨著道德教育理論的不斷涌現和豐富,人們對直接德育課程的看法也開始多樣起來,而“多樣”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對直接德育課程形式的直接或間接的否定或反對。其中以杜威為代表的反對直接德育課程的理論表現最為堅決。杜威認為,真正的道德教育并非關于道德知識的直接課程的教育,“迫切的問題是要在兒童當前的直接經營中尋找一些東西”,而且“學習科目相互聯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學,不是文學,不是歷史,不是地理,而是兒童的社會活動”①從杜威的生活化理念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實踐開始,直接德育課程的發展陷入困境,同時也逐步形成了人們對直接德育課程的一些迫切需要改革的“傳統”弊端的看法與“成見”,如強制灌輸的負面形象,脫離生活的理智開發范式等,這些也是人們認為直接德育課程需要改革的主要理由。
(一)傳統困境一:強制灌輸的負面形象
從形式上看,直接德育課程表現為以價值規范的解釋與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以及被動的接受學習模式等特征,將道德看成可教的知識,一種典型的知性德育。課程以文本化的材料為核心,師生關系表現為直上而下的直接的、強制的管教與服從關系,學生缺乏必要的主體地位。從內容上來看,直接課程的教學與學習內容的價值導向,大多是不需要公開辯難的,被公認為是合理的、合法的價值。
直接德育課程被認為是強制灌輸,20世紀以來就被教育者認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進步主義以及生活哲學復興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對直接德育課程的改造,似乎主要就表現在對強制灌輸的反思方面,而灌輸也似乎成了直接德育課程“揮之不去”的陰影。
(二)傳統困境二:脫離生活的理智開發
當直接德育課程的種種問題出現后,人們對直接課程“生活化”改造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對德育“非生活”特征的變革也就成了許多學者所認為的變革的“突破口”。有研究者認為,“把道德教育過程視為同智育無異的知識接受和智力的啟蒙或開發的過程,這樣,在性質上,道德教育必然淪為知性、缺乏情感推動和深刻體驗的冷冰冰的物理操作過程,是出于實際的生活實踐過程之外的。”②在實踐中,德育課程與學生生活相脫離也成為人們對直接德育課程進行改革的主要理由。
因此,非生活化的直接德育課程表現為極端理性化,缺乏了人性的情感因素、遠離受教育者日常道德生活的知性的教育。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的日新月異不斷更新,這種知性的德育顯然不能對道德的效力產生強烈的作用。這顯然也是其所面臨的一大困境。
二、直接德育課程形態變革的問題
從新課程改革的現實以及相關的一些調查和教學一線的各種反應來看,直接課程形態的變革中也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可以看作“課改專家”或課改實施者對改革理念的部分誤讀、斷章取義的結果。當然,也部分反應了“自上而下”變革模式中的一些先天的問題,以及教育實踐一線的教師和學生對于課程變革客觀現狀的認識。這也是在直接課程變革過程中必須去解決的問題,否則將被困于此而沒有出路。
(一)變革理念的對立化
在當代的變革中,各種對立否定性主張層出不窮∶如簡單地以活動性或生活德育替代學科或知性德育,以素質教育替代應試教育以及泛泛的自我建構等,都屬于這種對立化變革思維或理念的結果。這種做法反而容易導致非理性化、簡單化、不負責任的空洞托詞,更帶來了感性的泛濫,從而使道德價值表現的十分“人性”和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使變革理念變得空洞而不著邊際。同時,這也大大增加了理論進入實踐領域的阻力和難度。
(二)課程內容的反智化
現實生活中朝向生活方向的改革,往往由于對知性德育的“曲解”,導致了完全排斥理性思維的做法,這也是導致師生對改革感到困惑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我們的很多經典理論中的問題沒有被研究者滲透而被摒棄,而造成極端的全盤吸納個別理論或斷章取義的態度,這反而不利于生活或實踐德育的有效開展,同時也會導致直接課程改革中頻繁出現的極端的“反理智”和“去知化”情緒。
(三)教育形式的娛樂化
隨著德育課程改革的推進,在實施中,教育形式的娛樂化表現得尤其嚴重,這表現為過濫的花樣翻新、膚淺的文本形式與活動組織呈現,以及教學氛圍營造得過分“后現代’狂歡化,表達的其實是低品位的審美取向。“在藝術領域,波蘭劇場大師葛洛托夫斯基認為,劇場的出發點不在于類聚各色奇巧,極盡聲色之娛,而要去繁就簡,出去所以溝通上的障礙,促進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與交流······沒有化妝,沒有別出心裁的服飾和布景,沒有隔離的舞臺,沒有燈光和音響的效果,戲劇仍能存在。但沒有演員與觀眾之間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關系,戲劇卻無法存在······③類似的本末倒置的情形也表現在課程改革中。形式的娛樂化并不等于形式的多樣或多元化,所帶來的結果也相差甚遠。
(四)德育實踐的圖示化
從課程理論概念的演化過程和社會學對課題及其實踐的關注出發,至少可以認為,從事實出發的道德知識并非構成道德教育課程的主體,而只能是基本的和基礎性的,更豐富和更可靠的來源來自社會生活的實踐中,如體驗、經驗、活動等。關于這一點,已有學者明確指出過,社會生活的本質是實踐的,道德的本質也是實踐的,道德教育和德育課程的本質更應該是實踐的。過去道德教育脫離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已習慣于過分依賴有章可循的所謂的“實踐圖式”。“實踐圖式”并非實踐本身,而是一種理性的邏輯化。這直接導致了德育在改革中的形式化或程序化,這其實是另一種表現形式的強制灌輸,從而失去了道德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實踐感”,因而德育生活與實踐等方向的變革,是改革傳統和現行直接德育課程,建立真正的現代德育課程的必經之路。④
三、直接課程形態變革問題的解決出路
在正確認識當前直接德育課程變革中的問題的基礎之上,依據問題,擬提出以下一些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和策略:適度協調直接與間接之間的關系,拓展性地理解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對應與關聯,把握好導向與整體間的定位與功能對接等。
(一)直接與間接關系的適度協調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直接課程形態的變革中人們更加感覺到難以把握課程的發展,課程改革背后的理念變得模糊。對直接形態的否定或激進變得將教師和學生推向課程之“后”,否定了外部現實和過分強調主題的意愿及教師和學生的行動,造成了好像跟一般意義上的課程沒有什么關系一樣,而且如果課程僅僅意味著教師和學生在課堂里的實踐,就無法理解歷史現象,更無法持續地和以獨特的方式組織課程,教師和學校個體也很難具有適當的差異性,因為課程作為實踐限制了人們以歷史的眼光看待課程,也關閉了學生獲取道德教育的另一扇窗。
我們知道,無論來自正面的改革理由還是“反面的”(對傳統的變革不太成功的嘗試)改革誤區,似乎都在表明直接德育課程變革與發展的困境和難度。難道對直接課程的形態的變革真的是不可能的嗎?或者說直接德育課程的模式需要徹底顛覆嗎?實際上,現實中這種矛盾和困境曾經在西方也發生過:20世紀前半期,傳統的直接德育課程遭到強烈的批判,間接的全面課程開始居于主導;到了20世紀后半期,間接的課程開始流于形式,缺乏系統的弊端日益顯露,道德教育出現滑坡。直接德育課程的這種反復困境,也正好注解了后來德育在理論和實踐發展趨勢方面逐漸走向“中間、折衷和調和”方向的主要緣由。
(二)理論和實踐關聯的拓展理解
一些道德教育理論工作者們也注意到了這一情況,我們很難說,道德教育中哪個主要理論流派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全面的課程,或者論證出了一套詳細的道德教育的觀念與基本的教學理論,并且還與之配合地編撰出了比較成功的直接道德教育課程。以往的涂爾干沒有建立起一個學習道德教育的課程,只是一些不系統或者凌亂的教師經驗的混合。其中杜威在將課程轉化成具體詳細的教育實踐方面做出了實質性的努力,特別是在實驗學校。然而,就像進步主義教育的歷史所顯示的那樣,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而且杜威的事業‘從來都不是專門地與道德教育相關’。當代各個道德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方面,甚至沒有發展出明確的框架體系或細節上具體明了的專門的直接課程來。但或大或小的影響總是有的,即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課程的外延和內涵,改變了人們對課程的狹隘理解,也為我們樹立起變革與發展的希望。
(三)導向定位與整體功能的對接
直接德育課程主要可以定位為受教育者通過對有關價值、道德傳統與準則的學習,來促進自身道德認知、情感與行為的形成與發展的導向性教育方式或途徑。早在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的論斷確立了道德認知的基本理論之后,又歷經皮亞杰、科爾伯格等的努力探索,直接德育課程形態基本沿襲了以認知發展作為道德發展的基礎依據的內在邏輯。直接德育課程形態在傳授道德或價值知識、準則方面,也的確發揮了應有的歷史功能。在現當代以后,直接德育課程更是處于東西方學校德育的主導地位,其導向性功能顯而易見。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居于主導性地位的導向性功能逐漸受到多樣化的挑戰,且自身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要去解決的問題。
我們需要在綜合理解直接德育課程形態變革的基礎上,形成直接德育課程的導向性定位與整體功能的“對接”。無論在何種條件或背景下,改革的過程始終是一個整體和綜合的進程。同時,由于課程變革總是取決于學生、教師、教材、社會文化氛圍、課程專家的協同作用和共同意志,因而任何一方的單向行動都無法取得理想的改革效果。從當前國內外比較明顯的趨勢來看,直接德育的課程的形態變革,顯然必須走向多樣化的形態,并與其他學科、課程以及課外活動等結合進行,才能獲得整體的、理想的道德教育效果。這種功能對接是對直接德育課程改革全面考慮的綜合體現。惟其如此,未來的變革和發展之路才會越走越好。
直接德育課程的形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有著深刻歷史淵源的“老問題”。先當代以來,東西方教育界的許多研究者基于直接形態的弊病,干脆提出了以間接形態替代直接形態課程的建議。從杜威開始,這種理念自西方席卷整個世界,人們期望所有的教師都來承擔德育的責任,摒棄關于道德理念的教育,走向真正的道德教育,并期待調動學校的方方面面,來進行全方位的潛移默化。但要實現這一美好的愿望,其難度是可想而之。德育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合理性在近代以來不斷受到人們的懷疑,尤其西方德育還經歷了一個否定直接的學科教學和強調道德反思能力培養的階段。但在經歷了一個反復和反思階段以后,人們開始冷靜思考德育的課程問題。最終多數同意的結論是“道德教育所面臨的是尋找一條中間路線。它既不強迫年輕人接受一套道德規則,也不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即作出決定完全是個人的主張”。⑤這一歷史反復的現象再次表明,直接德育課程的存在在理論上是合理的,在實踐上是必要的。
注釋:
①王天一,夏之蓮,朱美玉.外國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213-214
②唐漢衛.生活道德教育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130
③周淑卿.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120.
④魏賢超.德育課程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262.
⑤檀傳寶.學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126
[1]王天一,夏之蓮,朱美玉.外國教育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2]周淑卿.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M]甘肅: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
[3]魏賢超.德育課程論[M]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
[4]檀傳寶.問題與出路——若干德育問題的調查與專題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5]高德勝.生活德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李成霞(1987-),女,貴州省遵義市人,碩士研究生,遵義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