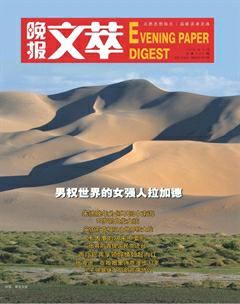《辛丑條約》是如何被廢除的
劉永峰
1940年4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五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在致開幕詞時,蔣介石說:“我可以說今天我們抗戰軍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見充實,一切技術與組織更有進步,敵閥已經上了絕路,已經預備進入墳墓……”通篇的致辭,蔣介石的神態都保持著始終如一的堅毅。然而,誰都明白,現實遠非那么樂觀。
那一年,蔣介石正經歷著一生中最焦慮不安的時刻之一。他被逼入了一種孤立無援的絕境。
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世界上的弱國,單憑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尋求外部的支柱。
戰時外交
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的外交大權迅速地集中到蔣介石的手中。
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蔣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長職務,正式成為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
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規、不問手續,并不拘泥于傳統的職業外交方式。
他曾在日記中批評中國的職業外交官說:“中國外交人才,怯懦無骨氣,無責任心,惟私利是圖,徐謨之膽小如鼠,尤為可鄙。”
因而,在蔣介石處理對外關系時,他更樂于使用非正規的外交途徑,常常倚重一些“外圍人物”。
在對美關系上蔣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齡、宋子文和商震,對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對蘇有孫科和楊杰,對德有李石曾和蔣百里。
如此龐大的非職業外交人員群體,使蔣介石在選擇外交途徑時游刃有余。
且圍繞在蔣介石身邊的外國顧問——如拉鐵摩爾,也使他獲取外交信息的途徑變得更加多元;諸如居里、威爾基等穿梭于重慶、華盛頓之間的外國特使,更使得蔣介石有能力繞過常規外交渠道,從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
廢約交涉
戰時外交,除了在軍事、經濟上爭取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外,另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爭取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
1941年7月,蔣介石在和他的美國政治顧問拉鐵摩爾長談時說:“中國進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戰爭,到頭來卻發覺自己依舊處境孤立……步入抗戰的第五年,卻沒有一個盟國。”
與此同時,日本卻利用這種狀況大肆宣揚說,白人依舊把中國作為一個殖民地加以對待,中國盡管進行了四年的戰爭,卻仍然沒有得到民主國家的平等對待,因此應該另謀出路。
蔣介石說:“如果這一現象不加以制止,將會削弱中國的抗戰力量。”隨即,他向羅斯福總統提出兩個建議:建議之一是,由羅斯福倡議英國和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建議之二是,中國參加英美澳和荷屬東印度召開的太平洋聯防會議。“這兩個建議中的任何一個付諸實施,都將保證中國與其他民主國家處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視中國人的感覺。”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盡管蔣介石做出了積極的外交努力,但英蘇忙于歐戰,無暇顧及遠東,美國也極力避免過早地與日本發生沖突,所以對蔣的建議反應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不宣而戰。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命運的轉機也隨之來臨。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國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國宣戰,宣布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關系者,“一律廢止”。
這樣,中國與日本、意大利及其軸心國同盟的西班牙所簽署《辛丑條約》的相關條款至此廢止,而德國從《辛丑條約》中所獲得一切權益也早在“一戰”后就被中國收回。
條約終結
1942年1月1日,中國、美國、英國、蘇聯等24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家宣言》。從此,中國與英美正式成為反法西斯的盟國關系。
從法理上,這些不平等條約依然將中國在盟國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時宜的東西。
1942年10月,蔣介石在接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維爾基時說:“中國今日尚未能取得國際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國民眾能了解中國,欲其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應先使其本身獲得平等地位始。”
1943年1月11日,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
同天,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駐華大使薛穆也在重慶簽訂《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國與英、美兩國之間的《辛丑條約》正式廢止。
中國與英美交涉的成功,對其他的國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后,中比條約、中荷條約、中法條約均做出同樣規定,廢除《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原簽字國共十一國。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國外,其余如德、奧、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國,因宣戰或改定新約,也已取消。
至此,《辛丑條約》強加于中國的約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強通過《辛丑條約》在中國獲得的權益只剩下使館界一些房屋的產權而已。
(水云間摘自《周末》201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