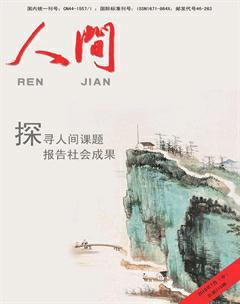圍城的現實主義表現
宋亞男
(天津工業大學,天津 300380)
?
圍城的現實主義表現
宋亞男
(天津工業大學,天津 300380)
摘要:“圍城”就是一個“小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充滿了無窮無盡的欲望,這些欲望又永遠無法得到滿足,這正是人類生存的悖論。本論文意在運用現實主義批判的理論和反諷理論來分析《圍城》中所包含的反諷藝術特色。《圍城》又是錢鐘書用反諷構筑的一座語言之城,他的語言風格是所向披靡中極富喜趣,調皮得引人發笑,在笑中發揮批判諷刺的威懾力。《圍城》可以說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
關鍵詞:圍城;批判現實主義;反諷
一、什么是文學?
文學是什么?什么樣的作品才稱得上是文學作品?這是每一位文藝工作者,甚至一般讀者都比較關注的問題,也是文藝批評和鑒賞的前提。面對這一敏感而又抽象的話題,現實主義批判對其做出了思考和解答。
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它曾經在歐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現實主義批判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比較廣闊、比較真實地展示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現實矛盾的揭示具有相當的深度。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在反映社會時,著力于暴露社會的黑暗,批判現實的罪惡。批判的現實主義揭發了社會的惡習,描寫了個人在家庭傳統、宗教教條和法規壓制下的“生活和冒險”,卻不能夠給人指出一條出路。在中國文學史上,錢鐘書先生的《圍城》恰恰是適合現實主義批評流派研究的典型范例。
然而,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接受與闡釋,今天的《圍城》已經是一個多元化、多角度的《圍城》,已經承載了幾代文學接受者所賦予的各種層次、角度各異的深邃內涵。
作為一代文學大師的錢鐘書先生,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知名的,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錢鐘書并未得到應有的關注。由于新中國成立后,政治題材、歌頌的基調普遍盛行,而《圍城》既沒有反映抗戰也沒有歌頌革命,更沒有塑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顯得非常不和時宜,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關于錢鐘書的研究才開始不斷深入。用錢鐘書自己的話說,《圍城》是他錙銖積累地完成的。脫稿后又屢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對文字的進一步錘煉。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杰出地位。
被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的《圍城》,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空虛、虛偽、灰暗的精神生活。它不像“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學那樣具有鮮明而強烈的為著革命和理想召喚風雷的戰斗色彩和內容;它所描寫的只是“那一部分社會”和“人類”的生活,但人們卻可以借一斑而窺全豹,從知識分子們精神上的“圍城”,看到中國社會這個大“圍城”。
關于小說的名稱,書中有過交代,作者引用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像一個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里面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或者法國也有這么一句古話,不過不是說鳥籠,說是被圍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沖出來……后來,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作者又通過方鴻漸的口照應說:“我還記得那一次講的什么“圍城”,我近來對于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可見,作者是采用一種象征手法,點名了主題,是借用這些言論為他的精神產品命名的,這個“圍城”既象征了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與逃脫,又象征了抗戰時期文人墨客,專家教授的種種精神狀況和心理狀態,這不是家長里短的普通人生問題,而是一個包含著更深的哲學道理的重大社會問題。
人是不能孤立于時代,孤立于環境的,小說在描寫主人公的坎坷命運的同時,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中國現代社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群像圖”。作者在書中所描繪的都是留學生、大學教授、文人墨客,但由于他們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樣的特殊環境中,所以大多數都有著精神空虛,虛偽自私和不學無術的共性。但是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個性。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這其中很多人物的描寫,繪聲繪色,惟妙惟肖,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構成了一部新的《儒林外史》。
二、現實主義代表作
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給人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錢鐘書先生在《圍城》里,還給我們形象地展示了西方文明是如何在中國破產的。方鴻漸、趙辛楣、蘇文紈等都是接受了正統的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他們又何嘗不希望中國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走上西方的道路呢?但是,在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極其深重的中國社會,“外來東西來一件,毀一件”,“外國的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最終連拿著這些東西的人也一齊毀了進去。表明著中國社會亟待革命,但資產階級本身及其思想武器,卻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長期處于支配地位。而這一理論重在把作品和社會聯系在一起,認為解釋和檢驗作品應以生產方式和經濟條件等決定性因素為參照,需將作品放置于經濟基礎乃至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中來考察。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積極意義,不應該只看它描寫的是什么,而是看他怎么寫。應該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實,揭示了生活的某些本質的方面。反諷,源出于希臘文eironeia ,最早主要是被古希臘修辭學家用來表示字面意義與實指意義不符或相反。
《圍城》文本中,其語言的復雜性和意義的多重性最多的是依賴反諷理論的作用。夏志清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圍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也是最偉大的一部。作為諷刺文學,它比《儒林外史》那一類的著名中國古典小更勝一籌。臺灣省的孟令玲先生說:“讀過錢氏小說的人,大多對其辛辣而且近乎刻薄的寫作手法,留下深刻的印象。”這話是一點兒不假。
當然,《圍城》也像所有的藝術作品那樣,并非白璧無瑕,它不可避免地帶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局限。對于作品中的人物,作者幾乎完全加以譴責嘲笑,少數幾個比較正面地人物也不完全可愛。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作者一定要寫先進人物,但至少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抗日浪潮不能不波及到他們,而作品在這方面表現的極少,但當然是由于作者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生活環境和作者當時的思想認識所決定的。但是,瑕不掩瑜,《圍城》的這缺點絲毫都不能影響它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它將以自己獨特的風姿屹立于中國現代文學之林。
參考文獻:
[1]彭小球.論錢鐘書《圍城》的諷刺藝術[J].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
[2]孟憲華.淺析錢鐘書《圍城》的諷刺幽默性[J].文教資料,2009.
[3]蘇涵.《圍城》語言的藝術特色.山西師大學報,2011.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7-0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