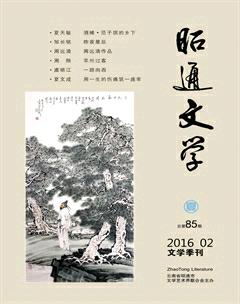我來看看我的胳膊
周遠清
1
那幢醫院36層的住院大樓是今年剛剛落成的,氣勢巍峨,直插云端。從15樓往下看,花園里有青青的草坪、怒放的鮮花。正中間一個涼亭,有石桌、石椅,好幾個人在里面閑聊。花園里到處是人,有病人,有閑雜人,還有一些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偶爾從那里穿梭而過。花園旁邊那條路上,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來看病的問診的住院的,醫生和患者各自忙碌著。章小明打開窗戶往下看時,大腦里突然閃現出一種影像,從十五層往下一跳,一定有一種衣袂飄飄飛揚臨風的快感。
這個念頭一閃現,把自己也嚇了一大跳。
這間病房他并不陌生,他多次來看望過病人。前年,他的一個工友曾從這里飛身而下,一了百了。
那個工友從三層腳手架上摔下來,脊柱骨斷了,左手也斷了。在醫院住了一個月,做了手術,脊柱釘了2根釘子和鋼板,左手上也釘了釘子。醫生說,回家去調養吧,在床上最少要躺1個半月才可以下床,3個月后左手背做2次手術把釘子拿掉,背后脊柱1年以后做2次手術拿釘子和鋼板,以后不能干重活了,可能會有后遺癥。他們都央求老板讓他繼續住在醫院治療,回家去哪有錢再進醫院?老板有些不悅,板著臉說,聽醫生的還是聽你們的?
老板是不是與醫生達成某種默契,不知道。現在是計算機管理,你只要欠費,誰也沒辦法給你從藥房里取出藥來。
那天,等章小明他們再去看望他時,那個工友已經躺在15樓地下的草坪上了。
章小明扶著這個窗子,窗口曾經上演過驚心動魄的一幕,自己莫非也像那個工友,需要縱身一跳嗎?為了討薪,那個工友曾經率眾搞過跳樓秀跳塔秀甚至抹脖子秀,秀是假的,淚和血卻是真的。原來是玩秀,這一會他來真的了。
跳不跳,對章小明現在的境況來說并不重要,不就是眼睛一閉挺身一躍的事情?他真的閉上了眼睛:他看見了家鄉的鳳凰山、灑漁河,還看到妹妹背著書包去上學,看到母親起早貪黑磨豆腐準備挑到集鎮上去賣,買回油米和鹽巴。看到父親大發雷霆,臉上的肌肉因憤怒而變形:二本不是大學?你不讀,要當一輩子老農民?什么?你說你還想再復讀,明年再考?吹你媽的大牛,你就肯定考得起?村長家長生不比你聰明?復讀了三年,一年不如一年,你不知道?再說,老子也沒錢再供你讀了,你就死了那條心吧。什么?你不耐煩讀二本,要去打工,生活的路也不止上大學這一條。好啊,你狗日翅膀毛硬了,老子的話當你放屁,有本事去了就別回來。滾!滾遠點!
滾就滾,誰怕誰?他真的賭一口氣遠遠的滾了。
他恨不得穿越回去,接受父親的建議,重新把自己做過的混賬事情一一更正,把二本讀出來,好歹也是一個大學生。
胸部一陣陣疼痛襲來,肋骨處發出“咯咯”生長的聲音。醫生高超的醫術讓他起死回生,把一個瀕臨絕境的人從死亡邊緣拽了回來,不得不驚嘆現代醫學的神奇。他睜開眼睛,一切似乎已經遠去。五年了,他沒有回過一次家,沒給家里寫過一封信。當年,他憤而出走,發誓混個人模狗樣才回去。可現在……
住院大樓的草坪在太陽的照耀下泛著藍盈盈的光芒,這時他發現那個肝癌病人又在一個女人的攙扶下從病房走出來了,來到那個茵茵的草坪上,仰巴朝天的躺倒,上身衣服全脫了,整個胸腹部裸露著,肚皮像一面灌入空氣的鼓。章小明知道,那是胸腔里充滿積液而形成的腹脹。中午陽光熱烈的時候,肝癌病人就要出來享受最后的燦爛,他至少在這個草坪上躺了三天了。他其實也應該從15樓飛身而下,對他來說,那絕對是一場亙古未有的飛行壯舉。
他想到一件事,昨天,吳校長曾帶著學校幾個領導來看望他并提出,說是經過行政會議研究決定,等他痊愈出院,就聘請他到實驗小學做收發工作,反正工作也不苦,待遇不會低于他打工的建筑隊。當然,他如果同意,還要聘請他做學校少先隊的兼職輔導員。他們還說他曾經考取大學沒有去讀,知識水平應該不會差,給學生們講講他的事跡,談談農民工為這個城市作出的奉獻。
人在受傷的時候,心理最為脆弱,一根稻草可以壓彎人的脊梁骨,一句溫暖的話可以讓人起死回生。他兩行淚從眼里慢慢流出,落到手背上,臉上淚水劃過的地方,像溫水滾過似的潤澤。吳校長的話說得夠好了,都會讓人心潮起伏了。可他居然沒有爽快地答應他們,他說自己已經殘疾,幾次出事都是在學校發生的,“學校”那個字眼太尖利,他怕自己再次受到傷害。也許老天不讓他來蹚學校這趟渾水也未可知。
吳校長說,小章,你想多了,那不過是一種巧合,世界上巧合的事多的是,不可信,千萬不可信。學校是一塊綠洲,我保證,她不會再傷害你,一定會讓你感到溫馨的。你是市上表彰的見義勇為先進人物,我們這樣做是對你的肯定,也是弘揚一種精神。實驗小學的大門隨時向你敞開,你愿意什么時候來就什么時候來,我們真誠歡迎你。
他雖然沒有答應吳校長的邀請,但他心里還是暖暖的,看人家那態度是真誠的,不像是在作秀。
是那個無知的家伙,一把將他拽入痛苦不堪的無底深淵。他眼前仿佛又出現在校門口那棵大榕樹下。榕樹樹干挺粗,有兩人合抱那么粗,年齡肯定比他大了若干倍,可片片葉兒都嫩得像孩子們的臉龐。天委實太熱,空氣里有一種熱辣辣的感覺。大榕樹一直為他舉著那把綠油油的大傘,他來來回回晃悠著。正是在這棵樹下,他被人拖出樹蔭。那時,太陽毒辣辣地高懸在頭頂,白晃晃的,突然間就變黑了,像無數只蝙蝠從四面八方撲過來,在眼前上下飛旋。
2
民工章小明被人打傷半個月后,終于從重癥監護室出來轉到普通病房,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猶如卸下了背上一塊沉甸甸的大石頭。
那塊沉重的石頭至少壓住三個人:
第一個首推實驗小學的馬保安。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一個農民工抓進值班室,先用手銬將其右手銬在椅子背上,繼而用電警棍將其電翻。他的問題是亂抓人,亂用警具,侵犯公民人生自由,已經違法。他是那個農民工再次遭受重擊致傷的始作俑者,如果那個民工因傷致死,他就是一個殺人兇手。他近幾天身子常常發抖,預感到有什么事要發生。
另一個是實驗小學二年級一名學生家長雷高楊。他的女兒半月前被一個賣冰糖葫蘆的人拐走,他急火攻心到處尋找,為人父母者擔心女兒安危無可厚非,但他聽到鄰居的兒子說他們學校保安抓住一個人,與前段時間來學校門前賣冰糖葫蘆的人極為相似,便斷定那人就是拐走女兒的歹徒,不問青紅皂白趕到學校值班室呵斥章小明還回女兒,在沒有得到對方及時應答的情況下,就往死里打人,致使章小明鼻骨和三根肋骨骨折,一根肋骨戳進肺葉形成氣胸,送進重癥監護室。該學生家長無端打人,致人傷殘,違法是肯定了。如果致死,他罪責不輕。
還有一個就是實驗小學的吳校長。吳校長是本地名人,書法家協會主席,不僅一手顏體在當地無人敢望其項背,學校也辦得風生水起。實驗小學作為本地窗口學校,生源充足,管理規范,教學質量高,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想不到半月前,一名二年級女生被人拐走,雖說事件是在校門外發生的,但無疑給學校帶來了不安定因素,挑戰了學校的公信力。少數家長曾放出話來說實驗小學不安全,不值得信任,要把自己的孩子轉走。那個無知的馬保安極大地損壞了學校名聲,辭退他,嚴肅處理,那是必然的。好在公安已經介入,吃官司蹲號子犯哪條由法律說了算。吳校長本想把這樁棘手的事捂住,但不知是哪路神仙,用手機拍了那個農民工被銬被打的畫面,配上文字在微信圈里流傳,說什么學校保安不是執法主體,居然用手銬銬住一個經過學校門前的農民工,并用電警棍電翻。農民工何罪之有?遭此厄運。農民工生存狀態堪憂,政府管不管?
微信流傳后,網絡上也有了,質問培養人的實驗小學何時變成公安局抓人打人,希望給市民一個說法。大街小巷都在議論紛紛,說三道四,給實驗小學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學校賠錢不說,今年的文明單位、等級學校牌匾是保不住了,先進教師、安全先進學校將被一票否決……
吳校長知道,連著發生兩樁事件都不讓人省心,這回算是玩完了,好在傷者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
不過,這不算完,最讓吳校長惱火的事還在后邊。
媒體開始介入。本地媒體被宣傳部打了招呼,不準亂發報道,所有與實驗小學有關的紙質材料、影像必須經宣傳部把關審閱,同意了方可登載和播放。外邊來的媒體就讓人抓瞎,先是省級住本地一個電視臺一男一女兩名記者扛著攝像機來實驗小學采訪,吳校長和幾個副校長滿臉堆笑讓座,忙著遞煙泡茶,辦公室主任悄悄往那兩個記者兜里塞了紅包。那個胖胖的記者說,吳校長啊,你別見外,事情發生了,就要看善后工作是否到位,這是十分重要的。并要他對著話筒談談農民工被打傷后采取的措施,看望傷者的次數、人數,以及校內捐款救助傷者的情況,重要的是要取得傷者的諒解。吳校長說知道知道,這些事都正在做,我們除了組織各班派出代表看望章小明外,還動員了一些學生家長也來醫院看望。他的腹稿打了一遍又一遍,既講了學校應承擔的責任,也號召全校師生慷慨解囊為民工章小明獻上一份愛心。兩個記者也算是給了他一個面子了,算是給社會一個交代。
那個打人的學生家長雷高陽已被公安控制起來了,他女兒被人拐走的案件也有了重大進展,山東那邊破獲一個專門拐賣兒童的犯罪團伙,案犯已經交代,曾在這邊一所小學拐走一名女生。實驗小學及時將小女孩的照片發過去,那邊一對照,相貌完全吻合。這邊公安打拐辦的人已經向山東出發。吳校長聽到這個消息,高興得提筆完成了一副毛澤東的詩詞《沁園春·雪》的書法作品。
但是,事情還是沒完。
接到報料,都市晚報記者趙鋼從省城火速趕到現場采訪,把胖記者剛剛撫平的傷疤再一次揭開,令全體市民大跌眼鏡:農民工章小明居然是市委、市政府表彰的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是本地區樹立的農民工先進典型,現在卻被實驗小學保安和學生家長黑打致殘,把好人當做壞人。
那天,趙鋼走進病房,看到那個羸弱的民工,特別是那雙隱沒在近視眼鏡后面有神的眼睛好熟悉啊。章小明也看到了趙鋼,兩人當初交流過多次,是很熟悉的朋友了。是這個記者把他推上了領獎臺,讓他一個農民工風風光光地當了一回先進,也給那個建筑公司長了臉。過后,老板親自請了趙鋼和一群民工到本城最豪華的酒店吃大餐,喝了好幾瓶五糧液。
三年后的今天,章小明以這種方式再一次見到趙鋼,眼圈不由得紅了起來。人的命運就像有種力量在冥冥之中巧妙地安排組合。造物主弄人,當初風光不再,自己落到如此地步,先進人物和犯罪嫌疑人的差別何止天壤?
趙鋼說,小章,別難過,事情出來,得積極面對,我們當記者的,別無長物,就用這支筆為你討回公道。
公道?章小明搖搖頭說,公道對我還有何意?我已是殘疾人一個,先是左手兩個指頭被歹徒的菜刀剁了,后是左胳膊被攪拌機廢了,現在是鼻梁骨斷了,3根肋骨也折了,我……
一向口若懸河的趙鋼感覺到自己拙嘴笨舌,居然找不著一句溫暖的話來安慰眼前這個可憐的農民工,他今后的生活難以為繼啊 。
趙鋼那篇紀實通訊題目就特別打眼:《英雄章小明再次血灑校園》,一石激起千層浪,市民們再一次把這件事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吳校長和實驗小學的老師們成了市民們議論的對象,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
趙鋼的長篇通訊題目為什么說是“再次血灑校園”?原來三年前,章小明打工的那個建筑隊在城郊一個民辦幼兒園修食堂。那天,幼兒園在舉行“六一”節前的文藝排練,小朋友們正在無憂無慮地唱啊跳啊,突然,一個中年男子揮著菜刀沖進大門,向天真爛漫的孩子猛剁。那個女老師被嚇得蹲在地上瑟瑟發抖,六名孩子被砍死,三名被砍傷。歹徒還在繼續行兇,再次揮刀時,被剛從廁所出來的章小明看見,大吼一聲“住手”,飛奔過去就搶歹徒的菜刀。在兩人搏斗中,章小明左手拇指和食指被菜刀削掉,血濺校園。后在其他民工的幫助下將歹徒制服。
當時的新聞采訪就是趙鋼第一個趕到現場的,章小明從此少了兩個指頭。后來,章小明被市委、市政府表彰為見義勇為先進個人,上過電視,登過報紙,戴過大紅花,想不到現在又發生這樣的事。只不過兩次血灑校園的內容大相徑庭,一次見義勇為光鮮無比,一次被人疑為歹徒誤打致傷,難免讓人唏噓。
后來得知,那個手持菜刀的家伙戀愛受挫、家庭不睦,心理失衡,精神幾近崩潰,沒有人對他進行疏導和溝通,找不到宣泄口,便把黑手伸向了本村天真的孩子。
趙鋼通訊的結尾這樣寫道:現在,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被人打成重傷,差點就釀成生命危險。而且,這個英雄并沒有違法犯罪,僅僅是在實驗小學門口晃悠。晃悠有錯嗎?哪條法律規定學校門口不能晃悠?想看看學校的教學大樓有錯嗎?又是那條法律規定學校大樓不能讓人看?晃悠一下,朝著學校看看觸怒了誰?就被當成罪犯往死里打。我們不僅要問:一個保安,一個學生家長憑什么打人?誰給的權力?人性何在?天理何在?
3
門響了,馬保安跨了進來。他看到章小明的模樣,心里“咯噔”一聲,章小明最顯眼的是眼鏡,除了臉上傷痕累累,眼鏡也傷痕累累,一根細毛線代替一條失蹤的眼鏡腿把眼鏡拴住了掛在耳朵后面,左眼的眼鏡片碎成了兩片。他小心翼翼地說,小章,看到你好多了,我也就放心了。我真誠向你道歉,讓你受到傷害,對不起,對不起。馬保安邊說邊向病床上的章小明鞠了一個躬。
章小明說,道歉?你不覺得遲了點?
馬保安忙點點頭說,是是是,是遲了點。我的工作已經停止了,可能還要負法律責任。公安叫我這幾天不準走哪里,老實待在家里聽后傳喚。我就趁這個時候來看看你。過了怕沒有時間了。
馬保安說,小章,你怎么了,要不要我叫醫生?
不見狗屎不惡心。章小明趔趄了一下,差點摔倒,連忙扶著窗,他抹了一把額上的汗水,回到病床上,沒有理那個討厭的家伙。
馬保安說,沒事就好,沒事就好。小章,我沒別的意思,就是想問你,那天下午,你在學校門口晃悠,到底是為什么?
章小明說,有句話叫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終于想聽我解釋了?我當時被你銬住,我就說,你聽我解釋,你不但不聽,拿起電警棍就戳我。那么跋扈,那么牛逼,誰給你的權力?
馬保安拍拍腦袋說,我當時是鬼摸著了,傷了你也害了我。
章小明說,你知道一個學校的普通保安能使用警具嗎?
馬保安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學校發給我們,我們就用。
章小明說,算了,說了你也不懂。其實,我就是想進學校看看啊。
馬保安說,那你為什么不進去呢?
章小明咧咧嘴說,你們當保安的見著外人如狼似虎,平時進去要左盤查右登記的,我們一個農民工,敢進去嗎?
馬保安說,那你在下午學生進校門和學生放學出校門時幾次想隨大流混進去,為什么又猶豫不決呢?
章小明說,你說對了,我就想隨人流一起進學校,但你那雙鷹眼一直瞄著我,提著警棍,我咋進?
馬保安說,也倒是,我早注意你了,你一個下午都在校門口轉悠,傻子都覺得有問題。我們當保安的責任重大啊,一旦出差錯,我們吃不了也得兜著走。聽說過吧,半個月前,也就是你被打的前兩天,一個二年級的女生被門口一個賣冰糖葫蘆的人拐走了,至今還沒有找著,我們見你形跡可疑,而且有學生看見那個賣冰糖葫蘆的中年男人也像你戴一副眼鏡和一頂白色太陽帽,年齡相仿,只是,你那左手……說實話,我就懷疑你就是那個拐走孩子的家伙,還要來再次作案。
章小明說,所以你把嫌疑當證據,就下毒手了。
馬保安說,唔,我,我不該那樣對你。
章小明鼻子發酸,右手握成拳,真想打這個討厭的家伙一個滿臉開花。
馬保安說,我沒有惡意,就想弄明白,你一定要到學校里干什么?
章小明說,看看,就看看,不可以嗎?
馬保安說,看看,當然可以。我就想知道,學校有什么看頭,你又不來讀書,也不可能來教書,不怕你帶著一副眼鏡,文縐縐的,其實,你就是……
馬保安的話觸動了章小明最為柔軟的地帶,身子又開始發抖,由于發抖,聲音也哆哆嗦嗦的,像深秋枯樹上的黃葉,簌簌的往下落。他推了推那副近視眼鏡說,其實,我……我……就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說……你看上去戴副眼鏡,文……文……縐縐的,不過……不過,就是一個農民工,對吧?城里人看不起我們,也就罷了,連你……你,也看不起?你是什么……什么,東西?你雖然是一個保安,不過多了身灰狗皮而已。其實,說……說,穿了,你也是一個……一個……農民工,比我高貴不到哪里去。
五十步笑百步,烏鴉嫌豬黑,馬保安那塊多肉的臉脹得通紅。
馬保安仿佛看到了一絲仇恨在他心里燃燒,怯怯地說,小章,你要罵我你就使勁罵吧,即便打我我也不會還手的。
章小明喘了一會兒氣說,你是欺侮我沒有力氣打你?
馬保安忙賠著笑臉說,沒有,沒有。我真沒有那么想,只想表達那個意思。
章小明說,你一定要問,那我就告訴你,我高考落榜后,隨村里的二娃來這個城市打工,實驗小學的這幢教學大樓就是我們參與修建的。出事那天,我頭晚上看了一本小說沒睡好,特別疲倦,一跤倒在攪拌機旁,我的左胳膊,就……被攪碎了,與水泥灰漿一起攪拌了,被砌進了這幢大樓。我之所以在校門口晃悠半天,就是來看看那幢大樓,也是看看我的胳膊。第二天我和二娃就要回滇東北鄉下了,可能以后都不會再來這個城市了,這不就來看看嗎?
馬保安“啊”的一聲,看著面前這個斯斯文文的民工空空的左袖筒,嘴巴半天合不攏。
【責任編輯 楊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