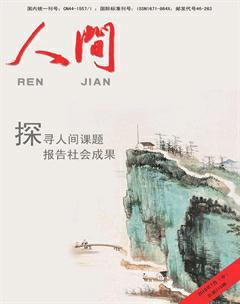地方立法權擴容背景下我國設區(qū)市立法權問題研究
鄧芬妮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
地方立法權擴容背景下我國設區(qū)市立法權問題研究
鄧芬妮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摘要:《立法法》修改后賦予235個設區(qū)的市地方立法權,我國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數(shù)量驟然增加。審視我國建國六十多年來立法領域的制度變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此次地方立法權的擴容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也符合我國改革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此外,此次《立法法》對設區(qū)市地方立法權的規(guī)定采取了保守主義,設置了較多的條件限制。地方立法權的擴容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挑戰(zhàn)。為保障地方立法權的有效行使,在國家層面,我們要堅持維護憲法權威和法制統(tǒng)一原則,轉變中央的治理方式;在地方層面,我們要明晰立法權限、豐富權力形式行使和完善立法監(jiān)督機制。
關鍵詞:地方立法權;設區(qū)市立法權;法制統(tǒng)一;立法監(jiān)督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終于表決通過了第三稿的《立法法》修正案,可謂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在新法的諸多亮點中,最具爭議的莫過于有關賦予設區(qū)的市立法權的相關條款,即修正案第31條。本文擬從我國地方立法權的歷史沿革和當前法治實踐的基本情況兩個角度,論證地方立法權擴容的必要性;繼而對地方立法權擴容后可能帶來的立法和實踐挑戰(zhàn)進行歸納并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一、地方立法權擴容的歷史沿革和現(xiàn)實需要
(一)地方立法權擴容的歷史沿革。市的立法權是我國地方立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市地方立法權的立法動態(tài)和理論研究動態(tài)的歷程可以看出,我國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可以說是一個不可逆的潮流和必經的過程。從其發(fā)展歷程來看,其主體范圍呈現(xiàn)不斷擴大的趨勢,經歷了從無到有,從試點到大范圍推廣,從點到線再到面的發(fā)展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初部分市重新獲得地方立法權以來,地方立法權的發(fā)展演變大致可以分為起步、探索發(fā)展和全面推廣三個階段。在起步階段,1982年的《地方組織法》修正案打開了我國地方立法權的大門,規(guī)定省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會,可以擬定地方性法規(guī)草案;并授權國務院批準了唐山等13個市為“較大的市”。至此,除重慶市外,較大的市的數(shù)量為39個。在探索發(fā)展階段,1986年《地方組織法》的修改,將較大的市人大常委會的擬定權規(guī)定為制定權。國務院也先后于1988年、1992年和1993年批準了寧波等6個市為“較大的市”。2000年我國《立法法》頒布實施,將經濟特區(qū)所在地的市納入到較大的市的范圍,使得較大的市的數(shù)量發(fā)展為49個。全面推廣階段,是以2015年3月《立法法》的修改為標志,將擁有地方立法權的市的數(shù)量從49個擴大到284個。從學術觀點的流變來看,學者的態(tài)度經歷了反對、質疑和接受的過程,研究的內容也經歷了從意識形態(tài)之爭到利弊分析之爭,繼而到現(xiàn)在的權限范圍之爭的歷程。在意識形態(tài)之爭中,主要圍繞著是否重新賦予地方立法權展開,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對授予市地方立法權還有較大的疑慮和擔憂,側重于意識形態(tài)和法制制度自身統(tǒng)一性的辯駁等宏觀領域。在利弊分析階段,在肯定是地方立法權擴容的前提下,探討有地方立法權的市的如何“用權”的問題,側重于地方立法權的制度構建等具體問題的研究。在權限范圍之爭的初期階段,也就是現(xiàn)在,目前主要注重地方立法權的權限劃分、程序、進度等問題的研究。
(二)地方立法權擴容的現(xiàn)實需要。一方面,地方立法權的擴容,是我國改革發(fā)展事業(yè)的“法律化”和法制建設的必然選擇和需求。在實踐中,對地方立法權的調適根源于改革所激發(fā)出的地方內在發(fā)展需求,而且每次的調適都與國家的改革戰(zhàn)略基本保持同步。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深水期和攻堅期,各地方權力機關和政府,尤其是基層的地方權力機關和政府,其所承擔的責任和處理的事務更為瑣碎和龐雜。于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市級地方權力機關和政府所擁有的權力往往難以滿足其日常運轉的需求。擴大地方的立法權,恰能解決當前問題,最大范圍內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充分發(fā)揮地方在某些領域和事項上的天然優(yōu)勢,降低制度運行的成本。
另一方面,擴大地方立法權的主體范圍,是我國實現(xiàn)法制統(tǒng)一的必然需求,也是提高立法質量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改革程度、經濟發(fā)展水平、社會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在適用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這樣或那樣不協(xié)調的情況。而且,在“事”、“權”不平衡、缺乏上位法指導的情況下,地方往往通過發(fā)布“紅頭文件”等方式變相“立法”;致使實踐中大量存在“超前立法”、“越權立法”和“同質化立法”的現(xiàn)象。通過賦予設市的地方以地方立法權,不僅有助于我們?yōu)閷嵺`中存在的“地方立法權”正名,規(guī)范其行使;而且有助于我們提高立法質量,避免“立法同質化”的大量存在。
二、地方立法權擴容面臨的挑戰(zhàn)
在地方立法權擴容的背景下,我國地方面臨的挑戰(zhàn)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個角度看待:客觀而言主要是立法權限的模糊性;主觀而言主要是立法條件的不完備。
立法權限的模糊性。從《立法法》修改稿初稿和二稿的有關立法事項規(guī)定來看,立法者對于哪些可以歸入到地方立法權限的范圍是存在逐步明確、認識逐漸加深的過程。初稿列舉為“城市建設、市容衛(wèi)生、環(huán)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二稿列舉為“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的事項”;三稿則沿襲了初稿和二稿放寬立法權限的基本精神,將地方立法權限的范圍規(guī)定為“城鄉(xiāng)建設與管理、環(huán)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然而,不能忽視的是我國目前為止仍未明確何為地方性事務,也未明確城鄉(xiāng)建設與管理、環(huán)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的具體內涵。其對立法權限的限制看似清晰,實則內涵具有相當大的模糊性。
立法條件有待充分。一般地說,設區(qū)的市和其他新增地方立法主體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其立法能力和有關準備工作應當具備以下四個基本條件:一是設置相關的工作機構,并配備必要的立法工作人員;二是工作人員具有專業(yè)的立法知識和技能;三是立法活動的有序化,即有相應的立法規(guī)劃和立法計劃;四是有相應的立法工作制度予以配套施行。由于過去只有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才擁有地方立法權,一般的市不具有地方立法權,一般的市也就難以快速齊備上述四個基本條件。可見,設區(qū)的市要真正有效的行使地方立法權,還需一個過渡、適應和探索的階段。
三、新形勢下地方立法權的發(fā)展建議
堅持法制統(tǒng)一原則。設區(qū)的市在行使地方立法權的過程中,尤其要重視遵循法制統(tǒng)一的原則。堅持法治統(tǒng)一原則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遵循法律保留原則,即遵循其所劃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機關立法與行政機關立法的范疇;二是遵循法律優(yōu)先原,即遵循其所確立的各個立法主體按照憲法法律優(yōu)先的原則,下位法服從于上位法。由于受到各方資源的限制,《立法法》的修改還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在地方立法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xiàn)模糊、“黑白”和“真空”地帶。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權力機關要在堅持法治統(tǒng)一和維護法律權威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和積極性,在做到“根據(jù)法律”、與上位法相協(xié)調的同時,又要因地制宜的服務于地方。轉變中央治理方式。目前,我國地方立法新結構剛剛成形、各方面規(guī)則尚未完備。為了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地方立法權濫用等消極情形的出現(xiàn),需要中央在較大程度上提供幫助和維護。這種自上而下的規(guī)則設定,就需要中央轉變治理方式:從一個具體規(guī)則和立法模式的設計者逐漸轉變?yōu)橐粋€基礎規(guī)則和凈化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者。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應主要著力于實現(xiàn)國家治理的現(xiàn)代化和立法關系的法治化。通過建立健全民主立法機制、備案審查機制等方式防止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通過正確理解和合理適用“不抵觸”原則來解決立法沖突、維護法制統(tǒng)一;通過完善落實立法聽證、審核、立法后評估程序來敦促立法質量提升等。
提升立法能力。地方立法是一項政策性、專業(yè)性和操作性都很強的系統(tǒng)工作。鑒于當前多數(shù)設區(qū)市尚不具備充足的專業(yè)立法人員,筆者建議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的起草可以委托第三方,特別是以科研項目的形式,委托給具有立法能力、立法經驗的科研機構、學術團體,借助社會力量,彌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專業(yè)立法人員的不足。另外,在尋求外部援助的同時,立法機關更要注重提升自己的“軟實力”,通過派遣工作人員到有地方立法經驗的市進行學習交流、招聘錄用有相關背景、能力的人員等方式加強立法人才的培養(yǎng)和儲備,逐步提高自身的立法能力。
四、結語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既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挑戰(zhàn)。在認識有待提升和立法條件有待完善的現(xiàn)實情境下,要想充分發(fā)揮地方立法權的效用,在國家層面,我們就要堅持維護憲法權威和法制統(tǒng)一原則,轉變中央的治理方式;在地方層面,我們就要明晰立法權限、豐富權力形式行使和完善立法監(jiān)督機制。
參考文獻:
[1]程慶棟:《論設區(qū)的市的立法權:權憲法為與權力行使》,載于《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8期。
[2]參見周尚君、郭曉雨:《制度競爭視角下的地方立法權擴容》,載于《法學》2015年第11期。
[3]周尚君、郭曉雨:《制度競爭視角下的地方立法權擴容》,載于《法學》2015年第11期。
[4]周尚君、郭曉雨:《制度競爭視角下的地方立法權擴容》,載于《法學》2015年第11期。
[5]曹全來:《新增立法主體背景下設區(qū)的市地方立法權行使問題研究——以提高立法質量為中心》,載于《法制與經濟》2015第20期。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7-0077-02
作者簡介:鄧芬妮(1992-),女,廣東 省梅州市,漢族,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