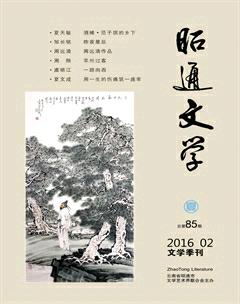于你、于我、于這個世俗
娘的目光
村莊種植的白發
長出裊裊的炊煙
你,立在村口
把遠方放在心里
用目光醞釀成白蠟樹下的酒
深埋于泥土
傾聽回家的杯盞
夜色披在你的身上
用秋風把牽掛折疊成渴望的信
多少年來,樹也老去
只有孤獨的風把酒灌醉
落日伸出了老繭的手
戳痛你望兒盼女的眼
路,在鞋里
在中秋的月光里
徘徊于村頭的石坎
雕 刻
拾起一把刀的力量
在樹根的表情里平心靜氣
勾勒人世間的花草,以及飛禽走獸
一個枯萎的春天復活了意識
拿起一把銼子的牙齒
在交錯的空間里咀嚼碎末
掃去時光的殘余,以及凡塵污垢
一只跳動的母雞產下了蛋殼
撩起歲月的面紗
在枯朽的失落里重塑形象
品味秋水流泉,以及山峰海韻
一樁樁故鄉的往事浮在心頭
刀具的恐慌
在下手的那一瞬間
刀鋒就猶豫不決
一粒粒沙土擋不住歸家的路
卻好像削平了故鄉的產床
“根”啊!莊重的符號
我怎么忍心做一個無情的劊子手
木雕的審視
它懷疑我的胡須
可不可以做羊群的鞭子
木訥過后,指甲開始變成化石
它審視我的腰身
可不可以做海邊的望夫石
浪潮過后,足印開始變成印章
它消化我的沉思
在偌大的胃里痙攣
饑餓過后,瞳孔逐漸縮放魔幻的光
于你、于我、于這個世俗
無論天色陰暗與否
我都一直在走過世俗的歡笑與蒼涼
當一個夢被眼前的桂花炫耀的時候
我想起你的眼,好像那就是桂花的香
或者,你散發出的濃艷只會吞噬無盡的凡塵
于是,你遠走的背影只能躲進黑夜的臉
無論大雨來臨與否
我都一直在觀望遠方的明凈與暗淡
當一片葉被路過的風聲卷起的時候
我想起你的唇,好像那就是雷電的閃
或者,你傾訴過的誓言只會咬碎破舊的愛情
于是,你回首的姿態只能彌補夜空的失眠
無論世俗太平與傷感
我都一直在舉起平淡的服飾與軀殼
當一雙破鞋被繁華的街景對比的時候
我想起你的手,好像那就是纖夫的愛
或者,你暢想過的心境只會懸浮于宇宙邊緣
于是,你隕滅的嘆息只能痛惜命運的不公
無論于你還是于我
我們都一直在兩個世界的節點注視與沉默
于是,所有的一切只能隱藏于內心
隔天相邀,隔海相泣
椿樹的長勢
開門后,一堆泥土落在目光里
密密麻麻的草遮掩著童年
穿透墻孔的不是陽光
是多年遠走后遺留的光陰
蒿葉治不好心病
破瓦難擋老屋的空曠
蛛網密織的窗戶
浮現炊煙的淚光
關門后,一棵椿樹長在心上
躍躍欲試的雨滴拍打著院落
刺痛裂口的不是鴉聲
是樹根擊痛堅韌的石沿
椿香調不出胃口
斷梯難撐牽掛的彷徨
椿樹安然的長勢
突破骨髓里的故鄉
竹林邊的溪水
青春去哪兒了?
去問竹花開放的沙土
去問風干青刺狂傲的枝節
去問牧羊人翩翩的棉襖
去問溝壑消失的鐮刀
竹林邊的打盹
折磨鳥兒展開的翅膀
溪水拍擊的青苔
是一片崖面的癬
流過的是水的速度
卻看過許多枯枝在風里搖擺
一只飛鷹俯沖下來
帶走了一座山的渴
觀油畫
歷史的腳步
在畫家的筆下成為杰作
于是,手中揮舞的思緒
留給后人無盡的遐想
好像那些皺紋和胡須都在說話
也許,我們都沒在意過程的細節
所以,當樂譜響起的時候
我們的細胞都在狂放
馬匹承載的往事
靠近煙斗
它會在仰望里寫下內心的獨白
當我們也老去的時候
有沒有一種可能
那怕成為一尊雕塑的粉末
河
河是交織的血管
從故土穿越,遠走他鄉
在太陽和山的吻里思緒惆悵
河是移動的夢幻
點墨壯麗,氣吞艱險
在浪花涌動的時刻描摹愛情
河是生命的流向
經歷坎坷,見證苦難
在源遠流長的腳步里永不停息
與荒野的對話
我是在夕陽謝幕后的夜里獨自看你
對視一匹匹野馬啃噬過的草原的眼眸
當薄霧曾經的多情變得淡然的時候
心中的流泉羨慕不已
山花一直守候牧人的腳步
多想再次重溫夕陽的光彩
樹影是人類播撒的思想
在草地上尋覓戀人的纖纖手指
那飄飄蕩蕩的白
對比一片森林的感傷
石頭在腸胃里痙攣
這個子宮里的深秋
帶走落葉也讓蚯蚓瘋狂
水草深陷的眼角
容不下蛙鳴
只有異常的靜態
可以安放故鄉的天空
牛羊吞下的云朵
在心里躁動
飛鷹展翅,托起又一輪太陽
遠方的古堡怎么羞澀起來
留下的胭脂
是否可以喂飽千年的風沙
我就是你的情人
為何錯過了你多年荒蕪的目光
作者簡介:魯慶鴻,云南魯甸人,教師,現供職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陽區一中。有詩歌、散文及英語論文等發表于《邊疆文學》《春城晚報》《昭通文學》《昭通日報》等報刊雜志。
【責任編輯 夏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