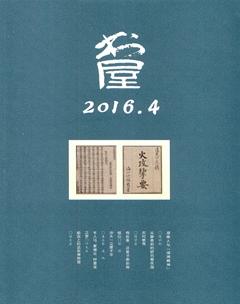“現代玄奘”
劉開生
一
譚云山1924年7月到了南洋以后,即全身心地投入教育華僑下一代以及向廣大華僑傳播中華文化的偉大事業之中。他首先在新加坡英俄街的工商學校教書。1926年10月,柔佛州麻坡市中華學校的中學三年級主任、他的好友紹崖因為要到檳城去當報館編輯,學校不放他走,除非他能找到譚云山去接替他。譚云山一方面鑒于幫助友人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想換換環境得到點休息,就去到麻坡中華學校教書。他后來又從麻坡去瓜拉丁加奴的中華維新小學當教務主任(或者校長),他還在南洋華僑學校任教過,又參加了柔佛州巴株巴轄的愛群女校的興辦。在此期間,南洋平民學校師范科還曾請他去教“中國文字學”。在教學的同時,他還參與辦報、寫詩。
初到工商學校時,他“初出校門,入世尚淺……濫竽工商學校,承校長以訓育重職相屬”,在這個職務上他盡心盡力,與學校校長及各教職員一起摸索出一套方法,寫出《一個訓育方法的商榷》的長文,從1926年1月8日起接連三期發表于《叻報》副刊。
譚云山在新加坡一邊教書,一邊于1925年10月為《叻報》創辦了一個文藝副刊《星光》,并擔任主編。此后,1926年9月又和“駱駝社”社員陳子實、張登三及何學尼共同為《新國民日報》(其前身是孫中山創辦的《國民日報》)創辦文藝副刊《沙漠田》,共出版了二十期左右。
譚云山除了編輯文藝刊物,本身也是馬華新文學團體的一個有成就的詩人。除了在《星光》和《沙漠田》副刊上發表了大量詩作,仍有作品在中國大陸發表,他的這些詩作1930年由廣州青野書店以《海畔》為書名出版。
在南洋,譚云山還收獲了純真的愛情,他與同鄉、同事陳乃蔚相知、相戀,直到結為秦晉之好。
就在譚云山到麻坡中華學校才幾個月時,1927年7月,泰戈爾來到新加坡,并且到了該校訪問和演說。從學生時代起就對泰戈爾充滿了敬仰與愛戴,作為一個喜愛詩歌的文學青年,譚云山幾乎讀過泰戈爾所有翻譯出版的小說和詩作,到南洋以后,他更有了到印度去留學的準備。現在,有機會面對景仰已久的詩圣,他向他介紹了自己的情況,還敞開心扉向泰戈爾談自己的人生理想。
泰戈爾1924年訪華時就曾和中國友人達成共識,即由梁啟超帶領其他中國學者到圣蒂尼克坦國際大學教中文并開展中國研究,由國際大學的印度學者到北京清華大學去傳播梵文并開展印度研究。可是,后來這些計劃未能實現。面對眼前這個熱情洋溢、充滿理想的中國青年,他多年的中印友好、發展中印文化交流的計劃和理想有可能實現了。于是,當場決定邀請譚云山去印度國際大學教中文,開展中國研究和佛學研究。
1928年8月,譚云山告別新婚的妻子,抱著“白馬投荒步昔賢”的宏偉壯志,只身一人乘英國輪船離開南洋前往印度,從此開始了他在國際大學的新生活。譚云山來到國際大學一面教授中文,一面學習梵文、佛學和研究印度文化。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譚云山與六十七歲的泰翁朝夕相處,成為真正的忘年交。
譚云山原本希望到國際大學當學生的,現在一來就要當先生,而且面對的還是一些學問大家,他一時還不能適應這個角色。于是,和兩位元老夏斯特利和克蒂莫亨·沈商量得出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用譚云山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決定我每星期教三堂中文課,沈教授每星期也教我三堂梵文,夏斯特利教授會經常和我進行自由討論。他會向我提出有關中國研究的疑問由我解釋或互相討論。我會向他咨詢有關印度研究的問題由他講解。”
譚云山與國際大學的同事們討論,希望實現中、印兩國民族的聯合和了解,互相研究兩國民族文化,決定以國際大學作為實現這一理想的基礎,提出如下計劃:一,多招收幾個中國學者來印度;二,在國際大學特別設一個中國學院;三,多介紹幾個印度學者去中國;四,在中國方面特別辦一個學院。
有了計劃,譚云山開始了實行這一計劃的行動。
他曾經接到過國內許多來信說要來印度國際大學,但大多沒有了消息;后來雖然來了三個,不久也走了。他在國內的《東方雜志》發表了《印度國際大學》一文,詳細介紹國際大學的情況,希望能引起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并為此寫信給國內的中央大學和蔡元培、易培基、歐陽競無等先生商量,都未得到滿意的結果。事情的這種發展讓譚云山深感他們要實現這種理想的困難,但他們也決定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要百折不回地勇往直前。
譚云山原來的的計劃,想縱不能如玄奘大師留居那么久,至少也要以五六年的時光消磨在印度,打算以三年在東印度詩哲泰戈爾先生之圣蒂尼克坦國際大學,以兩年在印度圣哲甘地先生之沙巴馬地真理學院,然后再實行中印民族之結合與中印文化之溝通,一面恢復兩國過去的舊情誼,一面創造兩國未來的新關系。
1930年夏天,夫人陳乃蔚在馬來亞突接到從家鄉遲來的父親與伯父雙亡的噩耗,譚云山就在假期中匆匆離開圣蒂尼克坦去了新加坡,準備與夫人帶著“愛之果”一起回國。
二
不料一到新加坡,就遭到幾個朋友的勸阻。恰巧這時緬甸仰光的《興商日報》正在托新加坡的友人找一個主筆,友人認為譚云山干這個很合適,便推薦了他去。譚云山于是安排夫人和孩子坐船回國,自己半苦悶半欣慰地踏上了到緬甸的旅途,于7、8月間去了仰光。譚云山到緬甸后本以為至此可以安定地工作一個時期,誰知又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在仰光,他結交了到緬甸游歷并考察佛事的湖南同鄉道階老法師,通過道階法師又接觸到一位同鄉要人謝國梁。
歷史上,英國殖民主義力圖以種種名義進入西藏,遭到藏族僧俗的強烈反對。此后英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活動逐步升級,直到對西藏發動兩次武裝侵略戰爭。為保衛西藏,應對邊疆危機,1909年謝國梁就在藏族青年組建的新軍出任管帶,此后長期在西藏工作。
英帝國主義不愿意看到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加強聯系,竭力挑撥藏漢關系,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脅,企圖使藏族同胞背離國民政府。1930年初,利用尼泊爾商人在拉薩的稅務糾紛,叢恿尼泊爾提出抗議,揚言全國總動員,派軍隊進攻西藏。
此時的謝國梁已升任蒙藏委員會的專門委員。1930年4月,由于長期在西藏工作過的背景,他奉派赴藏聯絡調解尼泊爾與西藏地方的糾紛,同時更重要的是將國民政府所提解決藏事問題的具體意見十一條送達西藏,并與十三世達賴接洽,切實商談。
謝國梁年事已高,政府決定派他的兒子謝瑞清(時任職外交部)同行,擔任秘書。按原來計劃,兩人應經過印度進入西藏。但考慮到英屬印度當局阻撓,他們便秘密前往緬甸,想經過云南、西康進藏。可是不幸的是,在盛夏的熱帶,兒子因感瘴氣于9月22日在緬甸瓦城猝然身亡。在他老人家孑然一身,逗留在瓦城、梅苗和仰光一帶,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之際,同鄉道階法師和兩位在緬甸經商的同鄉黎子清和李震中介紹他認識了譚云山。
謝國梁與譚云山一見傾心,相見恨晚。謝國梁決定聘譚云山為秘書長陪同進藏,譚云山表示,他不在于名義和薪水,是以私人感情幫忙,“盡國民責任為政府盡力”。
經過中國駐仰光、加爾各答領事協調,兩人喬裝改扮進藏,還秘密地與西藏著名商號邦達昌聯系,讓謝國梁、譚云山在葛倫堡化裝后悄悄加入邦達昌的商隊,混進西藏。
此時已是西藏的隆冬季節,大雪封山,一路皆雪地冰天,兩人隨著商隊穿行在喜馬拉雅的崇山峻嶺之中。謝國梁年將六旬,迭經旅途顛沛、喪子之痛,經過二十多天的艱難跋涉,謝國梁一病不起了。隨著病情逐漸加重,他在病榻上斷斷續續向譚云山多次囑托,一定要到達拉薩晉謁達賴,傳達國民政府解決藏事問題的具體意見和宣慰事項:“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為中國全國(含漢、滿、藏、蒙、回、苗等)之中央政府;中藏之關系乃國家與地方或特別區域之關系;解決中藏問題即解決中央與西藏地方聯合統一合作,以共謀國是之問題。”在最后向他交代了所帶禮物、經費等全部情況,要求他一定要代他完成使命之后,在距離拉薩僅一天路程的地方咽氣了。
謝國梁之死使譚云山十分悲慟,也為譚云山此行帶來困難與考驗。譚云山不是國民政府派去的,他加入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好好護送政府專員抵達拉薩、完成使命。現在到了這個地步,他決定認真擔當起“專員秘書”的責任來。沒有受過任何訓練的譚云山展示出不俗的政治才能,他面見達賴遞交了政府信件,代表中央加以慰問,并利用一切機會,將中央之主義政策加以解釋宣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拉薩期間,達賴對待他很優禮而又親熱,處處安排,都表明他的“親漢”,要遠離英國人,傾心于國民政府。
譚云山在拉薩住了兩個月,就于1931年2月15日離開拉薩返回,達賴并派人員護送至印度邊境,還特地委托他帶一封信到印度給圣雄甘地,代他問候。
譚云山自拉薩出發后,在冰天雪地里騎馬走了二十多天險峻的山路,再次跨越乃堆拉山口進入印度,回到國際大學。由于這次西藏之行,是一定要回國作個交代的了。回國之前,他安排了一次西游,并將這次的游覽經歷寫成《印度周游記》,在國內出版,傳誦一時。
周游期間,為了完成傳遞達賴信件的任務,譚云山特地繞道到沙巴馬地訪問了真理學院,并到巴多利去見了甘地。他莊嚴地向甘地表達了自己誠懇的敬意,轉交了達賴喇嘛的信和問候,在這里他與甘地親密相處了三天,就中印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談,還應邀參加了鄉村集會,自此與甘地有了深交。他與甘地通信來往,還寫了很多介紹甘地的文章或翻譯甘地的著作在國內發表。可以說,譚云山對甘地的崇拜甚至更超過他對泰戈爾的敬仰。
三
1931年6月,譚云山回到國內,他首先到南京向國民政府提交了赴西藏的述職報告,然后到妻子陳乃蔚的家鄉探親,并悼念在“馬日事變”中犧牲的岳父兩兄弟。此前,國民政府已在南京為謝國梁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在這次赴藏完成中央的使命中,譚云山也進入了最高當局的視野。所以,他一回到國內,就受到了新聞界的熱烈追捧。加之在探親的幾個月內,他寫了多篇文章在雜志發表,因此,“譚云山”這幾個字廣為人知了。泰戈爾訪問中國時曾表示有意與中國學者一起組織“中印學會”,他感到現在是將泰戈爾的愿望付諸實現的時候了。
大約在1931年的9、10月間,譚云山離開湖南到南京、上海等地,將他的想法與中國學術界、文化教育界人士磋商,得到有識之士響應。其中,支持最力的是蔡元培和戴季陶。在蔡、陶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推動下,“中印學會”的籌建工作獲得突破性進展,不少高官要員包括蔣介石都對籌建工作給予高度重視。
1933年6月,在譚云山的努力下,《中印學會:計劃、總章、緣起》出版。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文獻告訴我們:“中印學會”“以研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并融洽中印感情,聯合中印人民,以創造人類太平,促進世界大同”為宗旨。“中印學會”意在聯合中印人民,恢復舊情,開創新關系。9月,譚云山寫信將籌建中印學會的情況向泰戈爾作了匯報。次年8月19日,印度“中印學會”在泰戈爾住所成立,由泰戈爾任會長,尼赫魯任名譽會長,譚云山與陳友生博士代表中方出席了成立大會。
同年10月,譚云山返回國內,報告印度的進展情況,并帶來了一封泰戈爾給蔡元培的信,信中說:“我希望我的朋友熱情歡迎這個學會,并慷慨地幫助我的朋友譚云山教授實現他的計劃,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團體以促進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這樣,在蔡元培、戴季陶、泰戈爾和譚云山的籌措之下,1935年5月3日,中國“中印學會”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關于“中印學會”的成立日期、地點,有過不同的說法,甚至爭論。為此,筆者查到《內政公報》1935年第八卷十五期第八項“集會結社事項”中記載:
中印學會會章計劃準予備案——批中印學會發起人代表譚云山呈一件為組織中印學會,呈送會章計劃等,祈鑒核準予備案由。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來呈暨附件均悉。準予備案,附件存。此批。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日
可以確認5月3日的成立日期是準確無誤的。奇怪的是“中印學會”會章計劃等是四月二十九日才呈報到內政部的,內政部五月二日就批了,而第二天就開了成立大會。看來是籌備過程中疏忽了報批的這一項手續了。
學會推選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為理事長,戴季陶為監事長,譚云山擔任秘書,負實際事務責任。不久之后,“中印學會”由于有國民政府捐款給印度的事項,領導權就轉入在政府中任要職的戴季陶、陳立夫、朱家驊等之手,譚云山則擔任“理事”,也是學會在印度的全權代表。但在實際上這個組織很特殊,它在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中印文化交流的組織,還具有一種基金會的性質,是中國政府及私人向泰戈爾的國際大學發展中印研究,以及開展中印政治與文化交流做出捐獻的渠道。
“中印學會”成立之后做了許多重要工作。首先是在印度國際大學內設立了中國學院,作為兩國文化交流的基地,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包括組織演講、專題研究、文化考察、出版圖書、互派留學生和學者等。還推動或協助安排中印兩國重要政治人物的互訪。如1939年尼赫魯的第一次訪華,1940年戴季陶和1942年蔣介石夫婦的訪印等。這些活動大大提高了“中印學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其影響還不僅僅是在文化、教育、宗教等領域,而是對兩國政治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譚云山在神州與天竺之間牽線,以“中印學會”作為黃金紐帶,使中、印兩國關系得到了發展。戴季陶評價說,譚云山“致力于中印文化的融合,他倡議組織中印學會,這種努力在意義上不亞于佛教高僧玄奘、義凈的壯舉”。
四
“中印學會”成立之后的重要任務,就是籌建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這是泰戈爾的“國際鳥巢”吸引“外國鳥”的關鍵一步,也是譚云山在國際大學與印度教授們商議的實現中印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的計劃之一。譚云山1933年向泰戈爾匯報籌建“中印學會”的情況的信中,就提及他會見蔣介石和戴季陶時,他們答應了籌建中國學院之事。1934年被派往印度參加印中學會的成立大會期間,譚云山告訴了泰戈爾國內掌握“中印學會”領導權的人士(他們也都是政府要員)正在考慮如何向國際大學捐贈及建立起長期的中印文化交流問題,他請泰戈爾給戴季陶等去信對建立中國學院作出具體建議。此后,經譚云山在中國和印度之間多次奔走和無數中、印友人的努力,1937年4月14日,中國學院終于隆重揭幕了。
中國學院建成最高興的人就是泰戈爾,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他不僅親自主持揭幕典禮,還把這件喜事幾乎告訴印度學術界所有名流,邀請了一些印度公眾代表來參加成立儀式,使它成為一件國家大事,場面十分隆重。
中國學院成立后,譚云山擔任中國學院院長兼教授,負責主持學院的工作。自此,泰戈爾的“世界鳥巢”學府就有了永久性的中文班、永久性的中國研究機制以及永久性的中文圖書館,出現了一種新學術領域——中印學。國際大學變成了泰戈爾在國際大學成立慶典演說中所說的中印文化與中印學術交流的前沿陣地。譚云山作為中國學院院長積極執行這兩項任務,具體抓的是兩點:第一是在學院中建立起印度研究、梵文、佛教研究的雄厚力量;第二是利用學院的獎學金與住宿吸引國際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來進行交流。
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印關系發展的結果,為實現兩個偉大民族相互了解、增進友誼的強烈愿望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在此后的歲月中,不斷有中國學者到那里去學習印度文化,那里也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文化的印度專家學者。
中文教學和有關中國研究的課程是中國學院教學的主要和常態化的內容。在譚云山的幫助和推動下,印度的中國研究、中文教育都進入了一個新境地。而印度中國學院以外的各大學設立中文課程時也都請譚云山去做課程大綱的設計。可以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印度沒有那個學術機構的中文課程不是直接征詢了譚云山的意見而設計的。
中國學院是印度學術界第一個中國研究機構,是貫穿中印兩國古今的文化紐帶。中國學院成立,代表著中國與印度重新恢復了文化交流,從此中印之間有了知識匯聚的所在。從1937年開始一直到1962年為止,可以說譚云山是這一期間印度中國研究的精神指導。他一方面使中國學院成為中、印兩國學者互相切磋、進行研究的聚集的場所,使他們集中于中國學院變成中印學研究的急先鋒;一方面自己向印度朋友介紹中國文化,解釋中國文化。
泰戈爾一貫認為佛教是歷史上中印文明親屬關系的靈魂,希望中國學院注重佛教的研究。譚云山對此深以為然。為此,譚云山首先注重在中國學院營造佛學研究的氛圍,在佛教界建立廣泛的聯系,把中國學院發展成各國佛教專家交流的場所。其次,廣攬佛學專家,建立研究隊伍。譚云山自己盡力向印度朋友介紹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情況,還邀請不少佛學家來到中國學院。
譚云山根據佛教在中國和印度的交流的狀況,專門設計了一個“從中文和藏文的著作中重新找尋失去的梵文”的項目。我們知道,“佛教源自印度,茁壯于中國,之后傳播全世界”,但大乘佛教在印度卻失傳了,連大乘佛經也很少能在印度找到。全世界的佛教經典包括印度的佛教經典,全都譯成了中文。印度本土所遺失的經典,都可以在中文文獻中找到。譚云山的宏偉計劃就是從中印學會捐贈的文獻中,把中文的大乘經典翻譯成梵文,恢復其原來的狀況。可惜的是,1948年以后,中國學院失去中國財源,研究經費大減,這一宏偉計劃只能不了了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