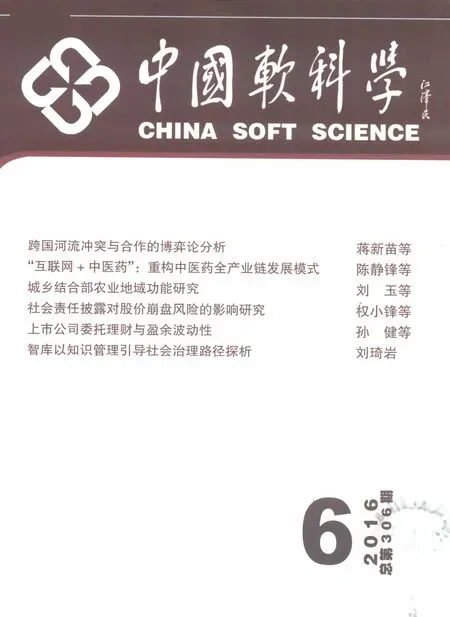跨國河流沖突與合作的博弈論分析
蔣新苗,虢麗霞
(湖南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南 長沙 410006)
?
跨國河流沖突與合作的博弈論分析
蔣新苗,虢麗霞
(湖南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南長沙410006)
摘要:跨國河流的地緣政治因素使得水權(quán)分配問題充滿了復(fù)雜性和不確定性,各沿岸國作為跨國河流水權(quán)主體對于沖突與合作,雙邊合作與多邊合作等問題各持己見。本文借用博弈論的“鷹鴿博弈”、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和納什均衡探析跨國河流中各沿岸國策略選擇的規(guī)律,推動合作、減少沖突,力圖對全球水資源的利用與發(fā)展等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關(guān)鍵詞:跨國河流;博弈論;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納什均衡
據(jù)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的報(bào)告,全球共有263條跨國河流,其中至少有158條河流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問題,其中河流各沿岸國合作與否,采取何種策略,權(quán)利主體之間的博弈成為爭論的焦點(diǎn)*國際上,對于跨國河流有多種說法,還有跨界河流、跨界水道、多國河流、國際水道等。此處選用跨國河流是基于國家主權(quán)和國際水權(quán)的雙重考慮,跨國河流以河流為主體,但不能離開國家主權(quán)這個重要的角色,只能依據(jù)各沿岸國的利益優(yōu)先對水權(quán)的分配作綜合考慮。因此,跨國河流意指流經(jīng)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河流,即多國河流。但跨國河流之爭不僅源于多個國家對整條河流的共有,更因?yàn)楦鱾€國家對占據(jù)河流標(biāo)段的單獨(dú)占有與管轄。“跨國”強(qiáng)調(diào)了國家主權(quán)對“河流水權(quán)”所有權(quán)和使用權(quán)分配的重要影響與制約。選擇“河流”而不是“水道”,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將河流視為“水生態(tài)”,將整個立體空間以及空間以內(nèi)的全部資源都包括進(jìn)來。。跨國河流水資源不同于國內(nèi)河流,不能依賴某個超越國家的體制對水權(quán)作強(qiáng)制性分配,于是出現(xiàn)了各河歸各管,“一條河流一種方案”的多面景觀[1]。
一、跨國河流水權(quán)博弈主體:沿岸國
一直以來,關(guān)于跨國河流利用的研究都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宏大敘事。大多學(xué)者認(rèn)為在國際法層面,能夠?qū)鐕恿魉畽?quán)進(jìn)行配置,獲得跨國河流初始分配水權(quán)的基本主體是國家,準(zhǔn)確地說,是河流沿岸國家*到目前為止,并沒有超越國家的上位力量。國際組織雖然也有參與建言或推動作用,但它并不是超越國家之上的強(qiáng)制力量。在跨國河流的事務(wù)中,非沿岸國雖然也有通過組織編寫參與公約或者外交途徑的方式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但并沒有實(shí)質(zhì)的、穩(wěn)定的、有力的地位參與水資源的所有與使用。。
(一)跨國河流水權(quán)理論
關(guān)于跨國河流水權(quán)論,學(xué)術(shù)界主要分為四個論斷傾向:絕對領(lǐng)土主權(quán)論、絕對領(lǐng)土完整論、有限主權(quán)論和沿岸國共同體論。“絕對領(lǐng)土主權(quán)論”,也稱為“哈蒙主義”,側(cè)重國家主權(quán)對領(lǐng)土的控制,主張一個國家對流過其境內(nèi)的水資源擁有絕對的權(quán)利而不受任何外部限制,沿岸國對境內(nèi)的跨國河流部分可以無限制地開發(fā)使用。“絕對領(lǐng)土完整論”側(cè)重河流的完整性,主張沿岸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改變跨國河流的自然水流,除非得到下游國或鄰國的預(yù)先同意,否則就是侵犯相鄰沿岸國的領(lǐng)土完整。這兩個理論都屬于極端原則,只強(qiáng)調(diào)一方的利益,各國對此意見分歧較大。進(jìn)入20世紀(jì),逐漸得到各國法律文獻(xiàn)和具體實(shí)踐接受的是“有限主權(quán)論”,該理論確定沿岸國都有權(quán)開發(fā)利用其境內(nèi)的跨國河流部分,但也有義務(wù)確保不對其他沿岸國造成重大損害。但是對于“重大損害”的標(biāo)準(zhǔn)仍然沒有定論。近年來,伴隨著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以及水資源綜合管理逐漸被國際社會認(rèn)可,沿岸國共同體理念逐漸進(jìn)入跨國河流治理領(lǐng)域。沿岸國共同體論是指將整個河流流域視作利益共同體,采用共同管理的方式,使整個流域?qū)崿F(xiàn)最佳而全面的發(fā)展。但有學(xué)者就對跨國河流“沿岸國共同體論”提出質(zhì)疑,稱其實(shí)質(zhì)是一種追求最大正和效益,超越國家主權(quán)界限,追求流域最大利益的近乎“烏托邦”式的理論學(xué)說[2]。
實(shí)踐中,因?yàn)楦髁饔蚯闆r存在差異,各國政治經(jīng)濟(jì)利益訴求不同,國際上通常根據(jù)各流域徑流貢獻(xiàn)情況、已有的用水需求情況、河流的本身徑流特征等因素進(jìn)行談判,達(dá)成具體的分水協(xié)議[3]。協(xié)調(diào)國際水爭端主要是通過國家間的外交途徑來進(jìn)行,反映的更多的是國家間的協(xié)調(diào)意志,國際司法僅作為備用的“后盾”[4]。在現(xiàn)實(shí)跨國河流沿岸國對水資源競相角逐的競技場,跨國河流水權(quán)解決問題的實(shí)質(zhì),是國家水資源主權(quán)范疇下的國家間水資源利益的分配與平衡,以及共謀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協(xié)商與合作的國際義務(wù)[3]。跨國河流的地緣政治因素使得河流沿岸的國家,因?yàn)楦鲊嬖V求層次不同,呈現(xiàn)沿岸國家之間利益多目標(biāo)的“鷹鴿博弈”關(guān)系[5]。
(二)沿岸國“鷹鴿博弈”
沿岸國A和沿岸國B都有兩種策略可供選擇,即“鷹策略”或“鴿策略”。“鷹鴿博弈”的穩(wěn)定演進(jìn)策略共有三種: 一種是鷹與鷹強(qiáng)勢的鏖戰(zhàn)世界,即霍布斯的弱肉強(qiáng)食原始叢林;一種是“鴿”與“鴿”弱勢的求和,即和平共處的共生;還有一種是“鷹鴿競爭”強(qiáng)弱共存的策略。鷹派實(shí)力雄厚,占據(jù)優(yōu)勢,具有進(jìn)攻性,意欲謀取利益的預(yù)期值較高。鴿派實(shí)力稍弱,處于劣勢,具有防守性,利益預(yù)期值較低。“鷹鴿博弈”如圖1。
上述得益矩陣中各個符號的意義如下:v代表雙方爭奪的利益(即水權(quán)的使用和開發(fā)),c是爭斗的損失。如果雙方都采用攻擊策略,那么雙方獲勝和失敗的概率都是1/2,因此各自期望利益都是(v-c)/2。如果雙方都采用和平策略,那么雙方能夠分享目標(biāo)利益,各得v/2單位的利益。如果和平策略遇到攻擊策略,那么采用攻擊策略者獲得v,采用和平策略收益為0。
跨國河流水權(quán)之爭中,采取鷹派的國家,將各自力主絕對有利于自己的、強(qiáng)勢的“絕對領(lǐng)土主權(quán)論”或“絕對領(lǐng)土完整論”;采取鴿派的國家,會傾向于接受“有限主權(quán)論”或“沿岸國共同體論”。

圖1 “鷹鴿博弈”(說明:圖中黑色代表沿岸國A的策略與收益,灰色代表沿岸國B的策略與收益。)
首先來看沿岸國B如何在預(yù)測沿岸國A的選擇后,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選擇。在跨國河流的競爭中,如果沿岸國A選擇主動進(jìn)攻型的鷹派策略,占據(jù)最優(yōu)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目標(biāo)利益,最大程度地開發(fā)水資源,如圖2。此時沿岸國B如果采用鷹派策略,回報(bào)為(v-c)/2;如果采用鴿派策略,回報(bào)為0。如果(v-c)/2>0,相應(yīng)地沿岸國B會采用鷹派策略硬碰硬;如果(v-c)/2<0,沿岸國B會選擇鴿派戰(zhàn)略保全自身。當(dāng)水資源非常珍貴,超出爭斗的損失時,沿岸國B將選擇鷹派策略迎戰(zhàn)沿岸國A;而當(dāng)水資源較之于國家爭斗的損失較小的情況下,沿岸國B采取鴿派策略更為經(jīng)濟(jì)有效。

圖2
相應(yīng)地,如圖3,如果沿岸國A選擇鴿派策略,此時沿岸國B如果采用鷹派策略,回報(bào)為v;如果采用鴿派策略,回報(bào)為v/2。v>v/2,所以沿岸國B會選擇鷹派戰(zhàn)略。

圖3
同樣,沿岸國A將推測沿岸國B的選擇并加以應(yīng)對。如圖4,當(dāng)沿岸國B選擇鷹派策略,沿岸國A如果選擇鷹派策略,回報(bào)為(v-c)/2;沿岸國A 如果選擇鴿派策略,回報(bào)為0。同樣需要比較(v-c)/2與0的大小。如果(v-c)/2>0,相應(yīng)地沿岸國A會采用鷹派策略硬碰硬;如果(v-c)/2<0,沿岸國A會選擇鴿派戰(zhàn)略保全自身。

圖4
如圖5,當(dāng)沿岸國B選擇鴿派策略,沿岸國A如果選擇鷹派策略,回報(bào)為v;沿岸國A 如果選擇鴿派策略,回報(bào)為v/2。同樣v>v/2,所以沿岸國A會選擇鷹派戰(zhàn)略。

圖5
依上分析,(v-c)/2是沿岸國決定策略的關(guān)鍵因素,即損失與回報(bào)的差值決定了沿岸國的決策。通常情況下戰(zhàn)爭的損失更大,即(v-c)/2<0,推斷沿岸國A和沿岸國B會采取“鷹鴿”或“鴿?jì)棥毕喾吹牟呗詠慝@得個體最大回報(bào)。假設(shè)爭奪水資源的回報(bào)大于付出的損失,沿岸國A和沿岸國B會采取“鷹鷹”策略搶奪(v-c)/2,或者斷定對方取鴿派策略,繼而取鷹派策略奪取全部資源v。
跨國河流沿岸國之間的“鷹鴿博弈”體現(xiàn)的是對利益的追逐。收益是合作與沖突與否的重大籌碼。除了“收益”,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成本”。
二、跨國河流博弈的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
在博弈論的終極實(shí)驗(yàn)里,生存就是回報(bào)[6]。
收益是分析博弈的重要參數(shù),而效用函數(shù)通常用來表示特定博弈中的收益。效用函數(shù)是個增函數(shù),即一般情況下理性博弈參與者都會追逐最大效用。但是期望效用與單純的效用函數(shù)不同之處在于個人偏好上,前者表示了對風(fēng)險(xiǎn)的態(tài)度。如果一個人僅為了得到確定性的貨幣收益,而不是具有同等期望收益的預(yù)測性回報(bào),即可稱為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式[7]。用c表示風(fēng)險(xiǎn)厭惡指數(shù),決策分析中決策者從得到收益x中獲得的效用支付是u(x)=1-e-cx[8]。厭惡風(fēng)險(xiǎn)指數(shù)越高的決策者效用支付越低,越傾向于選擇追求確定性的收入,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
跨國河流水博弈中最高風(fēng)險(xiǎn)莫過于河流的失衡,諸如水量的巨大變化、水生態(tài)被破壞以及河流的消失等。國際社會通過條約、會議、宣言、建議、標(biāo)準(zhǔn)等各種形式,持續(xù)在努力表達(dá)一種人文關(guān)懷的價(jià)值觀和道德傾向的法哲理念,即保持河流的可持續(xù)生存,保障人類的可持續(xù)生存。《赫爾辛基跨國河流利用規(guī)則》的公平合理利用,《跨國水道和國際湖泊保護(hù)和利用公約》的跨界影響,《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不引起嚴(yán)重?fù)p害原則、不同用途之間的關(guān)系原則,《21世紀(jì)水安全——海牙世界部長級會議宣言》的共同目標(biāo),以及《波恩國際淡水會議行動建議》提出的可持續(xù)分配,都是對保障基本權(quán)利的具體行動,對群體基本權(quán)利的認(rèn)可和對后代生存的憂慮*“可持續(xù)分配”首先要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然后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需求,最后是包括糧食安全在內(nèi)的經(jīng)濟(jì)方面的各種需要。“共同目標(biāo)”:為21世紀(jì)提供用水安全。這意味著確保保護(hù)和改善淡水、沿岸以及水系統(tǒng),確保促進(jìn)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政治穩(wěn)定性,確保人人都能夠得到并有能力支付足夠的安全的水,并確保易遭受影響的人群得到保護(hù)。“跨界影響”包括對人類健康和安全、植物、動物、土壤、空氣、水、氣候等影響及其相互作用,還包括改變上述因素對文化遺產(chǎn)或社會經(jīng)濟(jì)條件的影響。。
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模式。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注重的是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用以維持增長與發(fā)展,而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對生態(tài)、人和國家各個主體基本需要的保障。任何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各種環(huán)境資源,在數(shù)量、質(zhì)量、空間和時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度,每一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對外來的干擾都有一定的忍耐極限。1987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委員會提出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它要求“既滿足當(dāng)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gòu)成危害”,“人類應(yīng)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態(tài)成果的生活,公平地滿足今世及后代在發(fā)展與環(huán)境方面的需求以及求得發(fā)展的權(quán)利”。國際法院1993年蓋巴斯科夫-拉基馬洛大壩案在判決中就接受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概念[9]。國際法院的判決中指出,由于新的科學(xué)認(rèn)識和不斷增長的對人類無所顧忌開發(fā)自然的風(fēng)險(xiǎn)的認(rèn)識,新的規(guī)范和標(biāo)準(zhǔn)已經(jīng)形成,各國在策劃新的活動,或是在繼續(xù)過去的活動時,都必須考慮新規(guī)范,并對新標(biāo)準(zhǔn)給予足夠重視[10]。
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最低標(biāo)準(zhǔn),是一個權(quán)利邊界的閾值。可持續(xù)發(fā)展是基于追求發(fā)展至上的保守行動,而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源于共存亡的利益攸關(guān),防止公地悲劇的發(fā)生。水資源是一種公共性的自然資源,是關(guān)系民生、關(guān)系民族、關(guān)系人類的大事,國家及政府在處理水資源利用中無法回避民眾的基本利益訴求。
法的價(jià)值是法律作為客體對于主體——人的意義,是法律作為客體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是人關(guān)于法律的超越的絕對指向。任何法律制度的構(gòu)建,都有其基本的價(jià)值取向,即為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而進(jìn)行有關(guān)價(jià)值選擇。除了實(shí)現(xiàn)公平、正義、秩序、效益等法學(xué)價(jià)值之外,跨國河流水權(quán)的價(jià)值追求主要體現(xiàn)在保護(hù)跨國河流沿岸生態(tài)環(huán)境,供給生物,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生存,繼而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
首先,沿岸國居民有權(quán)享有“安全水”。20世紀(jì)70年代初,國際法學(xué)者雷諾·卡辛(Rene Cassin)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報(bào)告,提出要將現(xiàn)有人權(quán)原則加以擴(kuò)展,人類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潔的空氣和水中生存的權(quán)利。卡辛認(rèn)為,具體應(yīng)包括保證有足夠的飲水,純凈的空氣等,最終保證人類得以在這個星球上繼續(xù)生存。在斯德哥爾摩《人類環(huán)境宣言》中宣告:“人類有權(quán)在一種能夠過尊嚴(yán)和福利的生活環(huán)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quán)利,并且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huán)境的莊嚴(yán)責(zé)任。”
其次,沿岸國有義務(wù)保障“水安全”。在全球體系中,無論哪一個層次的行為體若要獲得水安全,其基本立場與途徑都只能是通過“互惠共建”達(dá)到“共存共優(yōu)”,這就需要國際關(guān)系任何一個層次中的“自我”與“他者”間的共同努力。從安全哲學(xué)的角度分析,理解安全內(nèi)涵的視角本身制約著安全實(shí)現(xiàn)的可能性限度。如從“威脅論”的視角把安全理解為“沒有威脅”,安全則是一種“危態(tài)對抗”式的均衡;而從“和合論”的視角把安全理解為“和合互動”,安全則將是一種“優(yōu)態(tài)共存”式的共建[11]。全球?qū)哟蔚摹吧鷳B(tài)安全”,如環(huán)境惡化(特別是污染和疾病),除了成為政治不穩(wěn)定與沖突的因素,進(jìn)而引起對主權(quán)的侵犯屬于傳統(tǒng)安全外,其他的直接影響人的健康與福利,并因?qū)Σ豢稍偕Y源的占用而導(dǎo)致生存關(guān)系緊張,則更多地涉及國家安全以外的層次[12]。
第三,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對生命權(quán)的尊重。生命權(quán)已不再停留在純粹自由法治國之下防御意義上抵制國家專斷剝奪個人生命的意味上,而是一個同時包含著如何在社會生活中維持生命及提高生命質(zhì)量意涵的概念[13]。任何一個文明社會所保障的生命權(quán),都蘊(yùn)涵著獲得食物、水、適宜的環(huán)境、教育、醫(yī)療和住所的權(quán)利。這些權(quán)利是文明社會里眾所周知的基本人權(quán),所有公民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都不能離開這些基本的人權(quán)。
第四,可持續(xù)生存理念是對波爾丁宇宙飛船理論的呼應(yīng)和對哈丁救生艇理論的駁斥。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學(xué)者波爾丁提出宇宙飛船經(jīng)濟(jì)理論,指出地球是個小宇宙飛船,飛船上的所有人都處于一個共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之中,因此人們必須改變行動,團(tuán)結(jié)自救。而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則恰恰相反,給出一個極端悲慘的模型,其中富裕國家獨(dú)自求生構(gòu)成冷冰冰的無法逃避的結(jié)論[14]。
因此,如果不以可持續(xù)生存為必然的價(jià)值取向,那么,環(huán)境、個體、國家、區(qū)域乃至全球的水安全都無法保障,何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資本。可持續(xù)生存正是跨國河流水權(quán)配置中群體權(quán)利的自治邊界。
三、納什均衡
每個沿岸國在做決策時,依據(jù)河流的特征、本國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政治外交策略、國際地位等綜合分析,趨利避害。“趨利”是追求利益,“避害”即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博弈分析中對局中人i決策問題的決策分析就是,首先確定i的主觀概率分布,以概括i關(guān)于其余局中人將使用什么策略的信念,然后為i選擇一個策略,以最大化其關(guān)于上述信念的期望支付[8]。沿岸國通過觀察并預(yù)測其他沿岸國的行為與應(yīng)對策略,做出最優(yōu)的博弈決策,達(dá)成納什均衡。
(一)沿岸國的策略組合
納什均衡定義:對于博弈G={S1,…, Sn;u1,…, un}, 如果在由每個博弈方的一個策略所組成的策略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si*,都是應(yīng)對其他博弈方策略組合(s1*,…,si-1*,si+1*,…,sn*)的最佳策略,也即ui(s1*,…,si-1*,si+1*,…,sn*)≥ui(s1*,…,si-1*,sij,si+1*,…,sn*)對任意sij∈Si都成立,則稱(s1*,…,sn*)為博弈G的一個“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5]。
基于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跨國河流水博弈中的局中人任一博弈方i(沿岸國)有如下幾種決策:S1={單邊開發(fā),自行管理};S2={相鄰沿岸國簽訂雙邊協(xié)議};S3={多個沿岸國簽訂河流共同管理協(xié)議或成立次區(qū)域共同體};S4={所有沿岸國簽訂河流共同管理協(xié)議或成立河流管理委員會};S5={沿岸國與第三方機(jī)構(gòu)簽訂協(xié)議};S6={以國際社會公約為管理規(guī)范}。
第一,單邊開發(fā)、自行管理通常追逐的是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但其存在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即河流沿岸國之間的武裝沖突。中東國家的用水沖突不僅困擾了中東地區(qū),對于整個國際社會都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和平難題。
第二,相鄰沿岸國簽訂雙邊條約是條約數(shù)量占比最高的一部分,如1909年美加邊界水條約,1960年印巴印度河條約,中國和蒙古國于1994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蒙古國人民政府關(guān)于保護(hù)和利用邊界水協(xié)議》,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于1994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府關(guān)于共同利用和保護(hù)跨界河流的合作協(xié)議》,中國與俄羅斯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lián)邦政府環(huán)境保護(hù)合作協(xié)定》等。
第三,多個沿岸國簽訂多邊條約,包括多個但不是全部沿岸國的多國條約。如1995年,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在泰國清萊成立湄公河委員會,并簽訂《湄公河流域可持續(xù)發(fā)展合作協(xié)定》(5/6),湄公河的源頭國中國并沒有包括在內(nèi)。1948年,多瑙河流域各國成立多瑙河委員會,簽訂《多瑙河航行制度公約》(7/19),并于1994年簽訂《多瑙河保護(hù)與可持續(xù)利用合作公約》。
第四,另外一種多邊條約包含所有沿岸國,形成沿岸國共同體,如1969年,銀河流域五國: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為利用和管理銀河流域水資源簽訂《銀河流域條約》;1999年,萊茵河流域各國成立萊茵河國際委員會,簽訂《萊茵河保護(hù)公約》; 1978年,亞馬遜河流域各國簽訂《亞馬遜河合作條約》。
第五,沿岸國與第三方機(jī)構(gòu)簽訂協(xié)議,如1960年《印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和國際復(fù)興開發(fā)銀行關(guān)于印度河的水條約》。
第六,國際社會致力于制定合理公正的公約為管理規(guī)范。如1921年41個國家(含中國)共同締結(jié)了《國際性可航水道制度公約及規(guī)約》。1992年,歐經(jīng)委通過了《關(guān)于跨界水道與國際湖泊保護(hù)和使用的公約》(也稱赫爾辛基公約)[15]。如今,赫爾辛基公約成為跨境水資源領(lǐng)域使用范圍最廣、最為有效、最有影響力的區(qū)域公約,并朝著國際性的公約邁進(jìn)。1997年,在聯(lián)合國第51屆會議上,聯(lián)合國大會以第51/229號決議通過了《聯(lián)合國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在公約表決過程中,103國投票贊成,27國棄權(quán),3國(中國、布隆迪和土耳其)投票反對。但公約的締約方數(shù)量到目前為止仍未達(dá)到35個締約成員,按照公約第36條的規(guī)定,該公約暫未生效[16]。
(二)沿岸國的策略選擇
跨國河流中的沿岸國博弈過程,類似蜈蚣博弈(如圖6),屬于多階段的序貫博弈*蜈蚣博弈是羅森泰爾(1981)提出的一個動態(tài)博弈問題,指給予兩個博弈者各1美元,由博弈一方開始選擇,他們可以輪流選擇停止或者繼續(xù)。如果博弈一方選擇繼續(xù),將從該博弈方那里拿走1美元,對手將獲得2美元。如果博弈一方選擇停止,他們雙方將獲得當(dāng)時各自所有的。如果雙方博弈所得達(dá)到100美元,游戲結(jié)束。。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核心方法是逆向歸納法,即從最后一個子博弈反推。沿岸國B最后一步選擇合作,回報(bào)為100;選擇停止,回報(bào)為101。101>100,沿岸國B將選擇停止。往上看,沿岸國A如果選擇合作,回報(bào)為98;選擇停止,回報(bào)為99。99>98,沿岸國A將選擇停止。依次類推,最后推到第一個子博弈,沿岸國A在預(yù)測沿岸國B在下一步必定會選擇停止以獲得更高回報(bào)的前提下,必然選擇停止,納什均衡為(停止合作,停止合作),回報(bào)為(1, 1)。
逆向歸納法要求博弈方具有完全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要求博弈方對博弈的所有細(xì)節(jié)、所有回報(bào)都完全清楚;且相互有完全的信任,確定對方一定會如何選擇。逆向歸納法適用于實(shí)驗(yàn)室里的研究,要求博弈方完全理性、且博弈回合的預(yù)測付出和回報(bào)都清晰無誤,與實(shí)證分析的結(jié)果偏差較大,但提供了研究的思路。
針對過去50年間跨國河流的合作與沖突事件的情況,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xué)匯編了一個數(shù)據(jù)庫。據(jù)該數(shù)據(jù)庫記載,過去50年來,有1228起合作事件,同時有507起沖突事件,而這些爭端中又有超過2/3仍限于口頭上的交惡,只有37起由水資源引發(fā)的國家間暴力沖突(除了7起外均發(fā)生在中東地區(qū)),而同期各國關(guān)于水資源條約的談判超過200個[17]。
根據(jù)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xué)的數(shù)據(jù)顯示,合作事件/沖突事件的比例為1228/507=2.42,合作事件/暴力沖突事件的比例為1228/37=33.18,合作的概率達(dá)到70.71%,暴力沖突事件的概率僅為2.92%。沿岸國并沒有全部選擇(100,100)的雙贏合作,或是逆推法最理性的將合作止于初始(1,1)收益階段。因?yàn)楦餮匕秶黧w在博弈策略選擇時除了博弈模型,還必須考慮如下幾點(diǎn)。
首先,博弈方具有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博弈論關(guān)于人的理性假設(sh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們決策行為的根本目標(biāo);二是他們追求目標(biāo)的能力。完全理性的假設(shè)意味著每個博弈方在所面臨的環(huán)境中都會最大化自身的利益[6]。但是博弈雙方在博弈過程中相互依賴和影響作用大,個別或部分博弈方的理性能力有局限性,甚至只要博弈方相互對對方的理性能力存在質(zhì)疑就會使博弈的結(jié)果出現(xiàn)偏移。
其次,博弈各方都被潛在利益驅(qū)動。對于沿岸國A來說,一開始的1份回報(bào)不是一個很大的風(fēng)險(xiǎn),而如果合作就能獲得潛在的99份得益顯然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雙方在一開始都傾向于選擇合作,希望將合作延續(xù)下去,都是基于對潛在得益的投機(jī)行為。

圖6
最后,合作的精神和相互的信心促進(jìn)合作。如果沿岸國A篤定堅(jiān)信沿岸國B沒有合作精神,那么堅(jiān)決地選擇停止合作是最佳策略。但是如果沿岸國A想要試探合作的可能性,只有選擇合作,才能了解沿岸國B的合作精神。在第一階段沿岸國A選擇合作后,沿岸國B理解了沿岸國A的合作信號,將進(jìn)一步選擇合作,從而加強(qiáng)了相互合作的信心。博弈一旦出現(xiàn)合作的良好開端,合作的可能性將增大。據(jù)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證實(shí)的數(shù)據(jù),自1814年起,通過國際談判產(chǎn)生了305個國際河流水資源管理、防洪、水能開發(fā)等消耗性或非消耗性用水分配等非航行水利用方面的條約,其中全文涉及水本身的條約有149個[18]。但是隨著潛在利益空間變小,逆向歸納法和理性思維再度出現(xiàn)效果,從而合作停止。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跨國河流全球國際公約規(guī)范難以達(dá)成共識的現(xiàn)實(shí)。沿岸國的策略組合排列比例中,出現(xiàn)兩頭小、中間大的現(xiàn)象。即雙邊、多邊條約居多,而單邊不合作或者全球合作則幾率較小。
小結(jié):跨國河流水博弈既有水沖突,又有水合作。沿岸國采取鷹策略或鴿策略,都是基于理性的考慮,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獲取利益,做出最優(yōu)決策。跨國河流水博弈,由單邊不合作,到雙邊合作、多邊合作,然后形成沿岸國共同體,最后實(shí)現(xiàn)全球共贏的國際規(guī)范規(guī)約,這是一個漸進(jìn)的合作步驟,也是一個構(gòu)想的進(jìn)階。從博弈論的現(xiàn)有研究成果來看,跨國河流水資源引發(fā)極端戰(zhàn)爭的幾率較小,國際公約規(guī)范的成功概率短時間內(nèi)也難以達(dá)成,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jìn)展,現(xiàn)代國家治理理性能力增強(qiáng)的情況下,雙邊和多邊條約將是減少水沖突與促進(jìn)水合作的重要渠道。
參考文獻(xiàn):
[1] White G. A perspective of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57, 22: 186.
[2]何艷梅. 國際水資源利用和保護(hù)領(lǐng)域的法律理論與實(shí)踐[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62-63.
[3]陶蕾. 跨國河流水權(quán)概念辨析[J]. 水利經(jīng)濟(jì), 2010(6): 29.
[4]李杰豪. 論“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法之遵守—以利益分析為基點(diǎn)[J]. 當(dāng)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07(6): 97.
[5]范如國. 博弈論[M]. 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 2012: 290, 39- 40, 25.
[6]湯姆·齊格弗里德. 納什均衡與博弈論:納什博弈論及對自然法則的研究[M]. 洪雷, 陳瑋, 彭工譯. 北京:化學(xué)工業(yè)出版社, 2014: 89.
[7]喬爾·沃森. 策略博弈論導(dǎo)論[M]. 費(fèi)方域, 賴丹馨等譯.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3: 246- 249.
[8]羅杰·B·邁爾森. 博弈論:矛盾沖突分析[M]. 于寅, 費(fèi)劍平譯. 中國人民出版社, 2015: 3, 79.
[9] ICJ. Case Concerning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 v. Slovakia)[OL].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code=hs&case=92&k=8d, 2015-04-10.
[10] Sands P.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2.
[11] 余瀟楓. 安全哲學(xué)新理念“優(yōu)態(tài)共存”[J]. 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 2005(2): 5-12.
[12] Terriff T. Security studies toda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118.
[13] 鄭賢君. 生命權(quán)的新概念[J]. 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科版), 2006(5): 87- 93.
[14] 李風(fēng)華. 我們能否共同求生——對哈丁救生艇理論的邏輯批判[J]. 哲學(xué)動態(tài), 2011(3): 73-80.
[15] UNEC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 31 ILM 1312 (1992) [OL].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water/pdf/watercon.pdf, 2015-12-01.
[16] UNGA. Resolution 51/229, 8 July 1997 [OL].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51/229, 2015-12-01.
[17]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jì)劃署. 2006年人類發(fā)展報(bào)告, 2006: 221 [OL].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_2006_cn_complete.pdf, 2015-12-01.
[18] WOLF A T. Criteria for equitable allocations: The heart of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lict [J]. Natural Resource Forum, 23(1), 1999: 3-30.
(本文責(zé)編:辛城)
收稿日期:2016-01-21修回日期:2016-04-28
基金項(xiàng)目:湖南省法學(xué)一級重點(diǎn)學(xué)科項(xiàng)目;201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基金資助項(xiàng)目“跨國河流水權(quán)利用的法律制度研究”(CX2013B168)。
作者簡介:蔣新苗(1964-),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長江學(xué)者”特聘教授。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6-0001-07
Game Theory Analysis 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Big Rivers
JIANG Xin-miao,GUO Li-xia
(LawSchool,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06,China)
Abstract:Transboundary River is endowed with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n account of the geopolitical feature.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iver hold different standpoints on affairs such as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bilateral cooperation 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so the forth.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undertake a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countries’ strategies-selection on the basis of game theory in hawk-dove game theory, avoiding risk and Nash Equilibrium, hoping to provide as reference for better cooperation of global water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nsboundary river; game theory; avoiding risk; Nash Equilibr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