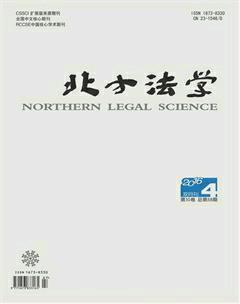都市社會語境下法治認同模式的構想
許小亮
摘 要:城鎮化進程的全面啟動與依法治國戰略的全面推進使得都市社會中的法治認同成為一個重要論題。一方面,都市社會的發展消解了傳統法治認同模式賴以存立的共同體,另一方面都市化的進程又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并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進而構成了一種新型的共同體——媒介型共同體。媒介型共同體以異質性的不斷生成為其正當性基礎,以多重空間分配與構造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傳統的依托于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模式,形成了一種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體。都市社會中的法治認同要求利他主義的都市法律主體,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動結構,以空間分配促進都市法律主體對于都市法治的認同,最終指向都市法治的實現。
關鍵詞:都市社會 法治認同 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4-0033-09
當下中國社會已經全面開啟城鎮化的進程,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城鎮化對于人們的居住環境、行為方式、意識狀況甚至是生活關系本身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城鎮化的過程不僅僅是在物質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上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更是在精神氣質上重塑了人們的意識狀況,進而從本質上改變了人們對于自身生活關系的固有認知。與此同時,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推進,法治逐漸成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必須要加以貫徹的一種對于新型社會生活關系的治理模式。法治中國的建設與城市中國的建設在此相遇。
如何在城鎮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使得人們增進對于法治這一治理模式的認同,成為擺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這不僅需要我們從制度和意識的層面去重新理解傳統的“城市”概念所指涉的范圍,更需要我們去重新構想一種不同于法治認同所立基的共同體類型。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同時構想一種全新的城市概念與法治認同模式,并通過將這兩者進行概念和現實上的勾連契合形成契合于都市社會的法治認同模式,將都市中國與法治中國這兩大國家建設戰略在現實路徑上進行融合。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從三個方面考察都市社會語境下的法治認同模式的塑造問題:一是揭示出都市化過程所造就的社會的轉型狀況,最終指向一種都市社會型態;二是揭示出都市社會的本質及其對傳統法治認同模式的挑戰;三是將都市社會構想成一種新型的共同體類型,這一共同體類型既能夠在都市社會的語境下為法治認同的模式提供一種不同于傳統法治認同模式的替代性選擇,又能夠真實地契合于都市社會的制度構造與精神氣質。
一、都市化過程與都市社會的形成
如果我們承認,城鎮化成果所帶的來不僅僅是一座座城市的涌現,更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形態的出現,那么我們在從制度和意識層面討論城鎮化所帶來的影響時就不得不區分出一種可以在不同意義上表征這一新型意識狀況和生活關系的概念。對此,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勒弗斐爾對“城市(city)與都市(urban)”概念的二分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勒弗斐爾認為,所謂“城市”,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觀察和感受到的當下的物質性的實體,譬如我們說某某建筑是某某“城市”的地標性建筑,某某“城市”對于自身道路和居住環境的改善等等。而所謂“都市”,他所意指的是由思想本身所建構或重構的基于此種物質性實體而發生的社會生活關系,譬如我們說消費型生活關系的形成等等。當然,“都市”概念不能脫離“城市”概念而獨立自存,其并非是一個純然的概念性建構,而是基于“城市”自身的發展而形成的。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Blackwelll Publishers,1996, p103 由此可見,都市概念既容納了城市的物質性面向,又引入人們對于這種不斷擴展和生成的物質性面向的思想建構或重構的生活關系維度。這既為新的生活形態提供了客體,又同時塑造了這一生活形態的主體。
但是,這種區分也使得我們意識到,都市的形成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實體型的“城市”發展和壯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我們擁有了“城市”,我們就獲得了“都市的生活”,進而形成“都市社會”。所以,從制度構造與意識生成的層面去討論問題,我們更愿意用都市化這一概念來代替城鎮化的概念。當然,都市社會只有在城鎮化過程完結之后才會形成,而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形態乃是一個從非都市的社會轉向都市社會的轉型社會。因此,我們有必要去考察這一轉型的進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切了解都市社會的形成過程,進而去構想一種不同于傳統社會形態的適合于都市社會的法治認同模式。
對于都市化的進程,我們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路徑加以考察:一種是歷史的路徑,即對于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包括其精神氣質、建筑風格和城市治理的模式的起源與演變,通過歷史的資料進行經驗性研究,從而為我們對于“都市社會”所可能關涉到的領域與層次有所認知和把握;一種是哲學的路徑,即我們不去巨細無遺地考察都市化的歷史進程,而只是經由對歷史的哲學式的思考——也即,我們需要在都市化完全不存在和完全都市化兩個時空點上,經由對歷史的哲學式總結——揭示出都市化的基本內涵及其所可能包含的領域與層次。
對于本文而言,筆者更傾向于哲學式的考察方式,理由有三:首先,歷史的考察最多告訴我們有關“城市”的總體性知識,并不能夠真正揭示出“都市”生活關系的本質與內涵;其次,歷史的考察往往流于細節,難以揭示出某一個時代的“城市”背后的“都市精神”是什么,而這正構成我們對于“都市社會”所可能和應該有的領域和層次的把握,因為從歷史哲學的視角來看,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城市”雖然可能消亡,但由此種“城市”所表征出來的“都市精神”卻不曾消亡,而是被都市化的過程所承襲,成為完全都市化過程之后沉淀在“都市社會”的基本生活關系構造中的要素;再者,純然歷史的考察有可能使我們陷入“鄉土社會—都市社會”的二元對立之中,將都市化進程的展開視為是傳統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進而慨嘆某種文明或者說某一個階層——譬如說農民——的終結。但是,這種歷史考察的方式所忽略掉的是,都市化進程本身并不意味著某種文明或階層的消亡,這種文明或階層有可能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存在于都市社會之中。由此,我們可以跳出上述的二元對立,兩種社會形態的關系不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區別只在于,哪種社會形態的“精神氣質”占據主導。正如孟德拉斯在考察都市化過程中農業社會和農民地位的變遷之后所說的那樣,“認為鄉村社會和鄉下人將來會變得和大城市的情況一樣,這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幻想。每個鄉村社會都是根據自己的創造力來實現現代化,同時也獲得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這些共同的特征抹去了過去的獨特性。”[法]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頁。
從歷史哲學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將都市化的歷程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農業文明下的都市化進程;二是工業文明下的都市化進程;三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后都市化進程。關于都市化進程的起源與發展,可參見Michael Paciniem eds, The 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Routledge, 2001,pp5—221 其中,在農業文明下的都市化進程主要表征為兩種都市化形態:政治形態和商業形態。政治的城市起源于古典的城邦政治,展現了都市生活所蘊含的基本要素:權力、階層分化、檔案、法律、稅收與土地的規劃使用,如此等等。而商業的城市則為都市化生活添加了商業、藝術和文化的要素。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pp8—11 然而,在工業文明下的都市化進程則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與路徑,都市成為生產與消費的核心,進而成為一種凌駕于經濟、政治與法律結構之上的一種“超級結構(superstructure)”。前引④,p15 依賴于都市實體在工業文明下所具有的“超級結構”之性質,無論是作為物質或制度而呈現的“城市”或者是作為生活關系或精神氣質而呈現的“都市”,都呈現出一種“聚集—擴張”的發展趨勢:“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呈現出集聚效應,從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生產資源;而“都市”的生活關系與都市的精神氣質,則飛快地向外部擴展。“城市”的聚集效應越強,“都市”的擴展效應就越廣且越長久。也正是依賴于這一“超級結構”,使得原本依賴于工業化進程的都市化進程逐漸獲得了主導性的地位,進入我們所謂的后都市化時代:在后都市化的時代,并不是工業化帶動都市化,恰恰相反,是都市化吸納了工業化。正因為如此,后都市化時代對于城市治理和都市發展的研究本身就容納了工業化的問題,與此同時,也容納了全球化、地方化和私人化的問題,并最終匯集于“人本的都市”的層面,從而豐富了都市社會中法治認同所可能關涉的內容和層次。
從人本主義的視角來看,都市社會的所有成就最終都不過是為了每一個個體能夠實現愜意的都市化生活。因此,都市社會成熟的標志乃在于所有的一切都從屬于“都市化的寓居(the urban to habiting)”。其是否存在,從根本上構成人們對于都市內部的法律治理與法律運行模式之認同是否能夠存續的前提。但事實上,我們從都市化過程中所看到的階層、財富、興趣、認知的不斷分化和主體高度異質性的不斷呈現,以及都市生活所帶來的高度消費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生活樣式都在根本上使得這種“都市化的寓居”變成一種有待實現的正義理念,而非切實可感的日常都市生活。這就對傳統論域中的法治認同模式從根本上構成了挑戰。因為我們通常所熟知的法治認同模式是以特定類型的共同體為基礎,強調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社會分化始終不會突破社會團結,主體的異質性始終受限于其同質性的訴求。但是所有這些要素在都市社會的情境中都不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基于都市社會自身的性質去構造一種新型的共同體模式,并在這一共同體模式的基礎上重新構想并設計法治認同的可能情形。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在都市社會的語境下實現都市化與法治化的合一,最終形成都市法治的理想生活情景。而要實現這一理想,我們必須首先明了都市社會究竟有何根本的特質?這些根本性的特質對于傳統法治認同的模式形成了何種挑戰?
二、都市社會對傳統法治認同模式的挑戰
對都市社會的本質能否獲得正確的理解,取決于我們用什么樣的視角去觀察都市。如果我們將都市視為一個與鄉村對立的有待我們去認識和發現的實體,那么,我們對于都市社會的認知大體上所能夠采納的視角就是描述的和靜止的,也即我們能夠通過對于現實中城市的規劃和建設、城市的經濟發展、犯罪率、宜居性來認知都市社會。如此一來,我們通過一系列的數據所獲得的結論不外乎是將都市社會的本質理解為陌生人社會、消費社會等等諸如此類的社會型態。而在這一認知框架下所獲得的有關都市社會與法治認同模式之間的勾連與契合事實上存在著諸種錯位和誤解。如都市社會的陌生人特質有助于人們樹立法治意識,有助于培養人們對于普遍規則的服從意識,進而增進都市中的居民對于法治治理模式認同。現有的對于都市社會與法治社會之間的高度契合性的結論基本上是在這一認知前提下得出的。在此基礎上去討論法治認同的模式,我們不過就是將原本我們心中所構想的一種普遍的法治認同模式置放在都市社會中進行考察,這樣的研究所能夠獲得的僅僅是法治認同在都市社會中的呈現形態,是“法治認同的都市表達”,其或許會與“法治認同的鄉村表達”對應,但絕對不會是我們所希冀的“都市社會的法治認同”。
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上述的視角只是觸及了都市社會的表層現象,并沒有揭示出都市社會的本質性要素。勒弗斐爾認為,由于都市社會包含了各種各樣復雜的生產與交換關系,海量的信息以及歧異的符號和意義表征,因此,很難有一門特殊的科學可以去把握作為一個整體的都市社會,因而應將都市社會的研究交由各個學科來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且,由于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全面觸及都市社會的本質,所以任何一個學科的結論相對于其他學科都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前引④,pp60—64 從方法論的視角來看,勒弗斐爾堵死了從外在視角研究都市社會進而獲得都市社會的本質的可能性,但他自己卻并沒有嘗試從內在視角去研究都市社會,也即從都市社會本身去研究其本質。如何以內部去認知都市社會呢?筆者認為可以借助尼克拉斯·盧曼的理論。
隨著都市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我們可以預想,都市社會將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全社會”,因此具有普遍性與多重復雜性的面向。要對都市社會進行研究,必須擺脫傳統社會理論的困境,從都市社會自身演化和發展的邏輯去認識其本質。正是基于此,依照盧曼所強調的認知社會整體的邏輯,我們必須以一種“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態度將“都市社會”視為一個可以“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Niklas Luhmann, Theory of Society, Volume 1, translated by Rhod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4 由于都市社會的復雜性和普遍性非常契合盧曼對于社會本身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的預設,因此,都市社會內部諸多復雜系統之間的“自我指涉”必定是同時運行并相互影響的,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整體的都市社會對于自己的自我指涉與其內部的多元性要素之間的“自我指涉”是同步的,由此,對都市社會的觀察就必須基于“多重聚合情境(polycontextual)”來認知。前引⑦,p46
從盧曼的社會理論所提供的視角對都市社會的本質進行認識,我們必然會得出如下的結論:都市社會的本質在于分化,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都市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和分裂,所有的城市都是“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在諸多城市研究者看來,分化或者說分裂恰恰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弊病,是必須予以克服和消除的,現代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也是以此為鵠的。這一觀念的集中闡述,參見Richard Scholar eds, Divided C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但是,這種觀察本身只是表面化的,其并沒有認識到,正是由于分化和分裂本身使得都市社會得以以一種多元化和異質性的特質呈現,與此同時,這種多元和異質性又能夠構成我們去認識都市自身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們才能夠在“多重聚合情境”中來認知都市,也正是基于都市本身,我們才能夠體認多元和異質的要素是如何在都市生活中被決定、指示、認知以及如何行動的。由此,我們更可以瞥見“城市”與“都市”的基本不同:“城市”是多,是質料,而“都市”是一,是純粹的形式。如盧曼所指出的,這一意義上的“形式”乃是由某物或其他任何某物組成,由某物及其語境組成,甚至由價值與反價值組成,一切事物皆是構成這一形式的要素,一切事物皆緣起于這一形式。前引⑦,p30 勒弗斐爾雖然沒有運用盧曼的方法,但卻與盧曼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認為都市最終在多元和異質的狀況下會形成一個純粹的“都市形式(urban form)”,并進而指出了都市形式與多元的構成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形式的存在使得理性分析成為可能;形式乃是研究的最高階段;可以基于形式對其內部的要素進行持續地批判和自我批判。前引④,p136
由此,都市社會的本質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在形式的層面,都市社會的本質乃是純粹的形式。但是這種純粹的形式不同于我們通常所謂的形式主義,其并非空洞無物的形式,而是一切都市要素得以匯聚的場所,并且是所有都市生活之魅力的中心展現:“因此,都市是純粹形式:一個相遇、聚集,同步性的場所。此種形式沒有特殊的內容,但卻是所有魅力與生活的中心。它是一種抽象,但不同于形而上學的實體,都市是與實踐相關聯的具體抽象”。前引④,pp118—119 在質料或者要素的層面,都市的本質是分化、沖突與分裂。具體來說,這種分化、沖突與分裂體現在四個層面: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空間的。政治的沖突與分化關注于都市化進程中的階級分化以及都市治理和都市演化的正當性問題;經濟的沖突與分化主要表現為都市化過程中的兩極分化和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問題;文化沖突與分化主要表現為異質性的身份認同和文化主張之間的沖突;空間性的分化和沖突是都市社會中的一種獨特性的分化和沖突,這種沖突所呈現的是都市社會中相鄰的區域之間的內在關聯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領域所引發的沖突。并且,對于這些沖突和分化的解決也并非是簡單地采用包容性的政策、計劃或法律就能夠達到的。在很多時候,都市社會中的包容性政策、計劃和法律反而有可能導致雙方更加極端地對立。Frank Gaffikin, Mike Morrissey, Planning in Divided Cities: Collaborative Shaping of Contested Space, Wiley-Blackwell, 2011,pp4,21 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的法治認同模式所提供的權利概念和正義理論并不能夠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主要表現在傳統法治認同模式所提供的法律形式不能夠有效地對應都市形式,與此同時,傳統法治理論中對法的作用和功能的自我設定也不能夠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空間領域內有效應對都市社會在質和量上的高度分化。
具體來說,傳統的法律形式是依賴于法律所指涉和治理的社會生活質料而存在的,其并不能夠自我指涉和自我生產。一個規則或原則要能夠成為法律,其要么訴諸這種規則或原則的內在或外在的道德正確性,要么訴諸于法律主體的先天的規范性思維范疇或是法律共同體整體的實踐。相關論述可參閱[日]長谷部恭男:《法律是什么?法哲學的思辨旅程》,郭怡清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41頁。 因此,經典法治認同模式中的法律形式自身是無法成為一切對于法律的認同和遵守的根源的,其最多向法律主體及其所指涉與治理的社會質料呈現其在邏輯和體系上的一致性,而真正能夠促成認同生成并進一步塑造共同體之認同和團結的,恰恰是外在于這一體系的價值共識或社會團結本身。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都市社會的本質在其作為一切來源與基礎的都市形式,而其質料本身則是不斷分化與分裂的。因此,如果我們固守傳統的法律形式的理論,就根本無法在都市社會中尋找到價值共識與社會團結的可能。
同樣,在都市社會的各領域中,我們揭示出沖突與分裂乃是一種常態,這就與傳統法治認同模式中對法的功能與作用的定位有著根本的沖突。在傳統的法治認同模式中,無論是西方法律文化或者其他法律文化,其對法律的功能與作用的界定都是圍繞著糾紛之解決而展開的,所謂通過法律的治理,不過是圍繞著糾紛解決所形成的爭議識別、程序運行和制度構造的法律機制的形成過程。相關的闡述,可參見Lawrence M Frideman, Rogelio Perez-Perdomo,and Manuel AGomez eds, Law in Many Societies, Stanf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71—175 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共同體的基于這種法律機制所形成的共識與認同的狀態,其以同質性的權利與正義觀念為基本特征,以主體間共享的價值理念為引導,以共同體基本物品的公平分配為基礎。但是,都市社會的存在前提卻是承認分化與分裂的正當性,只有通過分裂與分化,都市的多元性和異質性才會在都市中不斷地生成與呈現。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重新構想一種能夠容納并不斷激發異質性的共同體型態,只有基于此種新型的、契合于都市生活的共同體,新的法治認同模式才能夠得以形成。這種新型的共同體,就是媒介型共同體。而對此種共同體的揭示需從對都市社會的諸層次之描述與分析開始。
三、都市社會的層次與新型法治認同模式之構造
當我們慮及都市社會的層次時,所關注的乃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促成都市社會之形成與發展的力量、權力和權利的層次,我們將這一層次稱為都市社會的外在層次;二是城市內部的布局或者說某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對于都市生活的意義層次,我們將這一層次稱為都市社會的內在層次。
就外在層次而言,我們所關注的乃在于某種權力或權利對于作為整體的都市社會之形式的設定,也即對于都市社會的整體結構的設定。在當下的社會生活關系中,能夠從總體上關涉到都市形式與整體結構之設定的無非是政治的權力和資本的權利。只有依據特定的政治權力,都市化作為一種政治構想與政治策略才能夠得到切實的推行。更為重要的是,只有依據這種政治權力,都市化進程中所涉及到的人口遷移、資源配置、勞動分工,甚至于都市的規模、建筑、交通與各個城市所應該具有屬于自身的獨特精神氣質才能夠得以落實。對此,有兩個很典型的例證可以說明。一是歐盟在九個歐洲城市所實行的“城市發展規劃(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這一規劃主要從三個面向和四個層次上設計歐洲的都市化發展路徑。三個面向主要包括設計、建筑和商業化;四個層次主要包括世界城市、歐洲城市、大城鎮和小城鎮。其中目標是把鹿特丹和倫敦在建筑面向上打造為世界城市,把柏林打造成設計面向上的歐洲城市,把布魯塞爾打造成商業化的歐洲城市。二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于“人本都市”的基本構想。這樣一種對于都市發展的整體規劃,對于都市構建其時間與空間關系,更甚者對于其社會關系都有著根本的形塑。由此更可以佐證上文所言的純粹的都市形式并非形而上學的抽象,而是一種與政治權力的實踐與構想緊密相連的具體抽象。政治權力對于都市化進程及其目標的規劃深刻影響了都市形式的形成及其可容納的質料。就此而言,都市形式的邊界及其所可能形成的物質、社會和話語空間都受到政治權力的設定與規制。從這個視角看,外在層次的都市社會所折射出的乃是“政治權力的幾何學”。參見DMassey, Politics of Space/Time, New Left Review, Vol196, 1992,pp65—84
與此同時,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推動下的全球化浪潮也深刻影響著都市化的發展。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訴求就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通。資本的自由流通帶動了人力、資源與技術的自由流動,因此,自由流通的權利就變得相當重要。正是在這一情境下,有很多城市的發展及其精神氣質的形成并非源于政治權力的規劃,而是基于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通權利使然。由此而形成的三個最為典型的世界城市——紐約、東京和倫敦——即屬其例。只有在自由流通的情境中,全球生產體系的安排和全球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全球金融資本的運作才有可能塑造出此種城市類型,而這恰恰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實踐型態。參見Saskia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p 323—325. 當然,此處的自由流動不僅僅包含“城市”概念意義上的物質性要素,還包括“都市”概念意義上的精神氣質要素。人們經由自由流動本身所能夠感受到的不同城市之間的氣質使得“世界主義”逐漸成為都市社會的主流氣質,也即是說,人們越來越多地感受到自己不再屬于某個特定的共同體,而是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往返流轉。由此所推動的都市化進程在價值與理念的層面更具意義。Daniel ABell and Avner de-Shalit, 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8
如果說外在層次關注的是作為整體的城市形式,那么內在層次則關注于城市內部結構的媒介功能以及私人在城市中的“寓居(habiting)”狀況。就城市的內部構造作為一種聯接媒介的功能來說,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的關系形成過程來加以考察:一是城市自身在整個國家體系中所具有的“中間集團”地位,這深刻地影響到傳統的“國家—公民”關系;二是城市經由對內部構造中的公共空間的形塑來設定城市及其“居民”的關系;三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個個體經由城市所提供的基本物質和精神生活媒介而形成的彼此之間的人際交往關系。由此,城市經由其內部結構的規劃與設定就在“公民—居民—普通人”這三個維度上起到媒介的功能。在公民的層面,城市或者說都市能夠經由其媒介形成一種獨特的共同體型態,因而其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態;在居民的層面,城市內部的街區、公共建筑等所構筑的公共空間則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或關系形態;在普通人層面,城市或者說都市的媒介功能不僅塑造了普通人的想象力,也使得其自身從一種特定的方式被想象。
就城市本身作為一個“中間集團”而起到溝通與聯接“國家—公民”之功能的層面來看,筆者認為,城市的媒介功能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經由其物質、制度和精神的構建,形成了一種與傳統的“鄉土社會”和現代“民族國家”視域內的“共同體”型態都迥然有異的新型共同體。為了描述這一新型共同體的特質,日本學者中村浩爾從“同質性—異質性”以及“主體化—客體化”兩個相互對立的范疇來對共同體進行“理想型”的描述與構建。經由這兩對范疇的構建,得出四種類型的共同體形態:埋沒型共同體(同質性和客體化的程度高)、一體型共同體(同質性程度和主體化程度高)、集列型共同體(異質性和客體化程度高)以及媒介型共同體(異質性和主體化程度較高)。在這四種共同體中,媒介型共同體是都市社會的理想狀態。參見[日]中村浩爾:《都市中間集団と政治哲學(運動)》,載日本法哲學會編:《都市と法哲學(法哲學年報1999)》,有斐閣2000年版,第46—47頁。 依據此一分類,我們可以將傳統的“鄉土社會”歸為“埋沒型共同體”,都市化未完結的民族國家的社會型態依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殊異可歸為“一體型共同體”和“集列型共同體”,而在都市化發達或完結的情形下,我們可以將都市社會中聯接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媒介稱之為“媒介型共同體”。這種“媒介型共同體”的形成深刻影響著我們對“國家—公民”關系的認知。在傳統的“國家—公民”關系中,人的自利性乃是思考的原點:無論是自由主義的公民觀對于自利性的肯認抑或是社群主義公民觀對于自利性的摒棄都是以自利性的這一基本預設展開其邏輯論述的。但是,基于“媒介型共同體”的觀念為思考“國家—公民”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依照通常的觀念,主體化的程度越高,同質性的程度也應越高,否則就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重疊共識”觀念,以維系共同體的存在與穩定。正如羅爾斯所強調指出的,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穩定性有賴于所有自由且平等的公民都被視為是理性且合理的這一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參見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140—144 但在“媒介型共同體”中,異質性和主體化程度的雙高現象卻能夠并存。這說明在“媒介型的共同體”中,自利性并非被簡單地否定或接受,而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加以轉化:“不是通過自利的人的原初自我否定,而是通過共同社會之創造,將自利的人升華至自由的、主體的人。”前引B19,第47頁。 也就是說,在都市社會中,異質性的存在及其正當地位不是通過消極意義上的寬容而得以保留的,而是經由自由的、主體性的人的利他主義實踐而加以促進和形成的。也因此,利他主義成為都市法治認同構想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這與傳統法治認同模式有著根本的歧異。
對于城市的居民來說,城市中的公共空間的塑造以及自身所生活的社區構成了其“寓居”的基本場域。必須指出,“寓居(habiting)”與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謂的“居住(habitat)”應有所區別。具體而言,當我們說在都市化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有獲得在都市中生活的權利時,我們所指的不僅僅是其能夠獲得居住與生活的空間,享有多元化生活的可能以及能夠獲得都市化過程所帶來的基本的物質和精神利益,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其透過這種新型的都市權利,能夠使得都市的居民生活于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之中。由此,我們將回到“寓居”問題的本質,即真正的“寓居”除了在與他者的相互關系中生活外,別無其他。而近代以來主流的都市化觀念恰恰用“居住”的概念徹底驅逐了古老的“寓居”概念,我們所關心的乃是住房、公共服務、教育、醫療,并將之視為是“人本主義都市”的最為重要的要素,但卻遺忘了“寓居”的本質乃是在此處逗留之,生活之,照料之,關心之,操勞之。在人及其本質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東西能夠成為我們可“寓居”的場所。前引④,pp81—82;[日]名和田是彥:《都市と領域的秩序》,載日本法哲學會編:《都市と法哲學(法哲學年報1999)》,有斐閣2000年版,第79—80頁。 但是現實的都市化進程卻促使我們越來越關注于某種“居住”秩序的形成與獲得,并逐漸相信“居住”的邏輯乃是契合于都市化過程的邏輯。前引①, p80 我們可以區分出都市在與居民關系中的兩個層次的媒介功能:一是都市自身的內在結構能夠給予每一個居民的媒介功能,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居住”;二是都市經由自身的結構所創造出的“公共空間”所可能提供的居民的“寓居”場所。在這個意義上,都市中的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開放空間與封閉空間,對稱空間與不對稱空間,高空間與低空間,支配性空間與補充空間如此等等的空間設計及其規劃與排布,就具有根本性意義。因為不同的空間設計與排布可能對于“居住”來說差異甚微,但對于“寓居”來說卻牽連和關涉甚廣。這也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要加強城市的空間規劃的表述背后的深意所在。
不管是居民還是公民,其都是作為現代城市生活中的一個主體與城市發生關聯的,因而其不可能跳開城市所設定的基本物質、制度和精神框架來對城市進行思考和觀察。但是,城市作為“普通人”的媒介卻能夠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向。此處的“普通人”并非指的是生活在城市中抑或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只指純然外在于都市生活的“一般人”。正是透過“一般人”的視角,城市以其自身作為樣本,給予有關城市或都市想象的基本形態。經由“一般人”的視角,我們能夠瞥見都市生活中各種不同類型的生活模式和流行元素的想象,以及都市設計中的藝術表達所呈現出的某個城市或某一類城市的獨特精神氣質。與此同時,經由“一般人”眼中所描述出來的都市中的生活經驗的想象,又能進一步地思考我們到底應該過一種什么樣的城市生活,這就進一步構成所謂城市本身應如何被想象與呈現的問題。如此一來,文學中的城市、歷史中的城市甚至是對未來想象中的城市都構成我們思考的媒介和載體。關于都市想象的討論,可參見Gary Bridge and Sophie Waston, “City Imaginaries”, in A Companion to the City, edited by Gary Bridge and Sophie Was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pp5—17 都市社會所具有的這一特質與盧曼所強調的社會本身乃是實在和虛構的統一的基本判斷不謀而合。
綜上所述,都市社會的兩個層次及其作為一種媒介型共同體的存在方式構建出一種與傳統法治認同模式有著極大差異的新型認同模式。只有基于這一新型的法治認同模式,都市社會的法治化才能夠順利得以實現。具體而言,新型的、契合于都市社會之精神氣質的法治認同模式具有如下的特色:第一,都市社會的法治認同模式的邏輯基點是利他主義,而非傳統法治認同模式的利己主義。這種利他主義不是道德意義上的善的促進,也非傳統法律意義上的寬容價值的體現。而是說,都市社會的法律主體應當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促進并認同所有的異質性要素的呈現與發展,并且這種促進和發展要以都市法律主體的倫理意識與道德行為加以保障。所謂都市法律主體的倫理意識,指的是每一個都市人都應當盡可能去實現一種自己所認為的一種不同于任何人的、具有高度異質性的好生活。而所謂道德意識,則是指每一個人必須明確自己對異質性的尋求不可能脫離他者對于異質性的尋求而獨立存在,因為如果我們不對他者對于異質性的尋求給予積極地支持,那么我們自身的異質性也無法得到呈現,缺乏了支持而只被寬容的異質性最終的結局依然是同質性。在這個意義上,利他主義不是都市法律主體的道德自覺,而是都市法治認同得以形成的必然要求。第二,都市法治認同的形成必須突破傳統法治認同所立基的“公民—國家”二元政治構造,而進入到“公民—都市—國家—全球”到四元構造中來。這就意味著,都市法治認同模式需同時考量作為中間政治單位的都市和超越于民族國家的全球主義的發展。因此,都市社會語境中的法治認同既要考慮全球性的規范如何經由都市去產生和確認,又要認真思慮都市如何經由自身的發展去培育全球性規范的產生。只有同時考量全球的都市化和都市的全球化,都市社會的法治認同才算在真正意義上突破了傳統法治認同的模式。第三,都市法治認同的主體必須突破傳統法治認同中沒有任何區分的法律主體,而進入到“公民—居民—普通人”的三重主體情境中。換句話說,都市的法治認同最為重要的面向乃是如何經由公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去塑造主導都市之形式的生成發展的政治權力,與此同時,經由居民的公共參與形塑都市內部的精神氣質和制度結構,再者經由普通人的視角讓都市的異質性獲得其普遍意義上的觀察,進而呈現在人們的視閾中。第四,都市法治認同模式需改變傳統法治認同模式的時間屬性,而突出其自身的空間屬性。傳統法治認同的模式是一種價值認同的培育模式,是“時間—陶冶”型的認同模式,而都市社會中的法治認同模式乃是經由空間的分配與構想實現不同階層和不斷分化的主體的認同,因而是“空間—媒介”型的認同模式。
Abstract:The overall initi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all-round promotion of ruling of law strategy have aroused an important thesis on identity of ruling of law in urban society. On one h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has dissolved the community which the identity mode of traditional ruling of law is relied 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evolved a new type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unique spiritual features so that a new type of intermediary community is formed. The intermediary community is justified by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heterogeneity with basic features of multi-spatial al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By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mode of national countries, this new community is relied on urban and global communities. The identity of ruling of law in urban society requires urban legal subjects with altruism and is based on the “urban-global” interaction. The urban legal subjects identity of ruling of law is promoted by spatial allocation and finally aims to realization of urban ruling of law.
Key words:urban society identity of ruling of law heterogeneity
[作者簡介]王明鎖,鄭州工商學院文法系教授。
① 參見《德國民法典》,鄭沖、賈紅梅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蘇永欽:《民法典的時代意義——對中國大陸民法典草案的大方向提幾點看法》,載《月旦民商法雜志》2004年第3期。
③ 楊代雄:《潘德克吞法學中的行為與法律行為理論——民法典總則誕生的序曲》,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④ 李少偉:《我國民法典應采用潘德克吞立法模式》,載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頁。
⑤ 日本民法第四章為法律行為。參見《日本民法》,曹為、王書江譯,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⑥ 《大清民律草案》第五章、《民國民律草案》第三章、《中華民國民法》第四章皆為“法律行為”。參見楊立新主編:《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⑦ 如《民法要義》第四章即為“法律行為”。參見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