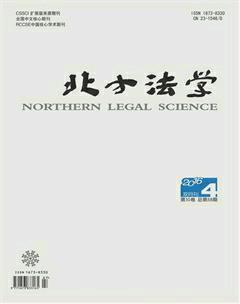《美國國際法雜志》南海專刊文章述評
摘 要:2015年10月29日,關于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的管轄權問題裁定出臺,使南海問題日益復雜。回溯到該仲裁案的提出,早在菲律賓于2013年單方面提出仲裁程序的當月,《美國國際法雜志》(AJIL)發表了一期關于南海問題的專刊文章。該期論文分別從不同視角深入探討了南海爭議的焦點問題,集中展現了中西方學者在觀點上的對立。專刊文章中批判中國立場的核心論點,與“南海仲裁案”中的菲方請求非常相應,亦與美國國務院在2014年12月發表的《南海報告》中的觀點高度一致。《美國國際法雜志》在國際法學術界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但國內學界對這期論文并無專門的分析與比較。
關鍵詞:美國國際法雜志 南海問題 領土 海洋法
中圖分類號:DF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4-0138-13
引 言
南海又名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因位于中國南部而得名。中國傳統上將南海區域密集的一些島、礁、灘、沙及其他海洋地物(insular features)分為四大群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①目前,針對南海區域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利,中國、越南、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6個周邊國家間存在爭議性主張。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步勘探出這些島礁附近存在巨大的油氣資源時,國際上還對這些島嶼鮮有關注。②事實上,東沙、中沙和西沙群島只在一兩個國家間存在爭議,因為它們都在中國的控制之下。③相比較而言,南沙群島包括了數量最多的聲索國,情勢最為復雜。④
南海問題最近因菲律賓提出“仲裁案”而倍受關注。2015年10月29日,應菲律賓單方面請求成立的仲裁庭就管轄權和可受理性的程序問題作出裁決,宣布對菲方提出的15項請求中至少有7項具有管轄權(其他議題尚待進一步確認)。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CA case No 2013-19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fore an arbitri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to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506, 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11月14日。10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明確指出該裁決是無效的,對中方沒有拘束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應菲律賓共和國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關于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裁決的聲明》,http://wwwfmprcgovcn/ce/cech/chn/ssyw/t1310470htm, 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11月14日。 盡管中方一再明確表示不接受菲方要求,不承認、不參與仲裁,但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附件七第9條規定,“如爭端一方不出庭或對案件不進行辯護,他方可請求仲裁法庭繼續進行程序并作出裁決”,理論上而言,菲單方所提仲裁程序并不因中方反對而簡單停止。宋燕輝:《由〈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論“菲律賓訴中國案”仲裁法庭之管轄權問題》,載《國際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5頁。
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依據《公約》第287條和附件七的規定向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提交了一份仲裁通知書和主張聲明,要求成立仲裁法庭審理菲律賓在南海所主張的海洋管轄權而與中國所發生之爭端。SFA Statement on the UNCLOS Arbitral Proceeding against Chi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January 22, 2013, https://wwwdfagovph/indexphp/2013-06-27-21-50-36/unclos,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7月8日。當月,《美國國際法雜志》(AJIL)發布了一期南海專刊(2013年第1期,第107卷)。該專刊共計68頁,除編者前言外,共有3篇論文集中探討南海問題。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 Agora: The South China Sea, Editors Int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1, 2013, pp95—97 其中,中國學者高之國與賈兵兵合著的文章主要闡述了中國南海“斷續線”的歷史、地位與法律含義(下文簡稱為高與賈文)。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107, No 1, 2013, pp 98—124 作者在文中以“九段線(nine-dash line)”來表述我國在地圖上所標繪的南海那U形的斷續線,同時也標注了“斷續線(dashed-line)”等其他的不同稱呼。為了保持名稱的統一性和標準性,本文一律以“斷續線”指稱“九段線”或南海“U形線”等。除非需要特別說明,下文不再專門標注。 其他兩篇分別是由弗洛里安·杜帕(Florian Dupuy)和皮埃爾-馬瑞·杜帕(Pierre-Marie Dupuy)合著的《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主張的法律分析》(下文簡稱為杜文),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 A Legal Analysis of Chinas Historic Rights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2013, pp124—141及羅伯特·貝克曼(Robert Beckman)獨著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南海海洋爭端》(下文簡稱為貝文),Robert Beckma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p142—163 這兩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提出了質疑和批判。
《美國國際法雜志》的這期南海專刊發表于菲律賓單方啟動“南海仲裁案”的大背景之下,其發表的時機和對立觀點的代表性,說明這期專刊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國內學界至今卻少有文章對這些論文進行專門探討。為此,筆者致力于將這幾篇文章的核心論點加以歸納,再比較和思考觀點差異的原因、邏輯和思路,最后再加以總結和評論。
一、中國南海“斷續線”的含義與法律相關性
(一)質疑與批判性觀點
盡管將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四個群島正式劃入領土范圍的中國官方地圖可以溯及到20世紀30年代,但南海專刊上的作者們均提及,“斷續線(nine-dash line or dashed-line)”在專刊文章中,“斷續線”也被稱為“九段線”、“U型線”、“斷續線”、“舌型線”等等,本文統一將其表述為“斷續線”。 從2009年才開始正式受到爭議。2009年5月6日,馬來西亞和越南就南海南部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共同聲明,5月7日,越南就南海北部大陸架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了一分單獨聲明。作為回應,中國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照會,要求委員會對它們的請求不予考慮,“斷續線”標示于這份照會的附件地圖上。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5、131; 前引⑨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文, p97
“斷續線”地圖在杜文和貝文中幾乎受到全方位的質疑。杜文直接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斷續線”所標示的地理范圍具體是什么?“斷續線”與中國主張是否存在相關性?“斷續線”如何在法律層面構成對中國主張的支持?針對中國的權利主張,“斷續線”如何產生說服力?等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31 之后,作者又針對“斷續線”的起源、設計、含義與法律基礎進行了逐項批駁。
杜文首先用怪異(peculiarity)來形容這種用九根“斷續線”來劃定南海的幾乎所有島嶼和大部分水域的設計。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5 “‘斷續線幾乎難以證明中國主張的確切界限,不管是地理層面的還是法律層面的”,“這個地圖僅僅是加重了對中國主張的迷惑”。作者進一步闡述其理由:1關于“斷續線”的含義,中國從來沒有給過確切的解釋和說明,譬如,它是劃定中國主張的水域界線呢,還是只圈定屬于中國的那些線內的島礁?2關于地圖和歷史性權利的關系,中國的意圖也不明確,這種不確切性所引起的問題是,地圖和中國歷史性權利的主張到底是如何聯系起來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2
其次,杜文還質疑了“斷續線”地圖的來源,認為它的作者和出處都不清楚(unknown)。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1 與此類似,貝文也指出,中國提交的這個地圖的名字是“中國南海島嶼位置圖”,說明這個圖最初的意思是描繪中國在南海所主張的那些島嶼的地理位置,它很難說明中國維護“斷續線”內的水域以及下面的自然資源的管轄與權利。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4
此外,杜文又對“斷續線”作為中國歷史性權利的證據之證明力加以否定。作者指出,削弱這個地圖的證據效力的主要因素是其來源的“公正性(impartiality)”問題。“斷續線”地圖不是,也從來沒有被宣稱是獨立的地圖繪制者的作品。中國學者宣稱地圖最早在1948年由中國內政部出版,承認地圖是中國單方面的有關主權界限的宣告。據此,地圖不符合“公正性”標準。該標準在1933年由查爾斯·切尼·海德在《國際邊界爭端中的地圖證據》一文中提出:“擁有必要地理數據的制圖者制定表達政治以及地理狀況的地圖時,其作為見證者的可靠度應當依賴于制圖時的公正性”。杜文還指出,“斷續線”以缺乏地理坐標、很厚的線等很不精確的方式畫就,根據它無法確定其所圈定的區域內的確切范圍。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32,134 文章繼續提到,即便是在中國學術界,學者們對“斷續線”的解釋也莫衷一是。一些學者指出,中國的歷史性權利是指歷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這種地位與《公約》中的專屬經濟區相同;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斷續線”只是用來標示其范圍內島嶼的歸屬,如果這樣,海洋主張將只是對《公約》的簡單適用問題。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1—135 這些闡述與“斷續線”并無關聯,或者不能說明“斷續線”的法律意義何在。
(二) 與質疑觀點相對應的論證
作為對應,高與賈文集中論述中國南海“斷續線”的歷史、地位及其含義,進而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進行分析。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98—124 他們認為,不管是從發現、占領的習慣國際法,還是從歷史性的權利依據與來源上,或者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來看,“斷續線”在國際法上始終擁有法律依據。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
關于“斷續線”的特殊設計,高與賈文中首先詳實地介紹了該地圖在中國實踐中的歷史進化過程,并將它具體區分為三個階段:1935年前中國對南海和平和有效的利用;1936年至1956年的發展;1958年至2011年“斷續線”的進化。以此證明東沙、中沙、西沙、南沙等四大群島是如何被中國人命名、利用,又如何以“斷續線”的方法描繪于地圖上用以標示中國的主權界限,以及如何逐漸被中國通過官方管理和立法活動加以確認。他們指出,“斷續線”地圖在公布后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被其他國家所尊重,受默認(acquiescence)、承認(recognition)和禁止反言(estoppel)等習慣國際法所支持。而且,這些事實作為有據可考的客觀存在,目前其他國家并無有力證據可以推翻。不管是越南還是菲律賓,從1948年到2009年間均沒有對“斷續線”提出過反對。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6
關于“斷續線”的法律關聯性,杜文認為,“斷續線”地圖的證據效力很低,因為它作為中國對其主權界限的單方描述,違背了見證人應具備的獨立的“公正性”標準。高與賈文則認為“斷續線”地圖由內政部這樣的官方部門繪制,正好符合在國際法的領土取得上之“有效占領”的要求。因為官方行為是可以歸屬于國家的主權行為,達到以發現和占領取得領土主權的條件。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1、102、110 高與賈文指出:經過了60年的進化,“斷續線”已經成為中國在南海區域長久以來的主權主張的同義詞,指中國一直擁有這些群島,并對這些群島及其鄰近水域享有捕魚、航行和其他海洋活動(包括勘探和開發礦產資源等)的歷史性權利。“斷續線”同時具備可能成為潛在的海洋邊界線的剩余功能。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08
關于“斷續線”的含義,高與賈文提出了以下五個方面的考量因素:(1)地圖在中國管理與立法實踐當中具有持續連貫性;(2)在2009年的照會提出以前,南海區域相關國家間的爭端一直是僅涉及到島嶼或海洋特征的主權問題,而不涉及到“斷續線”的問題;(3)關于中國所運用的相關術語的確切含義,譬如“鄰近水域”、“相關水域及其海床和底土”等,從來沒有被中國正式定義,同時,也沒有證據表明中國要將這些水域通過國內法而作為內水的一部分來對待(即如果將歷史性權利主張解讀為等同于內水地位的歷史性海灣等,均是誤讀。筆者注);(4)正如1947年中國內政部會議決議中所提出的“中國南海領土的邊界直到曾母暗沙”,這只是說明在過去的某個時候,“斷續線”及其前身可能被視作歷史性水域的界限;(5)有證據表明,繪制于1948年地圖上的斷續線是作為這些群島與對岸鄰國海岸的中間線,從而表明該線具有潛在的劃界意圖。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8—109
最后,高與賈文提出“斷續線”可能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它表示中國對“斷續線”以內的島嶼、巖礁等擁有主權,同時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鄰近島嶼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享有管轄權;其二,它表示中國保留在線內的海域進行捕魚、航海以及諸如在大陸架開發油氣資源等其他活動的歷史性權利;其三,它還擁有一種剩余功能,可能成為潛在的海洋劃界界線。
根據高與賈文的闡釋,南海“斷續線”是中國在特定的歷史與法律背景下,基于主張和維護南海區域四大群島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利而形成,早已為2009年前的國際社會所接受。其他國家并不能提供證據否定或超越中國的南海“斷續線”,甚至諸多證據可以證明,周邊國家有明顯的承認及默認的表現。同時,“斷續線”的法律含義亦需要從歷史進化的角度來理解,具有復合性、多層次性,并不為單一的歷史性權利概念所囊括。
二、中國 “歷史性權利”主張的含義及性質
(一)質疑與批判性觀點
杜文從地理范圍和法律框架兩個角度分解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主張,認為中國的主張不符合國際公法的標準;中國學者們所援引的為數不多的那些稱作歷史證據的資料,對于在“斷續線”以內的南海水域建立主權是不夠的;中國所重申和強調的模糊主張甚至缺乏最低限度的說服力。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41
中國“歷史性權利”術語的模糊性首先受到批判。杜文和貝文均指出,中國的官方聲明、意見以及國內法,乃至學術界,在南海問題上所運用的術語不但模糊而且多變,難以運用現代國際公法理論,或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法律詞匯與概念進行理解。他們指出,中國官方及學界在說明南海立場時有以下概念同時或交錯使用,具體含義、界限或相互關系不明確:歷史性權利(historic rights)、歷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歷史性權利依據(historic title)、也有將“historic title”翻譯為“歷史性所有權”。筆者認為這個概念主要是關于歷史性權利的依據與來源,在特定的上下文背景下,它有時候也等同于“歷史性權利”。為了與“historic right”相區別,本文統一將其翻譯為“歷史性權利依據”。具體還可參見羅歡欣:《國際法上的領土權利來源:理論內涵與基本類型》,載《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4期,第166—180頁。 歷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歷史性的(historic)和歷史上的(historical)概念;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p124、128、135 中國的主權(Chinas sovereignty)、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權利與相關主張(rights and relevant claims)、南海區域管轄權(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鄰近水域(adjacent waters)、相關水域以及海床和底土(relevant waters as well as the seabed and subsoil thereof)等概念。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5—157 術語的不統一和模糊使中國主權聲明乃至國內立法都過于籠統和寬泛。
杜文認為,因為中國的主張一直沒有運用清楚的法律術語加以闡述,只能從中國的官方聲明、行為或是學術文獻中推測其潛在的法律理由。從中國的官方聲明、實踐以及數不清的中國學者的著作觀點來看,中國的主張是某種建立在歷史基礎上的權利(some sort of entitlement based on history)。這種語言的運用導致了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按照中國的觀點,什么是歷史因素(historic factors)的法律相關性( legal relevance) ?第二,中國所運用的這種模糊與變化的術語,是意在說清楚領土主張(territorial claim)、海洋主張(Maritime claim),還是兩者兼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8
杜文進一步指出,中國領土主張的范圍是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個群島,而最近的聲明表明,中國所主張相關海洋權利不僅包括島嶼周圍的領海和毗連區,還包括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6—127 這種寬泛的主張導致的問題是,中國沒有區分哪些是可以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定義享受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島嶼,哪些是只能享有領海和毗連區的巖礁。并且,因為“斷續線”地圖以及偶爾提及的它與“歷史性水域”的聯系,在“斷續線”是否具有劃分中國領水的功能方面,導致了更大的不確定性。鑒于中國沒有對“斷續線”作出確切說明,其結果便是中國的海洋主張在本質上是不清楚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5
接下來,杜文分析了中國“歷史性權利”主張在國際法上的意義。作者指出,從海洋法上說,歷史性權利術語源自“歷史性水域”這一狹窄部門,該部門由國際法委員會提出。然而并不存在一致接受的“歷史性水域”的定義,并且“歷史性海灣”和“歷史性水域”的法律體系,從來沒有在某個國際條約,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闡述清楚。不管是規定直線基線問題的第7條,還是規定海灣的第10條,均沒有關于這些概念的定義。
在領土取得背景下的“歷史性權利”往往指一國對其具有遠古淵源的領土之法律依據,也指主張國通過真實的、持續的權力展示以及第三國的默認等形成的“歷史的創造”或者“固化”的過程。前者涉及到法律文書,例如割讓條約,而后者涉及領土取得的模式,可是,“歷史權利固化”一直是高度爭議的,并且在國際法院的案例中被多次拒絕適用。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7—138 因此,針對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杜文分別探討了“對‘斷續線內的海域”、“對‘斷續線內的島嶼”、“作為中國在南海享有自然主權的歷史證據”等幾種解釋的可能性,進而提出中國的主張不符合國際法,“其不確定性讓人迷惑”。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6—141
貝克曼也從類似的角度批判了中國歷史性權利主張的“模糊性”。他主要分析了中國2009年照會的兩種潛在的解釋,他認為,一方面,照會提出對島嶼及其鄰近水域主張主權,這個水域可能是指領海;中國陳述包含這些島嶼享有它們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意思,這無關于“斷續線”地圖,可能表明中國會根據《公約》提出海洋主張。另一方面,中國陳述稱“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相關權利以及管轄權被大量的歷史和法律證據所支持”,也表明中國可能將它的海洋主張建立在歷史證據的基礎上。這些潛在的解釋可能性,表明中國在南海的主張保持著一種戰略性模糊的政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55—156
(二) 與質疑觀點相對應的論證
高與賈文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中國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問題。首先,中國的歷史性權利是自遠古以來歷史發展的產物(from time immemorial),就如國際法院在厄里特里亞和也門案件中所提及的,一項歷史性權利可以潛在地通過擁有領土的共識(common knowledge of the possession of a territory)來建立。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3 關于這種歷史性權利的類型,他們以中國渤海為例,在過去的歷史上,包括1958年的中國關于領海的聲明在內,渤海一直被視作中國的內水。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他們強調,越南、菲律賓等聲索國也提出歷史性權利主張,比較起來,其他這些國家的主張都不具備這些特征,證據上有明顯瑕疵。例如,越南所聲稱其占領西沙群島某些島嶼的最早的主權行為的證據是在1816年,但是,這根本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國家行為來證明其所謂的“占領”主張,因為越南在1884年前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同樣,在1887年和1954年之間,法國是越南的保護國。事實上,1887年的中法條約是將這些島嶼以及南海的其他群島分配給中國,所以,越南建立在歷史性權利依據上的主張本身剝奪了1887年中法條約的效力。此外,1933年,法國以 “無主地”為借口占領南沙九小島的事件并不能成為其取得領土主權的依據,因為中國在此之前早就發現了這些島嶼并實施了主權權利。1947年,當中國內政部正式宣告擁有四個群島的主權并將它們置于廣東省管轄之下時,法國以及其他國家均沒有任何回應。實際上,從1933年到1956年,法國并沒有在該區域實施任何主權行為。所以,到1974年,法國向英國承認,它已經喪失了對南沙群島的權利依據。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1
其次,高賈文提出歷史性權利在中國的主張中只是扮演著補充(supplementary role)的角色。他們指出,在論證“斷續線”時,中國律師們也考慮到了歷史性權利學說的相關性。但是,基于中國的發現以及和平和持續的主權展示,歷史性權利學說在此承擔補充性的角色,以證明中國長期踐行的所有權實踐已經成為符合發現和占領要件的權利根據。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4 并且,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不只是及于這些群島,還為其他附帶性的權利主張提供了依據,譬如該區域的中國公民世代建立起來的賴以生存的設施和設備等。
為了證明這種歷史性權利的形成方式,高與賈文以1998年國際常設仲裁法庭作出的厄里特里亞和也門仲裁案為例。在該案中,仲裁庭的意見是,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某些歷史性權利可以通過歷史固化的過程累積形成,這種權利形態未及于完全的領土主權,但為維持某些(在該案中,針對紅海兩岸的人口而言)存在了世紀之久的“共有物 (res communis)”類型的權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礎。從而,仲裁庭認為應該永久保留一些傳統漁區,盡管這些島嶼周圍的水域判給也門,但為了那些勤苦人們的秩序與利益,也門有必要保證厄里特里亞和也門雙方的漁民都享有自由出入和捕魚等相關權利。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p121—122
再次,針對概念和術語運用上的質疑,高與賈文提出,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權利自古沿襲而來,形成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前,自然無法完全套用海洋法公約的規則、概念或定義。雖然歷史性權利這一概念在《公約》中有提及,但其內容并不完善。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由持續的、長期的中國實踐所形成,這種按照習慣法、通過歷史而形成的狀態既包括權利資格、依據(title),也包括實踐中所實際擁有的權利(rights)。并且,將“historic rights” 和 “historic title”這兩種術語交換使用的做法,不但在厄里特里亞和也門案件中存在,也出現在其他一些國際司法案例當中。例如,1982年的突尼斯和利比亞的大陸架案件中,國際法院認為,因為長期的利用,歷史性權利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這種權利與權利根據及于地中海的游動和附著物種。同時,盡管突尼斯提出的歷史性漁權(historic fishing rights)問題在目前情況下并不影響雙方提出的大陸架劃界,但在海洋主張的背景下,對那些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源的人而言則意義重大。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2
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相關法律的適用問題
(一)批判與質疑性觀點
貝文專門探討南海爭端中《公約》及相關法律的適用問題。作者簡要回顧了南海各聲索國的主張,認為南海爭端既包括領土主權爭端,也包括海洋劃界爭端,因此領土主權爭端與海洋劃界爭端應該放在一起討論。然而,《公約》并不規定陸地領土歸屬事宜,為了將南海爭端放在公約的框架下分析,貝克曼又指出,盡管《公約》中未對陸地領土歸屬問題作出直接規定,但其諸多的條款涉及到領土主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相關問題。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42—143 據此,貝文提出了一個復雜的前提假設:
如果各南海劃界國家能夠善意地適用《公約》的規定,那么海洋主張將被區分出來,從而可以使各聲索國撇開有關島嶼的領土主權爭端,建立一種在海洋主張重疊的區域進行合作的框架。相反,如果一國或者多國在海洋劃界中強調其海洋主張不以《公約》為依據,其他國家為了使主張的有效性獲得一個有法律拘束力的決定,將沒有選擇而只能訴諸《公約》的爭端解決機制。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43
接下來,貝文從三個方面展開對這個假設的驗證與探討:
首先,作者概述爭端各國的主張,指出總體的爭議為島嶼主權爭端與海洋劃界爭端的混合,并認為:盡管所有聲索國在南海劃界時都主張從它們的群島基線或者大陸沿海基線計算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但這些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的外部界線的確切位置都是不清楚的。據“陸地決定海洋”的原則,海洋區間只能根據一國主權范圍內的陸地領土計算。因此,不同的沿岸海域的地理特征,例如島嶼、巖石、低潮高地、人工島嶼、設施與構造、暗礁等,在《公約》中的法律意義差別很大。那么,南海區域近海的海洋地物可以導致哪些海洋區間呢?因為,在南海的大多數地理特征在高潮時都不露出水面,聲索國也都沒有說明他們認為哪些是島嶼,亦沒有澄清他們根據這些島嶼主張哪些海洋區間。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1
其次,貝文考察了各聲索國在南海劃界上的立場演變。作者先介紹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情況,之后才是中國。有意思的是,在此作者又提出了一個前提假設,即:如果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認定離他們的大陸或者群島基線遙遠的符合島嶼定義的海洋特征僅僅只享有領海而沒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這將符合它們的利益,使大多數富含油氣資源的地點位于爭議的區域之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2
事實上,一系列的證據也證明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正逐步走向以上假定的立場。“一個最為重要的發展是,正如它們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所提交的聲明中所述,馬來西亞和越南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只是從他們的大陸沿岸基線起算,而沒有根據大陸沿岸基線以外由它們主張主權的其他任何島嶼起算”。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2—153
然后,貝克曼批判中國在南海的立場遵從著不同的演變路線。他指出,“盡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在逐步和《公約》的規定保持一致,但中國仿佛要將其海洋主張不僅僅建立在《公約》,還要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上。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3
進而他從“島嶼”定義的角度質疑中國在南海的領土取得依據:
一些聲明指出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是針對這四個群島的所有島嶼、巖石、暗礁以及沙洲等,但是,其中的部分地貌特征并不符合國際法上對于島嶼的定義。例如,中國所主張的四個群島中一個是馬科斯菲爾德沙洲(Macclesfield Bank,即中國所稱的中沙群島,筆者注),報道稱,它是由下陷的暗礁所組成,即便是在低潮時期也完全淹沒在海水下,如果是這樣,這將不能成為一項主權主張,因為主權主張只能針對陸地領土。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4
對此,杜文也有提及。該文指出,中國未根據《公約》對其在南海主張的海洋特征進行區分,哪些是“島嶼”(可以賦予全部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哪些是“巖礁”(只能賦予內水和領海),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 從而批判中國的主張是不明確(uncertainty)的。
貝克曼還結合南海爭端與《公約》的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了分析。他提出,協商與暫時共同開發的途徑過多地依賴于中國是否在南海區域依據《公約》進行劃界。如果中國按照《公約》規定對其主張進行限制,則不能對符合《公約》定義的島嶼以外的海洋地物主張主權,也不能對那樣的一些海洋區域和資源主張歷史性權利。根據2009年的中國照會及行動,中國在南海的主張為三個維度:一是中國主張島嶼及其鄰近水域的主權,這個類似于領海;二是這些島嶼將各自授予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三是以某種歷史性權利為基礎,中國還主張對“斷續線”內水域和資源享有進行控制的權利與管轄權。結合《公約》的規定,中國主張的這三個維度均不確切。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7 貝克曼對中國主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中國自身為《公約》的適用設置了一個重大障礙。它似乎基于歷史性權利而對南海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主張管轄權,且這種權利來源先于《公約》和現代海洋法。中國的主張威脅到建立在《公約》基礎上的整個體系。在海洋法上,它所牽涉的根本利益不僅是相關國家在中國南海的劃界問題,而且關系到海洋法和《公約》之持續有效性框架下的所有國家的利益;除非中國愿意使其主張與《公約》保持一致,否則沖突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63
(二)與質疑觀點相對應的論證
關于法律適用的問題,高與賈文從兩個法律體系的角度進行闡述。他們首先提出“沒有任何條約可以窮盡國際法規則”。中國所主張的在“斷續線”內的群島及相關水域的權利是以包括但不限于《公約》的國際法為基礎的。關于群島的領土主權問題,例如島嶼發現和占領,主要以習慣國際法為依據;對于線內的海域空間,《公約》的相關條款以及歷史性權利理論提供了法律基礎。《公約》不能窮盡國際法,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的權利依據及權利(title and rights)形成于《公約》以前,它與中國在《公約》下的義務不相矛盾,是對《公約》的一種補充。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9、123
接著,高與賈文又對中國主張的權利依據進行了具體闡述。首先,關于發現和占領的證據與事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在南海一直享有和踐行著某些權利而不受任何其他國家質疑。中國發現南海這些島嶼的時間要比菲律賓和越南早了許多年,這是不容否認的,“斷續線”就是中國長期以來以國家身份在南海宣布主權的重要證據。在現代國際法的早期階段,發現就足以有效地建立領土主權依據,此后,在國際法上逐步形成占領的概念。然而,一國通過占領取得領土主權同樣必須以對“無主地”的發現為前提,對“無主地”的發現是占領國進行占領的時機。“無主地”區別于無人地,指不屬于其他任何主權國家管轄范圍之下的陸地,對此不能進行輕易的假定。如果“無主地”是因為某國對領土主權的喪失或放棄而形成,這種放棄或拋棄必須有肯定的意愿及行為表現。中國對南海諸島的發現是一種自然的最早發現,之間不存在他國提前發現或者自身放棄或拋棄領土等情況,故這種最早類型的發現只要配合以象征性并入(symbolic annexation),哪怕是國家對主權權利的微小的確切實踐,即足以滿足發現與占領取得領土的效果。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0—111 所以,“斷續線”地圖作為國家行為的產物,在中國表達國家占領的主權意愿和行動上都具有明顯意義。
其次,承認、默認和禁止反言也是中國重要的權利依據。關于承認的一個重要事實是,1887到1959年間法國和越南對中國在南海的島嶼主權的承認,特別是1887年的《中法邊界條約》以及越南對中國1958年《關于領海的聲明》的承認。同時,標示中國對這些群島擁有主權的地圖被全世界廣泛復制,包括1912年英國海軍艦隊制作的“中國航海圖”等。關于默認,從1948年到2009年,不管是菲律賓還是越南都沒有對中國的“斷續線”提出任何反對。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6 可以說,“斷續線”所標示的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歷史性權利,在二戰以后的60多年里進一步得到鞏固,也從來沒有被其他國家抗議過(直到2009年)。同樣,基于中國在南海區域的這種長期實踐,歷史性權利固化理論也可以具有一定的證明意義,盡管這個理論存在爭議。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高與賈文進一步說明,中國沒有忽視或者違反《公約》的條款。盡管《公約》是一個全面而復雜的法律文件,但它是各國在談判中達成妥協的產物,并不能包含海洋法中的所有問題。《公約》條款中也指出,對于其中沒有規定的情況,各國應遵循習慣國際法。中國繪制的“斷續線”地圖主要建立在習慣國際法的基礎上,所以,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與《公約》并不矛盾,甚至,中國有關“歷史性權利”的主張與實踐可以為《公約》以外發展習慣國際法提供空間,填補在1982年時不能放入《公約》條款的空白理論。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3
四、比較與評述:專刊觀點與南海其他相關議題
(一)菲律賓單方所提仲裁請求的相應法理
《美國國際法雜志》南海專刊的出刊同月,菲律賓單方提起“南海仲裁案”。細加考察,菲律賓所提出的15項仲裁請求主要包括:要求認定中國主張的南海“斷續線”內的主權權利、管轄權以及“歷史性權利”與《公約》相違背;美濟礁、仁愛礁、渚碧礁、南薰礁、西門礁(包括東門礁)為低潮高地(不符合島嶼定義),不能產生領海、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黃巖島、赤瓜礁、華陽礁和永暑礁不能產生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中國非法地干擾了菲律賓享有和行使對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等等。參見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2 January 2013,http://wwwgovph/2013/01/22/dfa-notification-and-statement-claim-on-west-philippine-sea-january-22-2013/,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6月8日。
菲方所提交的證據材料無法一一考察,但就其請求的內容來看,其單方申請仲裁的目的,即是要求在《公約》的框架下,否定南海“斷續線”的歷史與法律意義,否定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以及從島嶼定義的角度否定中國在相關島礁及附近海域應享有的主權、主權權利與管轄權(主要是劃定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的權利)。可以說,菲仲裁請求的法理思路即是從前述三大爭議焦點來否定中國主張,與南海專刊中杜文與貝文所持的觀點非常相應。從這個意義上看,杜文和貝文為菲律賓所提仲裁請求提供了頗具代表性的學理支持。當然,有必要說明,筆者并不推測文章作者與菲律賓之間有什么聯系,此處完全是基于學理觀點上的相應性而探討,由此,至少可以發現,《美國國際法雜志》所刊文章的學術代表性與影響力還是值得重視的。
(二)美國《南海報告》的相應觀點
2014年12月5日,美國國務院對外發表了題為《海洋界限——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Limits in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專門報告(簡稱美國《南海報告》)。該報告由美國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撰寫,特別質疑了中國地圖上的南海“斷續線”,其基本觀點與專刊中的杜文和貝文如出一轍。只是,相比于南海專刊60多頁的篇幅,美國《南海報告》正文共24頁,文字內容上更為精煉,同時增加了諸多具體的地圖與圖片比較。參見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 5, 2014
其中,“斷續線”地圖是其分析的首要出發點,特別是對地理坐標、精確度及范圍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比較。報告在第一部分即專門對1947年中國地圖上的南海“斷續線”與2009年地圖的“斷續線”進行對比分析,分別列出全圖、比較圖和局部圖,并且對各圖所繪“斷續線”的數量、線條之間的距離、線條與沿岸國的距離、“斷續線”本身的位置等進行了細致比較,進而指出中國不同年代的地圖上所繪的南海“斷續線”在寬度、位置等方面均不精確、不統一。參見前引B60, pp3—9 以此為基礎,報告接著從《公約》出發,提出中國并未明確其“斷續線”主張的性質與范圍,從而圍繞島嶼歸屬線、國界線、歷史性主張線等幾種可能性展開推測性探討(這與貝文的假設性論述在邏輯上頗為相似),最后提出,中國的主張要在海洋法上找到依據,應該只能從島嶼歸屬的角度來理解南海“斷續線”,再依據《公約》定義來劃定相關海域的界限。
然而,美國《南海報告》并沒有回應高與賈文的論點,未分析《公約》適用的非溯及性和內容的局限性,未對中國“斷續線”形成前后的特定歷史與法律條件進行考量,未對周邊其他國家所提歷史性權利的概念和證據進行比較,亦沒有討論高與賈文中所提出的承認、默認及禁止反言等問題。
菲律賓在“南海仲裁案”中的請求,因為中國是被申請方,它所取的否定中國的立場無可非議。但是,美國《南海報告》,從分析主題、問題取舍和所適用法律等多個角度來看,幾乎完全呼應了專刊中杜文與貝文的思路和觀點(質疑性觀點),卻忽視高與賈文的觀點(支持性觀點)。如果以客觀中立的標準來評價,不能不說這份分析報告在邏輯上還欠完整,在內容上還欠全面。
(三)比較與總結
綜合來看,南海專刊文章顯現了理論觀點上的鮮明對立。為什么針對同一主題,會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很大意義上,國際法的不確定性是其作用受到質疑的焦點。作為批判法學派的核心代表人物、著名國際法教授馬丁·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曾提出:“國際法的目的基于不同的立場而存在差別。國際法無法避免不同的國際行為者的偏好、利益與政治價值。”Martti Koskenniemi,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 Malcolm 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2 所以,對同樣的法律規則,不同的律師或法學家完全可能做出不一樣的解釋。
這一點,在南海專刊文章中得到明顯反映。例如,關于“斷續線”地圖問題,杜文指出,因為該地圖的起源具有政府背景,不符合國際法上關于地圖證據的“公正”要求,從而不具有證據的證明效力;高與賈文則認為,正是因為“斷續線”地圖具有政府背景,從而符合國際法上有關領土占領取得的國家行為要件,是國家行使主權意志的體現。又例如,關于對中國“斷續線”以及歷史性權利主張,杜文與貝文堅持用《公約》上的“島嶼”定義,“歷史性權利”與“歷史性水域”、“歷史性海灣”、“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等概念及其理論來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主張“模糊、不確定”;高與賈文則指出,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及“斷續線”地圖形成于《公約》之前,該公約主要針對海洋劃界、海洋資源共享,由各國通過多年談判達成的妥協方案,它不解決島嶼歸屬問題,亦不能規范一切海洋問題。
此外,前文也提到了美國《南海報告》與南海專刊中的杜文與貝文在論點與思路上頗具一致性,而對高與賈文中的視角少有關注。如果用科斯肯涅米的批判性法學觀點來解釋美國《南海報告》的內容、分析方法與結論,可以認為,該報告發布方所持的目的、立場、政治利益及偏好可能會影響到報告在問題與思路上的取舍。
綜合說來,比較正反兩類觀點之間的主要矛盾,《公約》的局限性不容忽視,因為南海特殊的地理、歷史背景與爭議現狀是獨特的事實。因此,筆者認為,以下問題值得注意或進一步探討:
1時際法問題與證據優勢的相對性
時際法關注的不是時間的有效性,而是某項規則的適用時間。如果有法律交互作用以任何形式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而同時相關的法律規則進行了進化或改變,那么是適用原來的舊法還是現有法的問題就會產生。當法律的作用形式依原來的法律規定是合法的,或至少是不被禁止的,而現在被禁止了,這個問題就至為關鍵。Markus Kotzur, Intertemporal Law, wwwmpepilcom,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8月6日。早在1899年,國際仲裁機構認為,圭亞那和委內瑞拉的邊界爭端應該按照“取得當時”的領土規則來解決。 Délimitation de la Guyane anglaise [Grande-Bretagne, Vénezuela],http://legalunorg/riaa/cases/vol_XXVIII/331-340pdf, p338 1928年有名的帕爾馬斯島案中,著名的瑞士仲裁員馬克斯-胡伯概括國際法上的時際法規則為“司法事實的認定必須根據與事實同時代的法律,而不是爭端發生或解決時實施的法律”。Award of 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 22 AJIL1928, p845
就南海問題而言,在1982年《公約》之前,世界上并無統一的、受到普遍接受的關于“島嶼”“群島”等概念的定義,更不用說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了。因此,在中國最早制定“斷續線”地圖以宣示在南海主權的年代,并沒有區分島嶼、非島嶼巖礁或者其他海洋地物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而且,不管概念或用語如何,中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將所有的這些島嶼、巖礁或暗礁等視作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等四個群島的一部分來看待。中國多次宣告,這四個群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此,不管是越南、菲律賓還是馬來西亞等國,都沒有超越性的證據可以形成對抗。從而,按照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的觀點,領土爭端中最關鍵的問題,可能往往不是對領土管理之通常規則的解釋問題,而是在相比較之下,爭議雙方誰的證據更優的問題。Georg 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1957, p290 也就是說,南海爭議各國之間在法律上應該最終關注相對性證據優勢的問題。
2關于不符合島嶼定義的巖礁及其他海洋地物是否適用領土取得規則
南海的一些小島、巖石、暗礁、沙灘可能不符合《公約》中有關“島嶼”的定義,但是否就能夠認為這些海洋特征不能作為國際法上“領土取得”的對象呢?事實上,國際法上的領土概念指的是“空間(space)”,并不局限于陸地領土。參見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th edition, 2013, p216 而且,《公約》對“島嶼(island)”進行定義,其目的在于對海域的測量和劃界,并未說明那些不符合“島嶼”定義的巖、礁、沙、灘等不屬于“領土(territory)”范疇。這一點,在英法大陸架案件中就有過闡述。在該案中,英國在反駁法國的觀點時提出,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包括運用低潮線時的島嶼周邊作為海洋區域),英國人在事實上存在著將艾迪巖(Eddystone Rock)作為島嶼對待的當代實踐。盡管國際仲裁法庭沒有確切地對艾迪巖的法律地位闡明立場,但法庭提出在該海峽劃定大陸架邊界時,艾迪巖應當作為一個關聯基點對待(relevant-point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 in the Channel)。參見Anglo-French Continental Shelf Case (United Kingdom v France) (1977, 1978) 18 RIAA 3, p 271; E D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1: Introductory Manual, X edition, Dartmouth Publishing Co, 1994, pp153—154; Barry Hart Dubner, The Spratly “Rocks” Dispute-A “Rockapelago” Defies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 9, 1995, p301
3.如何對南海的特殊地貌進行定性并劃定領海基線
按照《公約》第46條,“群島(archipelago)”的定義是:一群島嶼,包括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相連的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彼此密切相關,以致這種島嶼、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質上構成一個地理、經濟和政治的實體,或在歷史上已被視為這種實體。按此定義,中國的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島全都符合“群島”的條件。那么,即便不談“島嶼”定義的爭論,“群島”是否可以整體地作為一種“陸地領土”來對待呢?這些問題在既有理論及實踐中都鮮有確定性,是當前海洋法局限性的體現,但是,不能因為法律規定不明而對中國的權利予以簡單抹煞,或以其他概念生搬硬套。
如果將“群島”這個整體概念作為領土取得的對象來看待,再依據“陸地決定海洋”的規則,只要陸地領土能夠確定,海洋邊界的確定就是關于《公約》的簡單適用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不能說中國的主張是不確定的,因為中國至少對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個群島作為整體的陸地領土主張(區別于海洋主張)是肯定的。關于中國歷史上對這四大群島的發現及占領等問題,高與賈文的探討比較詳實,甚至杜文也對此進行了肯定。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7 對此,美國《南海報告》也在一定意義上給予了肯定,至少認可了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可以是一種“島嶼歸屬線”,前引B60, p11 因為島嶼的法律意義與陸地領土一致。事實上,如果有關群島歸屬的“整體性”主張成立,相關島礁因為都隸屬于群島,島嶼的單獨定義問題也不再有意義,而有關中國主張模糊的質疑則只是屬于中國未宣布在南海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外部邊界的問題。
有必要指出,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表態將南海“斷續線”與我國的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的外部邊界相等同。并且,包括越南、菲律賓等南海周邊國家在內,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沒有宣布它們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外部邊界。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47按照《公約》,何時宣布在南海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的精確外部邊界與坐標是中國自己的權利,如果因為中國沒有宣布這樣的精確邊界而單方面地批評中國的主張含糊或不確切,顯然沒有依據且有失公平。事實上,中國在1996年已經宣布了西沙群島的直線基線,PRC Straight Baseline Declaration (15 May 1996) 只是南沙的領海基線和劃法中國暫時都還沒有公布。
總之,有關南海問題的爭議,很大一部分屬于《公約》所沒有規定的事項,例如:“群島”的領土取得與領土歸屬問題;因歷史而形成的群島“附近水域”的經濟權利問題(“歷史性權利”問題范疇);在一國的領土內既包含大陸領土又包含若干遠洋群島(這種狀態并非海洋法公約中的“群島國”定義所能涵蓋)的情況下,如何劃定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的問題等等。所以,如果簡單地套用《公約》的概念、名詞與規則,必然產生某種混亂或對中國的“斷續線”與“歷史性權利”主張難以理解。
《美國國際法雜志》發表的南海專刊體現出國際學界對中國南海問題的關注。盡管一些文章對中國觀點提出尖銳質疑,但這種討論有助于對南海問題的多元認識,有益于促進中西學界的學術對話,亦可以為南海問題的解決提供思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學術界對南海問題的研究有必要保持開放的姿態,加強對不同觀點的研讀與回應。對于我國南海“斷續線”的歷史、地位與作用,高與賈文論據詳實、邏輯清晰、說理客觀,可以說為我國南海問題的澄清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持。高與賈文已經以中英文的形式出版。參見高之國、賈兵兵:《論南海九段線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
國際法是一種“平權”社會的法,沒有凌駕于所有國家之上的、具備獨立權威的立法、司法與執法機關,國際法的產生取決于國家的意思,國家既是國際法的制定者又是國際法約束的對象。實際上,正是因為《公約》的局限性和南海問題的獨特性,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在表述上相對比較復雜,層次比較多。但是,南海問題的復雜性與解釋上的困難,不應該成為一攬子予以否定的理由。相反,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理論立場,應該是豐富和發展國際海洋法的重要實踐,可以為國際社會積累有益經驗。
Abstract:On Oct. 29, 2015,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Hague made an arbitration award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as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filed by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s mad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creasingly complex. Dating back to the same month of 2013 when the Philippines unilaterally proposed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JIL) issued a special series (Agor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hich those articles have deeply discuss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dicating sharply contrasting opin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The critical views against Chinas position can be summarized to be ra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arbitration claim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highly similar to views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Report made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namely th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d on the Dec. 5, 2014.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AJIL is world-widely recognized, but unfortunately, this special series have not been particularly analyzed and studied domestically.
Key words:the AJIL Issu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law of the sea
[作者簡介]劉蕊,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海南省委黨校講師。
① 參見[日]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朱恒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頁。
② 程維榮:《兩漢贖刑考》,載《西北政法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③ 參見周密:《中國刑法史》,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