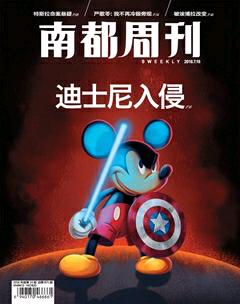嚴歌苓:我對中國社會不再只冷眼旁觀
河西

剛剛卸任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評委,嚴歌苓就出現在她的最新小說《舞男》發布會現場。
白色短袖連衣裙,蛾眉淡掃,略施薄妝,頭發簡簡單單在腦后挽了一個發髻,顯得清新大方,又不落俗套。
1958年出生的她,今年已經58歲了,可是嚴歌苓在旁人看來,年齡似乎已定格,永遠是美麗中略帶憂郁的少女模樣,將人生悲喜,藏在心中。
年容未老,心已滄桑。
嚴歌苓當然是個“有故事的人”,否則,怎么能將那么多人世間的男女、生死、人性的掙扎、蒼涼與繁華寫得入木三分?
“大概因為我善于講故事,也喜歡刻畫人物吧。”她淡淡地說。生于上海,在安徽長大,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對越自衛還擊戰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進入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時,和莫言、余華是同班同學。90年代末,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后,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研究生,那一年,她已經32歲。一邊刷盤子,學叉子、西餐和咖啡,捋順了舌頭學英語單詞,敏感而痛苦的年代。
這些經歷,從她的小說中一眼就看得出來,《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少女小漁》中剛到美國、像一顆小小臺球感受著中西兩種文化碰撞的小漁,何嘗不是她當年苦苦奮斗的淚水化成?
也許是太有故事性的緣故,她的小說似乎特別容易改成影視作品并大獲成功。
現在,嚴歌苓透露,她的新作《舞男》,影視改編權的爭奪可謂異常激烈。一個光怪陸離的上海灘舞場,地位懸殊、文化背景懸殊、年齡懸殊的兩個男女,演繹了一場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戲,還暗藏著她對中國社會新階級的觀察,怎么說,都有很多賣點,讓人異常期待。
我喜歡給陳沖口述故事
南都周刊:上世紀70年代,你曾經是成都軍區一位年輕的舞蹈演員,那時,每次去阿壩草地的軍馬場演出,都會經過汶川地區,那一段經歷是否也影響到你寫《天浴》?
嚴歌苓:是的,汶川是我非常熟悉的小城。第一次去的時候還是個小女兵,是1972年。后來還去過許多次。寫《雌性的草地》時去過一次,采訪留下的知青。第三次去草地,我就是在那里學會了騎馬,跟那些牧馬班的女孩子放過夜牧。寫《天浴》的時候,一閉眼睛,草地的味道都回憶起來了,所以我是幸運的,很小就走了那么多地方。
南都周刊:在你所有改編成電影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天浴》。
嚴歌苓:我自己也很滿意陳沖導演的《天浴》,不論是從電影藝術的角度,還是對人性的思考,都和我非常非常接近。我覺得當時她之所以能拍出這樣的電影,是因為她清心寡欲,沒有什么雜念,自己投資了40%,現在這種精神也挺少見了,可能20出頭的年輕導演還有這種勁頭,有這樣純粹的追求。
南都周刊:是怎么寫《天浴》的呢?
嚴歌苓:《天浴》的短篇小說是得了獎的。中文得了臺灣的大學生小說獎(因為那時我還沒有讀完碩士),英文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獎。在寫小說之前,我把這個故事口述給陳沖聽,她說她都能看見畫面了。然后她按照小說寫了個電影大綱,我們就是從那里開始合作這個電影的。我常常喜歡把故事口述給陳沖,《小姨多鶴》的故事我好多年前就講給她聽了,她說是個好小說。記得當時一位朋友送了我一件日本女人的和服,她還說,穿上它去寫那本小說吧,找點感覺。
南都周刊:和陳沖是怎么結識的?我知道你們是特別要好的朋友,據說和陳沖一碰到就整天黏在一起玩,吃飯、逛街、買衣服?
嚴歌苓:和陳沖的最初結識是通過我父親和我繼母。那時候陳沖的哥哥陳川和陳逸飛常到我爸爸住的賓館去玩,有幾次把陳沖帶來了。陳沖的第一部電影《青春》是和我繼母俞平一塊演的。現在我們已經不怎么逛街買衣服了,在美國大家都是牛仔褲T恤,穿得太漂亮像是挑釁大眾似的。我們在一起燒菜比較多。
老在原單位待著不是挺乏味嗎
南都周刊:1980年,你發表了電影文學劇本《心弦》,次年,該片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你是怎么會去寫電影劇本的?
嚴歌苓:當時我爸爸在寫電影劇本,他周圍的叔叔都在寫電影劇本,包括白樺、葉楠、梁信等等長輩。我總是受我爸爸的影響很深,跟他學,他干嘛我就干嘛。
還有就是,寫電影馬上就被電影廠抽調出去,到電影廠的招待所住著修改劇本,這樣就可以離開原單位。老在原單位待著不是挺乏味的嘛。到了電影廠,沒有領導看著,又可以和一幫像自己一樣的年輕人在一塊狂妄、自由、海闊天空地瞎侃,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不是最理想的嗎。電影拍了當然好,不拍,也如愿以償了。
南都周刊:當時你寫了很多劇本,《殘缺的月亮》《七個戰士和一個零》《大漠沙如雪》《父與女》《無冕女王》等大多沒有正式投拍,是什么樣的原因?
嚴歌苓:因為當時的制度是沒有導演、光有編輯,只聽編輯的意見,一遍一遍地改劇本。一個電影怎么可以是編輯的主旨,不是導演的呢?等你按照一層層編輯的意見改完了,那劇本還能看嗎?哪一個有才華的導演會看上這樣的劇本,來導演它呢?這是一個謬誤的創作程序。
南都周刊:你是好萊塢專業編劇,在好萊塢編劇的報酬是否也比在美國寫小說要高得多?
嚴歌苓:好萊塢的編劇協會每一次罷工,都會把協會會員的最低稿酬鬧得高一些。但中國編劇的稿酬也在上升中。國內沒有這個協會,所以編劇的權益沒有受到保護。其他電影行當也一樣,沒有業內人自己的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南都周刊:剛剛到美國定居以后寫作和生活方面是否一帆風順?在美國如果只是用中文來寫作,那么你寫的小說主要還是給臺灣發表和出版?
嚴歌苓:我是作為留學生到美國的。留學生的生活都非常艱苦,但非常有趣,有時候還挺刺激。朝不保夕,充滿未知,充分調動你的生存原動力、生物的生存力和智慧,不是很刺激嗎?當時我寫出的小說在臺灣、香港發表,主要是因為我要掙美元生活。國內的稿費那么低,又不能換成美元,我就是寫,對于我在美國的生活不也還是杯水車薪嗎?所以存在決定意識是一點沒錯的。生存的大命題往往決定一個人相應的舉措。
南都周刊:1995年的《少女小漁》是劉若英電影成名作,影片獲亞太地區電影展最佳故事片獎。導演張艾嘉是怎么看中你的這篇短篇小說的?據說是李安看中了轉給她的?
嚴歌苓:是的。我并沒有跟張艾嘉直接聯系過。只跟李安通過幾次電話。當時我在芝加哥讀書,他在紐約,所以最初買版權和后來怎樣改劇本的事情,都是在電話上談的。劇本我寫了兩稿,張艾嘉和另一個編劇又改了幾遍,最終拍攝用的稿子跟我的第一稿差別挺大的。
作家筆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難忘
南都周刊:你說:“我喜歡寫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衣服、首飾都是給女人的一樣,寫她們很過癮。”《一個女人的史詩》這個題目基本上可以視作你的小說寫作的一個宗旨:為女性立傳,從一個女性的人生歷程來折射歷史的變遷。對你來說,什么時候開始有一種獨立的女性意識來創作小說?有沒有考慮過以男性視角來寫作一部小說?
嚴歌苓:豈只是我愛寫女性!不說國外的和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家,光看國內當代的男作家,包括蘇童、莫言、畢飛宇等等,他們筆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難忘。尤其是蘇童。
其實我也寫過男性為主角的小說,比方說我的中篇小說《倒淌河》《拉斯維加斯的謎語》英語小說《赴宴者》,等等。但因為自己是女人,寫女人對于我更加自然。
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訴我她們的女朋友的故事,有寫不盡的題材。我覺得有趣的是,女人談論女人比談論男人要多。這樣我得到有關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過也說不定我冷不防就會寫一本以男性為主人公的小說。
南都周刊:《有個女孩叫穗子》是你的中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小說可以獨立成章,但是串在一起的就是一個叫穗子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的身上是否也有你本人的很多影子?
嚴歌苓:是有一點我自己的影子。童年時候有一些故事是聽來的,有一些是看來的,但都只是一點因子,被想象力發酵,補充,完整了。參軍后的故事里面,我們確實有過那么一只狗,許多細節也是真的。還有那個西藏女孩,很多細節是真的。我多次說過,細節很難編。
我的美國教授說,寫什么不重要,怎樣寫就是小說的一切。我還要加一點:一篇小說“說”的是什么,也非常重要。這個“說”就是英語所指的小說家通過小說發送的“message”,是字面下的。一篇小說怎樣寫是文字的問題,而“說”什么往往是一個小說家的全部素質決定的。國內好故事滿天飛,但不是每一個好故事都能被寫成一個好小說。這要看小說家們怎樣說這些故事,以及用這些小說“說”什么。
南都周刊:《小姨多鶴》來源于一個真實的故事,你還為此去了日本。寫《第九個寡婦》這部長篇你也到河南去,看他們怎樣吃喝、穿戴、過日子、閑談,生活的細節是否決定了你的小說的走向、長短和結局?
嚴歌苓:當然是在當地待的時間越長越好。細節可以觀察到,但一個地方的神韻,那地方人的神韻是要靠長期體味的。可是我現在的生活沒有這個條件,允許我待得更長。我除了做小說家,還有其他的責任,比如做妻子和做母親。不過我是盡了力了。
南都周刊:我記得一位朋友對我說過,你搜集了很多檔案,其中有沒有《寄居者》中那位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呼風喚雨的猶太大亨的原型?
嚴歌苓:史料里沒有杰克布這個人物的原型,這是我虛構的人物,除了小說的戲劇構架,小說里的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這是一部純粹虛構的小說。就像我的絕大部分作品和絕大部分作品中人物一樣,都是我虛構的,只不過虛構的成分有多有少。做歷史資料的搜集和調查—無論調查得多細致得到的資料多真實豐富,目的都不是為了省去“虛構”這一小說創作的第一重要手段啊。
這是我最有把握的一本書
南都周刊:你說寫小說“我也算是快刀手”,哈金說,他的小說反復修改多遍,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要字斟句酌?
嚴歌苓:我寫東西很快,做其他事情也一樣快。我是個圖痛快的人。任何事情有激情就一氣呵成地做。所以寫小說就是這樣,抓住一種感覺,找到一種語氣,對于一篇小說的創作非常重要,假如感覺和語氣斷了,再重新找,很困難,有時干脆就找不著了。我的一些小說流產,就是因為感覺和語氣斷了。
我覺得現在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說擱下一篇小說就要擱下,我就特別怕這樣把一篇原來寫得很好的小說感覺、語氣給丟了,所以有一段相對集中穩定的時間就爭取一口氣寫完,這就是我為什么顯得寫得那么快。
但我做一篇小說的準備工作是非常長時間的,有時候需要十來年。我讀D.H.勞倫斯的傳記時,發現他寫小說也很快,所以就對自己的創作習慣放心了。一個人有一個人創作的習慣。
南都周刊:那現在出了這本新書《舞男》也引起了很多關注,寫《舞男》是怎么樣的初衷?
嚴歌苓: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的大表姐,她向我介紹了這樣一種生活,在十幾年前的上海,有一些富有的海歸寄居者,使得我有這樣一個機會,了解到上海的另一面。
想寫這個故事也有很多年了,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寫這個故事?我的書最后寫成,往往和我在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有關。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前總編輯魏心宏先生問我:“你怎么老不給我們上海文藝出版社寫本書啊?”年年碰到我都問我:“什么時候寫出來啊?”我就有點不好意思,覺得不寫說不過去,我就給他寫出來了。也覺得每次到上海都去跳舞也跳出感覺來了,就寫了這部小說。
南都周刊:這部小說的主題是?
嚴歌苓:我用上世紀30年代一個在百樂門的舞男鬼魂的視角來看今天的男女、今天的愛情、今天性的關系,他來看今天女性凌駕于男性之上的身份關系,他想人們是不是不會像他們那個時代那樣戀愛?
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文學性的一面,我也有一些社會性方面的思考。我覺得中國社會新的階級正在形成,階層矛盾和分歧也在形成,現在的上海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構成的上海,和過去的上海大不一樣。我對現在上海的不同階層——講英語的海歸、本地土著以及那些漂泊在上海、底層的外來者,他們的不同命運都感興趣。
我原來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社會的旁觀者,現在我覺得我參與其中越來越多了,比早兩年寫中國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我每隔兩個月都要回來一次,我不再是側目而視的那個人了,這樣,我寫的時候就非常有激情,牢牢把控著故事、人物和氛圍的把握,應該講,這本《舞男》是我寫當代生活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一本書。
南都周刊:你的很多小說都改編成了電影,那這本《舞男》呢?
嚴歌苓:這部小說還在電子稿的時候就已經被一家公司買走了電影版權,但是后來有一家和導演有掛鉤的公司也想要買,我就和原來那家商量,說是不是可以讓出來,因為我覺得有導演掛鉤的,比較可以掌控電影的質量。而小說正式出版之后,對它電影版權的爭奪就非常激烈了,我也在考量,看哪一家才是最合適的。它得了解上海生活,它還能請得動好的演員,有的導演很好,但是不一定能請到很好的演員,我對電影的攝制和制作都沒有控制,因為我不喜歡控制任何東西,我也不喜歡控制任何人,喜歡控制人的那些人在我眼里都是很令人討厭的。
但關于文學和電影的關系,我覺得現在電影很熱,好像文學就得依靠,要找到電影這個寄居體才能存活,這是讓我覺得很悲哀的一件事。